《古代兵法散文·宋遼金元兵法·守城錄》原文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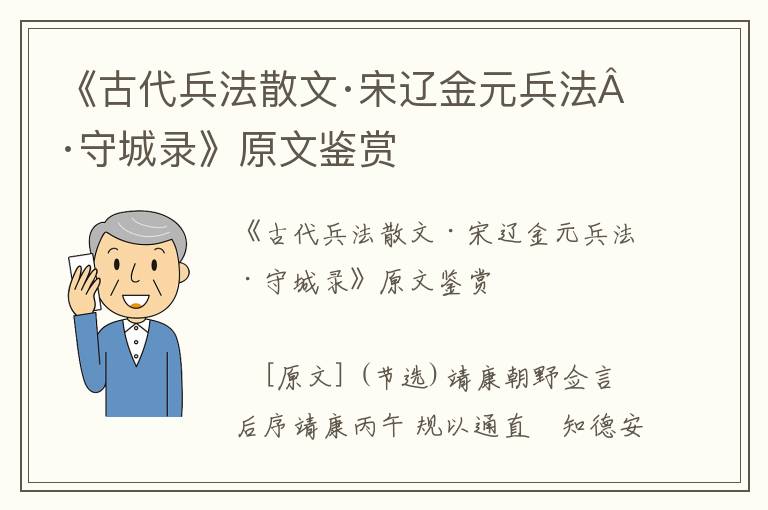
《古代兵法散文·宋遼金元兵法·守城錄》原文鑒賞
[原文] (節選)
靖康朝野僉言后序
靖康丙午 規以通直郞知德安府安陸縣事。丁未春正月,群盜王在等犯德安府。時郡將闕規攝府事,賊來攻城,規在城上與賊語,問何因到此。賊言:“京城已為金破。”規獨念都城之大,壕塹深闊,城壁高厚,實龍淵虎壘,況禁旅衛士百萬。雖金人乘我厄運,一時強盛,亦何能破?殆不足信,二月四日,賊遁,遣人詣都城奏功。還,乃知京城果為敵陷。徒深痛切,但不知破城之所以然。爾又恨當時不得身在圍城中,陪守御之士,以效綿薄。紹興己未春三月,朝延既復河南。規自祠宮被命知順昌府。夏五月到官。行及期年,暇日會同僚語及靖康之難,汝陰令云:“嘗收東齋雜錄一篇。中有《靖康朝野僉言》,具載金人攻城始末。”規得之熟讀,痛心疾首,不覺涕零。嗟乎!治亂強弱,雖曰在天有數,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揚雄所謂“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康京城之難,若非人事之失,則天亦不得而為災。規不揆至愚,竊觀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巨與將吏官帥應敵捍御之失,雖既住不咎,然前車之覆,后車之戒,事有補于將來,不可不備論也。朝廷欲再援太原,大巨以為中國勢弱,敵勢方強,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殊不知勢之強弱在人為,我之計勝彼則強,不勝彼則弱。若不用兵,何術以壯中國之勢,遏敵人之強?用之則有強有弱;不用則終止于弱而已。強者復弱,弱者復強;強弱之勢,自古無定,唯在用兵之人何如耳。
河東宣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河東義勇禁兵五萬,共兵二十二萬,皆敗績。致太原陷于敵,非兵不多,蓋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行而前,先鋒遇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卻,與其后大兵皆卻,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后知其不能援也。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則攻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住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二萬,只十萬亦可以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以優為之援也。又不五萬,至其下亦可援之理。且以五萬為率,若止分為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將,兼備策應內外,三兩將詣扼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敵境,綿亙可布三五十里。不知敵人用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求向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兵; 多則退之,少即擒之; 但絕其糧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并用。假令數將失利,其大兵必不至于一齊敗衄,潰散為盜。京城之難,其源在于援太原之失利也。
尼瑪哈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敵之眾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守城人中有善為守御之策者。僉言以為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城太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為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先策定險備,設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已使即死。今夫百里之城,內有數步之地,賊人登之,守城之人,使自甘心伏其城拔,乞命于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
九月,安炮于封丘門外。大炮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為金人所得,咸謂金人得攻城之具。規以為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炮數百座,亦必無害。在于御炮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發箭,止之甚善。百姓鼓眾擊殺,此亦見其自亂,素治之術失也。
敵先采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戴之,令人運土木填壕,欲進攻城。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大炮碎之;亦可用單梢炮,取遠至二百五十步外者,制其首領用眾之人蓋益州郡舊有朝廷所降守御冊定格,單梢炮上等遠至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此格用與不用。若人稍不完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 亦莫能及; 若能究心, 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 又以小炮御近眾,其小炮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致數十步。勿謂小炮不能害物,中人四肢,則四肢必折; 中腰以上,則人必死; 中馬亦然。又況大炮每放一炮,小炮可放數炮。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圓為之。 泥圓之利亦博,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放去中人, 人必死傷;不中則泥圓為炮擊破,不致反資敵用。若要摧毀攻械,則須用大炮及石。金人攻城用大炮,蓋欲摧壞城樓; 守城者欲摧毀敵人攻械,大炮與小炮齊用,縱敵在城外伐大木為對樓云梯火車等攻械,可以破盡。金人廣列壘石炮座,尋碑石磨盤石羊虎為炮;欲攻之所,列炮座百余。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御官一時失計耳。茍守御官得計,止令卒近女頭墻坐立,城外炮來,高則于女頭墻上過,低則打中女頭墻,擊破在外; 無緣中人一卒,亦不至于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唯女頭墻稍加高厚,則愈加安堵。又須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長一丈闊一丈上下外直里斜外密里稀洞子,外密處以大麻繩橫編,如荊竹笆相似,以備炮石眾多,攻壞女頭墻,即于兩邊連珠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炮石縱大數多,未易損壞。間有損者,即逐旋抽換。假令只如此御捍,則炮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其無虞也。
敵以云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間御捍,有設重樓獲勝者,固甚善也; 又恐人在重樓之上,愈招矢石。又攻東門,守御官具亦備。對樓云梯至,每以木沖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沖木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傷,亦非全勝。金人填壕橋成,運對樓過壕攻城。城下列炮座二百余所。七梢炮、撒星炮、座石炮并發,又以強弩千余助之。城上失石如雨,使守御卒不能存立,然后推對樓使登城。每對樓上載兵八十人,一對樓得城,則引眾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炮大數多,失石齊發,只前說女頭墻次備以洞子,皆可隔盡矣。對樓登城,每一對樓,果能載兵八十人?樓廣不過二丈,當面立得幾人?與守城人接戰者,不過十數人而已。假令八十人盡用力,施設五對樓,止四百人。此外必無伏兵,亦無奇兵。樓高須及五丈,乘高而來,其跡亦自甚危。自履危地,來與城上立平地人接戰,勝負人人可以自決。若守城者于此不勝,則交戰于平田廣野之地,不知其敗若何。況對樓填平壕上,唯可以直進直退,必不能于城下橫行。守人備御,不過止備對樓所占之地。假使有十對樓,所占地步數亦不多,不獨接戰可以必勝,縱兵上城獲全勝者,術亦多矣。不思則弗得也。
敵用云梯,止要登城。每座云梯,須十余人可以負荷到城。城上御之,亦難向前來。縱不御之,使敵倚城登梯,上至城頭,少不死者,何以致之?于女頭墻里鵲臺上,靠墻立排叉木。每空闊三四寸一根,通度槍刀向上,高出女頭墻五六尺,敵至女頭墻上,必為排叉木隔住,背后乘空,守御人于木空中施槍刀刺擊,豈有刺擊不下者?下而不死者鮮矣。
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再攻。推對樓五座,盛失石來城上。以竿沖倒三座。城上士卒爭持草以焚之。對樓木多而草盛火熾,火乘南風遂引燒城上樓子三座。對樓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卻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敵人攻械來路,可以置而不問。焚者失也,縱不引燒城樓,止燒了敵人對樓,亦是城上人自持草火,與敵燒開再進攻械來路。此事大失。所有再造城樓骨格,欲于舊處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敵必不容,矢石必倍。守御官若能用前說,造洞子于闕樓子處兩頭連珠并進,不終日決可蔽合,權代女頭墻,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于前,亦必無害。次于燒了城樓處兩頭,橫直深埋排叉木,以防敵急登。城上分甲兵兩向攻打。城里從下斜筑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于城里腳下取土為深壕,離壕三五丈,筑月城圍之。使敵乘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卻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倒入壕內無不死者。如此一挫,必罷攻退兵。乃守御之人失之以致城陷,豈不痛哉。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勢可畏者,莫甚于炮,然亦視人之能用與不能用耳。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御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雖能者,亦難施設。竊聞金人用炮攻城,守御人于城上亦嘗用炮。城面地步不廣,必然難安大炮,亦難容數多。雖有炮臺,炮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炮才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眾炮來擊。又城上炮亦在高處,自然招城外敵人用炮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當時守御之人,其不能用炮也明矣。假令當時于城里腳下立炮,仍于每座炮前埋立小木為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炮所在,雖有能用炮者,何由施設?或謂炮在城里,炮手不能見得城外事,無由取的。每一座炮。別用一人于城上,專管城里一座外照物所在,里照炮梢,與外物相對,即令施放。少偏,則令炮手略少挪腳;太偏,則令拽炮人抬轉炮座。放過,則令減人或用炮稍大者; 不及,則令添人或用炮稍小者。照料得一炮打中后,炮少有不中。又城里立炮,可置數多。守御人用炮若止能如此,則攻城人用炮何能為也?
筑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頭墻。女頭中間立狗腳木一條。每兩女頭中掛搭篦蒿,唯可以遮隔弓箭,于炮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墻,不用蓖籬,只于近下留品字方空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
或問何以備御城外腳下,自有馬面墻,兩邊皆見城外腳下,于墻頭之上,下害敵之物。當敵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遏,宜便于城里腳下取土為深闊里壕。去壕數丈,再筑里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卻于新筑城下緣里壕,入三二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于里壕垠上,新城腳下繚繞三二里,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敵善埴壕,止不過填得里壕。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腳下,里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臨敵,何物不可施用?正是敵人死地,必不敢入。由正門入城,尚且不敢,則豈肯用命打城?但只如此為備,則敵兵雖多,攻械百種,誠可談笑以待之矣。又況京師舊城,亦自可守。若逐急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之內,軍兵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令竭力修作,不獨添筑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令添筑城壕數重,亦不勞而辦。重城重壕既備,然后招敵人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諺云:“求人不如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于人。”皆此之謂也。
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聞當時敵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實者,止開三兩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閉生路,而為敵開其生路也。為守之計,不獨大啟諸門,仍于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有門數十座。齊門于城內運土出入,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覘望敵人空隙,稍得便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敵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內創開城門,自運土填壕,欲為出兵計,則其在外填壕欲入之計,不攻自破。然所以敢自創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敵兵可欺,蓋恃其自于城內設險已備,引敵入城,而敵必死耳。晉王浚遣都護王冒及鮮卑段疾陸眷、末杯等部五萬之眾,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為可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余道。勒既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陳未定,躬帥將士,鼓噪于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丕,疾陸眷等眾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余里,獲鎧馬五千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者也。后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
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為盡善。城上有敵樓,而敵人用大炮摧擊。城高數丈,而敵人用天橋、鵝車、對樓、幔道、云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作,可以自謂堅固前古所未有;奈何敵人攻械之備,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于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觀之,雖利不至于百,功不至于十,然自古圣人之法,未嘗有一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也。為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于馬面上筑高厚墻,下留品字樣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覘望,及設施槍路。墻里近下,以細木蓋一兩架瓦棚,可令守御人避寒暑風雨。屋在墻里,比墻低下,則炮在外雖大而數多,施設千萬悉莫能及人。
壕上作橋,橋中作吊橋,暫時隔敵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為實橋,則兵出入俱利。
城門宜迂迥曲折,移向里百余步置。不獨敵人矢石不入,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里,便是敵人落于阱。何謂落阱?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敵人,應敵之具,皆可設施。又于舊門前橫筑護門墻,高丈余,兩頭遮過門三二丈。城門啟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
城外腳下,去城二丈臨壕垠上宜筑高厚羊馬墻,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墻腳下亦筑鵲臺,高二三尺,闊四尺。鵲臺上立羊馬墻,上亦留品字空眼,以細覘望及通槍路,亦如大城上女頭墻。墻里鵲臺上栽埋排叉木,以備敵填平壕塹,及攻破羊馬墻至城腳下,則敵于羊馬墻內兩邊受敵。頭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敵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御之。羊馬墻內兵賴羊馬墻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墻與大城系是上下兩城,相乘濟用。使敵人雖破羊馬墻而無敢入者。故羊馬墻比大城雖甚低薄,其捍御堅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也。又羊馬墻內所置之兵,正依城下寨,以當伏兵。不知敵人以何術可解?若此則既有羊馬墻,而鹿角木可以不用,仍于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于羊馬墻內出入。又羊士墻腳去大城腳止于二丈。不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墻外,反害墻內人; 又不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槍。又于大城里城腳下作深闊里壕,里壕上向里度地五七丈,可作來往路,外筑里城排叉木,但多備下敵攻城應敵處。用此以設備,雖使敵人善攻,不足畏也。墨翟,宋大夫,善守御。公輸般為云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褋為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余。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此見攻械者,宜乎古人以為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見敵人設一攻械,而無數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規嘗聞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為兵者詭也,用無中形,詭詐為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然而有傳之于家而達之于遠,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者,不可不先傳也。嗟乎,靖康丙午,金人以兒戲之具攻城,守御者一時失計,遂致城拔。迄及一紀有余,而金人猶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陵。規于未知金人攻城設炮之前,每見人云:“金人攻城,大炮對樓,勢豈可當?”貴顯言之,則怏然而不敢辯; 眾人言之,則亦不敢痛析。今既知其詳,則豈可不盡曲折,剖其所見而言之?然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變萬化,人何能窮之?今止據金人攻城施設,略舉捍御之策。至于盡精微,致敵殺敵之方,雖不憚于文繁,而有所謂真不可示人者,未之傳也。又況雖欲傳之,有不可得而傳者矣。唯在乎守城之人,于敵未至之前,精加思索應變之術,予為之備耳。區區管見,輒序于僉言之后,紹興十年五月日陳規序。
[鑒賞]
《守城錄》是宋代城邑防御的專著,為南宋抗金名將陳規等所著。全書共4卷,約17800字。陳規(公元1095年~公元1145年),密州安丘(今屬山東)人,先后任安陸令、知德安府、知順昌府、樞密院直學士及知廬州兼淮西安撫使等職,以善于守城聞名于世。《四庫全書》提要中說;“宋自靖康板蕩,宇內淪胥,規獨能支柱經年,不可謂非善于備御然。”湯濤,字君寶,瀏陽(今湖南)人,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進士,曾任德安府教授。《守城錄》全書由《靖康朝野僉言后序》、《守城機要》和《建類德安守御錄》三部分組成,原各自成帙,寧宗以后合為一書,刊行于世。該書是我國歷史上較早較具體地講到城池守御作戰原則、應變之術、守城準備和戰具的兵書。現存有守山閣本、《墨海金壺》本、子書百種本、曾氏叢書本、《長恩書室》本、《四庫全書》本、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抄本及嘉慶、道光時刻本。
《守城錄》第一部分《靖康朝野僉言后序》,作于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靖康朝野僉言》原為夏少曾所著,詳細記述了靖康間金人攻汴始末。陳規在改知順昌府之后,得知同僚中有人收藏《靖康朝野僉言》,便找來“熟讀”。當他讀到京城黎民凄慘的景況時,“痛心疾首,不覺涕零”,于是便邊讀邊寫,批駁了夸大金兵威勢的種種觀點,總結了汴京失陷的教訓,闡述了應該如何御敵的意見,作為《靖康朝野僉言》的“后序”,遂成《靖康朝野僉言后序》一文。陳規在談到寫“后序”一文的目的時說:“朝廷大臣與將吏官帥,應敵捍御之失,雖既往不咎,然前車之覆,后車之戒,事有補于將來,不可不備述也。”著眼點是為了奪取“將來”宋金戰爭的勝利。第二部分《守城機要》亦陳規所著。靖康末(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荊湖一帶潰兵與饑民紛起,眾至數十萬,附近州縣皆被攻破,唯陳規率兵數千守德安(今湖北安陸),多次擊退其大規模進攻,深為朝廷所贊賞。《守城機要》就是德安守城經驗的具體總結,它著重論述了“城廓樓櫓制度及攻城備御之方”。對于在攻者有炮的情況下,城壘應該如何改造與加強,防守者如何正確用炮以粉碎敵之攻擊,守城軍民的組織編制、力量運用和守御實施等問題,均有詳細的說明,貫穿著“凡攻城者有一策,守城者則應以數策應之”的“因敵而變”的思想。第三部分《德安守御錄》是湯濤輯錄的陳規在德安的守城事跡,具體記述了陳規在德安率軍堅守孤城、奮力殺退金兵的經過,并于紹熙四年(公元1193年)向朝廷奏呈其書。這一部分,從軍事角度對城邑建筑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
《守城錄》是我國軍事史上一部重要守城專著,它根據攻城武器的發展和實戰經驗,闡述了守城戰法的改革。它認為,過去古人所說“沒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變法,沒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改換器物”是因循守舊,抱殘守缺。從現在的城池防守制度看,雖然改革的利益達不到百倍,功效也達不到十倍,但行不通的就要改革。它提出“善守城者”不能只守無攻,而要“守中有攻”,要注意溝通城內道路,便利隨時出擊。它主張改革城廓舊制,增強御炮能力。如收縮易受炮擊的四方城角,拆除馬面墻(城門兩側城墻上的突出部分)上的附樓,另“筑高厚墻”等。由原來的一城一壕代之以“重城重壕”,以增強城邑防御能力。它主張要有足夠數量的大炮,充分發揮大炮的威力,“以炮抑炮”,并具體闡述了炮在守城中新的使用方法。例如,由配置城頭變為暗設城里,由城上觀察目標,糾正射向和彈著點,等等。此書還記載了陳規于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研制成長竹竿火槍20余支及其在守城作戰中發揮的作用。這種火槍是最早的管形火器,在科技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曾詔刻《守城機要》為《德安守城錄》,頒行天下,令各地守城將領效法,在當時產生過很大影響。
《守城錄》守御之術,是建立在樸素的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一是強調“人為”。陳規針對當時朝廷中“敵勢方強,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的這種無所作為的投降主義論調,尖銳指出:“殊不知勢之強弱在人為。我之計勝彼則強,不勝彼則弱。若不用兵,何術以壯中國之勢、遏敵人之強用之,則有強有弱;不用,則終止于弱而已。強者復弱,弱者復強,強弱之勢,自古無定,唯在用兵之人何如耳。”陳規的這些觀點,在當時不僅在軍事上,而且在攻治上也具有重大意義。二是力主“先策”。即事先的籌策。在陳規看來,“先策定險設備”乃是善守者的一個重要標志。陳規認為,無論城大城小,關鍵在于是否有善守之人。有了善守之人,事先作了周密計劃,充分估計了各種危險,并作了相應的準備,敵人是無法攻克的。他還認為,敵情在不斷變化,具體的制敵之方也必將隨之而變化。強調“守城之人于敵未至之前,精加思索應變之術,預為之備耳。”三是堅持“為今”。強調必須按照新情況,對舊的“城池之制”加以適當的改革。認為“可則因,否則革”,一切從“為今”出發,一切以“今”之實際需要為準繩。陳規提出的一系列改筑城壘的方法,都是建立在他對“今”之透徹了解的基礎之上的。陳規這種以“今”為準的思想,現在看來也是正確的。
《守城錄》所論述的具體守城之法,無疑早已成為歷史。但它在記述其守御之術時所體現出的要把守御之地修建得堅不可摧,守中有攻,以及從武器裝備方面增強防御手段,等等,至今仍有參考的價值,對未來反侵略戰爭城市防衛作戰仍有借鑒作用。
當然,局部守城技術與戰術,無論如何的先進與成功,也難以挽回南宋整個戰略上的錯誤與失敗,因為技術與戰術總是受戰略、策略的制約。南宋王朝的滅亡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