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陽休之書》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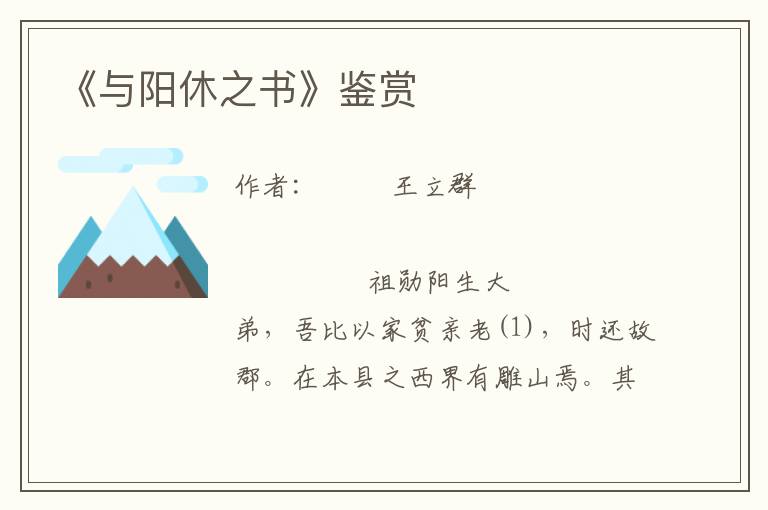
作者: 王立群
祖勛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1),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2),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于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3);日華云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蒽蒨(4)。時一褰裳涉澗(5),負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6)。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7)。首戴萌蒲(8),身衣缊袯(9),出藝粱稻(10),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為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11)!
而吾生既系名聲之韁鎖,就良工之剞劂(12)。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13),訪玉山之遺文(14)。敝精神于丘墳(15),盡心力于河漢。摛藻期之鞶繡(16),發議必在芬香。茲自美耳。吾無取焉。
嘗試論之。夫崑峰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光折。是以東都有掛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粱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17),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拼簪;則吾于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掛中重枝,攜酒登,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導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人生的意義何在?人究竟應當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這對于已經解決了生存需求并充分意識到人生選擇的封建士大夫來說,無疑是一個必須做出回答的問題。求富貴之樂,則可能如“崑峰之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光折。”保“七尺”之軀,則必須“解佩捐簪”,結廬山林。“孤坐危石”、“獨詠山阿”的歸隱生活,雖然在物質生活上較之仕途官場,顯得清貧寂寞,但是“簷下流煙”、“園中桃李”之景,自有其足樂之處。更何況“采漏簡”,“訪遺文”的讀書著述,還有其獨到之快意。這種精神上的輕松自得,當然非仕途可比。至于友朋之間,“把臂入林”,“攜酒登”,此種樂趣,宦途之中更無從領略。無怪乎作者要高呼“茲自美矣”,“斯亦樂矣”了。
南北朝之書信山水文,雖寥寥數篇,但多成于南朝作家之手,且俱為零簡片牘;祖氏此書,首尾俱存,是為完璧,因此更顯得彌足珍貴。與其它幾篇書信山水文相較,此文表述的物我同化的山水體驗也頗有深度:“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此刻作者似乎不再意識到自我的存在,渙然融匯到自然之中。同時,此刻的山水自然,也不再具有道德、情感、理性價值、無功利無實用,回歸到自然的本體。無知覺無意識的自我進入無目的無價值的自然,二者不分你我。物即我,我即物,物我同化,人的本體與自然的本體合二為一。作者在這種物我同化的體驗中,獲得了靈魂的安寧、心理的澄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