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死羊巖上》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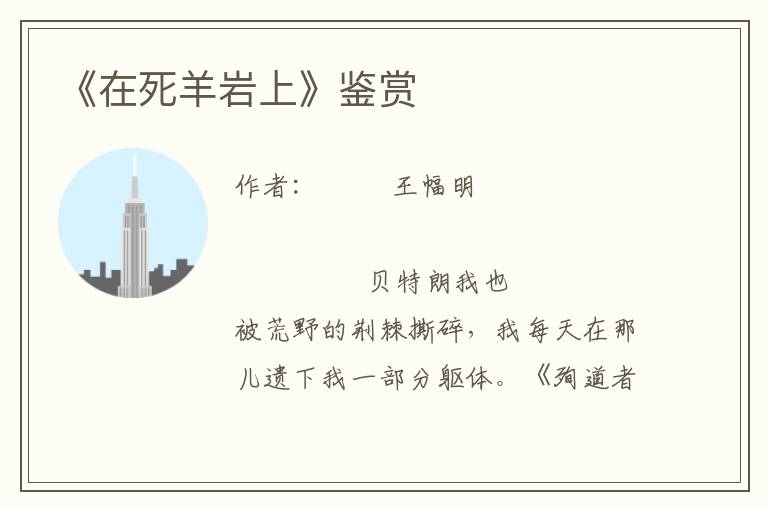
作者: 王幅明
貝特朗
我也被荒野的荊棘撕碎,
我每天在那兒遺下我一部分軀體。
《殉道者》(1)卷五
這里沒有橡樹上的蘚苔和新芽初吐的楊柳,這里沒有齊聲訴說愛情的微風和小溪。
雨后的清晨,露水凝聚的傍晚,嗅不到任何芬芳;除了尋覓青草的小鳥的啁啾,聽不見任何悅耳的聲音。
荒漠上再也聽不見讓·巴蒂斯特的聲音,荒漠上沒有隱士,也不見飛鴿!
我的靈魂也是一樣寂寞。在孤寂中,我躑躅在深淵的邊緣;生死咫尺,我發出一陣痛苦的鳴咽。
詩人就象脆弱而馥郁的紫羅蘭,生長在花崗巖縫里;他需要泥土,但更需要陽光。
可是,唉!自從賜我才華的那雙秀眼緊閉,我失卻了陽光!
(程依榮 譯)
一個幾百字的小品,能夠同時容納兩個主題,且表現得撕肝裂肺,震撼人心,這在散文詩史上,亦不多見。
題目本身便給人一種警示:生與死的抉擇。
一切都為了愛。為了一個能夠賜給詩人才華的美麗的靈魂。
在茫茫荒漠之上,詩人尋覓著。可他看到的是什么呢?沒有橡樹上的蘚苔。沒有新芽初吐的楊柳。沒有齊聲訴說愛情的微風和小溪。嗅不到任何芬芳。聽不見任何悅耳的聲音。這使我們想到,當一個人失卻愛情時,太陽也會失色。“一切景語,皆情語也”。大自然本身并沒有情感,在有情人眼里,它便有了情感。這也使我們想到,失去的這些,正是詩人倍加留戀的,是他和情人過去曾經享有的。可是,這一切,都失去了。因為,“荒漠上再也聽不見讓·巴蒂斯特的聲音”!
在異常的寂寞中,詩人來到死羊巖上,躑躅在深淵的邊緣。當詩人發出痛苦的嗚咽時,我們怎能不感到震憾!
詩人視愛情為生命的陽光,陽光失卻了,生命也就會隨之枯萎。把愛情看得高于一切,在現實生活中,固然不可取,但在藝術中,以殉情寫愛的忠貞,卻有它獨特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