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齋隨筆·古跡不可考》譯文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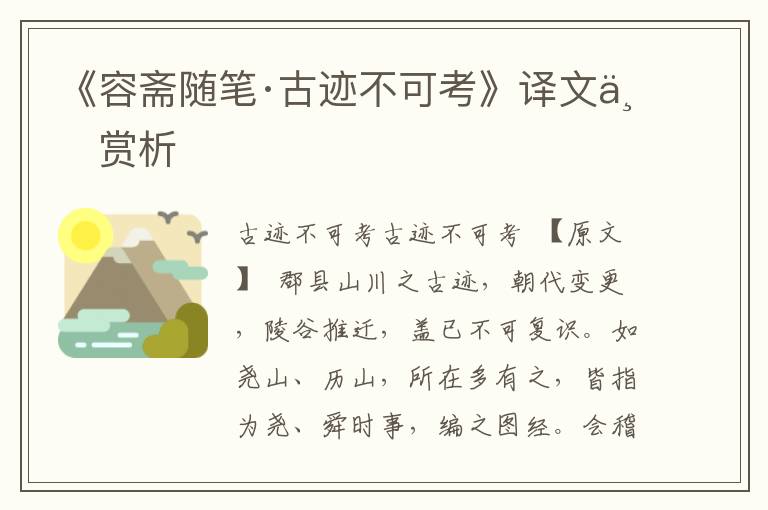
古跡不可考
古跡不可考
【原文】
郡縣山川之古跡,朝代變更,陵谷推遷,蓋已不可復識。如堯山、歷山,所在多有之,皆指為堯、舜時事,編之圖經。會稽禹墓,尚云居高丘之巔,至于禹穴,則強名一罅,不能容指,不知司馬子長若之何可探也?舜都蒲坂,實今之河中。所謂舜城者,宜歷世奉之唯謹[1]。按張蕓叟《河中五廢記》云:“蒲之西門所由而出者,兩門之間,即舜城也,廟居其中,唐張宏靖守蒲,嘗修飾之。至熙寧之初,垣墉尚固。曾不五年,而為埏陶者[2]盡矣。舜城自是遂廢。又河之中泠一州島,名曰中耼,所以限橋。不知其所起,或云汾陽王所為。以鐵為基,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然。嘉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跡。中耼自此遂廢。”顯顯者若此,他可知矣。東坡在鳳翔,作《凌虛臺記》云:“嘗試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記其一時之盛,宏杰詭麗,堅固而不可動。然數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謂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則區區泥于陳跡[3],而必欲求其是,蓋無此理也。《漢書·地理志》,扶風雍縣[4]有橐泉宮,秦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不以為穆公。
【注釋】
[1]宜歷世奉之唯謹:應當世代小心謹慎的奉祀。[2]雍縣:今陜西鳳翔。
【譯文】
郡縣的山川古跡會隨著朝代變更、地形地貌的推動遷移而發生變化,大都已經不是原來看到的樣子了。像堯山、歷山,許多地方都有這樣的山名,都稱是當年堯、舜活動過的地方,其地理圖形被編進圖籍中。會稽的大禹墓,據說位居高丘的頂端,對于禹穴,就只是牽強命名的一個裂縫而已,就連手指都不能容下,不知當時司馬遷是如何去探求禹穴的?舜的都城蒲坂,實際上就是現在的河中府(今山西永濟西)。所說的舜城,應該世代謹慎小心的奉祀。根據張蕓叟的《河中五廢記》中記載:“蒲坂城西的出入口,兩門之間,就是舜城,其中又有一座廟。唐朝張洪靖管理蒲州,曾經修葺此廟。到宋神宗熙寧初年,那里的城墻還相當堅固。不到五年時間,就被燒制陶器的人挖空了,舜城那時就被毀滅了。另外,河中建造一座小島,名叫中耼,用來固定橋梁。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有人說這座小島是唐朝汾陽王郭子儀所建造的,用鐵柱為基,島上還有河伯廟,它的周圍都環繞著水,喬木茂盛。宋仁宗嘉祐八年秋天,大水泛濫,這座小島被大水沖刷得了無痕跡。中耼從此也就消失了。”像這樣堅固的古跡都能夠遭遇這樣的命運,其他的古跡就可想而知了。蘇東坡在鳳翔時,曾寫《凌虛臺記》說:“我曾嘗試著登上高臺向東眺望,看到的是當年秦穆公祈年宮、橐泉宮的遺址,向南眺望,看到的是漢武帝的長楊宮、五柞宮的遺址,向北眺望,看到的隋仁壽宮、唐九成宮遺址。這些遺址在當時都是非常有名的宮殿,宏偉壯觀,堅不可摧。然而數世之后,想要再看到當年的壯美景象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看到的只有破墻爛瓦斷壁殘垣,以前的宮殿已經不復存在了。”所以說事物的廢興成毀,都是不可預料的。如果只憑著一點點殘留的古跡,就想求得其真實面貌,這是不可能做到的。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扶風雍縣(今陜西鳳翔)有橐泉宮,是秦孝公建造的。祈年宮是秦惠公建造,不認為是秦穆公所建。
【評析】
洪邁用古今廢興成毀的歷史,抒發“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的感慨,由此推出世事均不能以“區區泥于陳跡,而必欲求其是”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