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話實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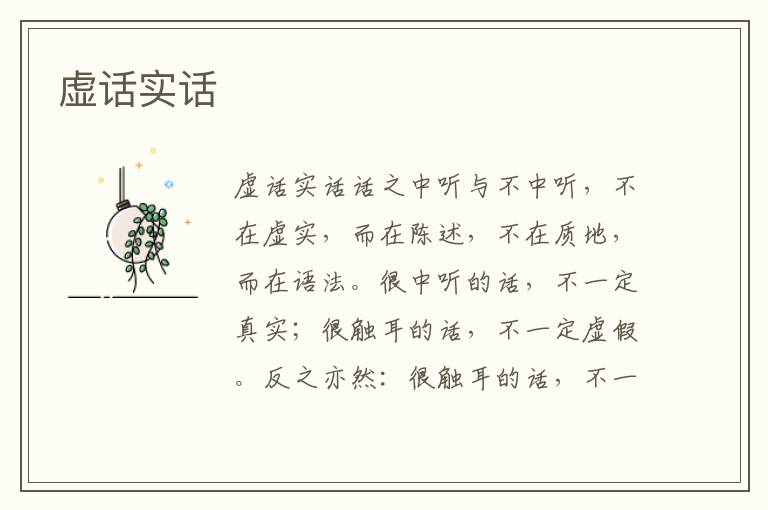
虛話實話
話之中聽與不中聽,不在虛實,而在陳述,不在質地,而在語法。很中聽的話,不一定真實;很觸耳的話,不一定虛假。反之亦然:很觸耳的話,不一定真實;很中聽的話,不一定虛假。我們有時喜聽觸耳的實話,也有時喜聽悅耳的虛話。在我們有時喜聽悅耳的實話,也有時喜聽觸耳的虛話。為什么呢?因為我們所喜聽的,不是話的質地,而是話的語法。
我們常常讀書閱報,也有這種情形。我們所閱讀的書報,不一定講真理,講實話。但是我們今天細讀,明天重讀,總是“手不釋卷”。我們閱讀書報,不全在討求真理。我們看他們的語法,看他們的語法好不好,周到不周到。說得周到,就是有點虛假,我們往往信以為真;說得不周到,就是全然真實,我們毎每不大相信。所以我們看《西游記》,覺得很好;看“前后漢”,也覺得很好。我們實在看文章,看語法,不是看事實,看虛實。
鄒吉甫是一個看墳墓的鄉下老頭子。他的小“東家”姓婁的兩位少爺,三公子,四公子,到他家里來了。他招待他們的時候說道:“鄉下的酒水,老爺們恐吃不慣。”四公子道:“這酒還有些身份。”鄒吉甫道:“再不要說起。而今人情薄了。這米做出來的酒汁,都是薄的。小老(吉甫自稱)還是聽見我死鬼父親(即“先嚴”之意)說:在洪武爺(明太祖)手里過日子,各樣都好。一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釀子。后來永樂爺(明成祖)掌了江山,不知怎樣的,事事都改變了;一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來。像我這酒,是扣著水下的,還是這般淡薄無味。”三公子道:“我們酒量也不大,只這個酒,十分好了。”
這故事節自《儒林外史》第九回。一樣的米,一樣的水,當然做成一樣的酒;決不會洪武時出的是二十斤,永樂時出的是十五六斤。鄒老頭的話,當然虛而不實。但是我們讀《儒林外史》的時候,總覺得他們講話講得伶俐,講得像一個“憂時憫世之子”。他講得自己的酒水分不多。我們雖然聽不見他的聲音,但是那幾句話,在那一回中,真是合宜;他的陳述,他的語法,最適當也沒有了。四公子的“這酒還有些身份”,未免太老實了——毛病出在一個“還”字。那個“還”字,是批評鄒老頭子的酒不佳——水分多而酒少。三公子年紀大些,閱歷多些,說話比他的弟弟高妙得多。他說:“我們的酒量也不大,只這個酒,十分好了。”客人的量,與主人的酒,卻好相合;主人聽見了,當然歡喜。三公子的“語法”真好,然而倒是一句客套話——假話。
詩曰:
語言無定質,
但看閑談人。
虛者反為實,
真誠可不真。
講實話者,當然呆笨;但是講虛話者,亦何嘗聰明?我們——不論受過教育的,或者沒有受過教育,總能分別他人的實話與虛話。我們聽他們的話,并非要“取”他們的“口供”,實在是“學”他們的語法。
有許多人在聽話的時候,想求獲真實,同時還想取得語法。他們做一件事,要達到兩個目的,一定失敗。他們的親戚朋友五分之四常說虛話,漸漸被察覺了,一一都斷絕了,那么他們豈不寂寞么?再經史子集中講的,不一定全是真理。倘然他們只愿讀那些講真理的,那末世上之書能讀者幾何?我們讀書,應當聽孟夫子的教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原載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文友》第四卷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