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路花雨·被搶走魚山的貓能成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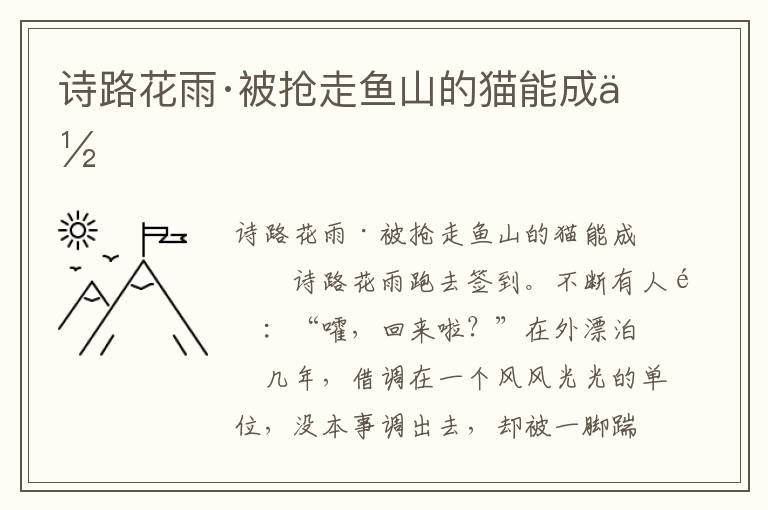
詩路花雨·被搶走魚山的貓能成佛
詩路花雨
跑去簽到。不斷有人問:“嚯,回來啦?”
在外漂泊好幾年,借調在一個風風光光的單位,沒本事調出去,卻被一腳踹回來,人家問兩聲也是正常的。有關心的,有獵奇的,我一律點頭復點頭,微笑復微笑:“回來了,嗯,我回來了。”
上午辦飯卡,走進一個月亮門,行行復行行,一轉頭——幾行高高的槐樹,細細的槐枝描畫著灰灰的天幕,樹腳下是長面包一樣的畦土,零落碎卷著那么多那么多的樹葉,交疊靜臥,遠處殘雪將消未消。乖乖,你真美。
去年冬雪淹了膝蓋,農田菜園俱被深埋,一條小路蜿蜒而過,一步步踏下去,左邊一歪,右邊一倒,倒下去手撐地,一只深深的手印就烙進雪里。通衢大道不肯行,只愿在小徑跋涉,實在是愛極了萬物皆被雪,唯枯草幾莖,支棱在渾圓的雪饃饃上,那樣圓潤渾然的景色,美得人心都發疼。
那時亦如現在,也是不快樂的。暗夜思索,總不知道活著為了什么。以前覺得發表一篇文章是無上的快樂,再以前,覺得教出一個好學生是無上的快樂,再以前的以前,家里若有錢給我買一頂新草帽便是無上的快樂,因為隨我爹去田里勞作的時候,頭上戴的這頂,早被風雨汗水漚得發黃變黑,險些糟成一個帽圈了……可是所有的快樂,都如同鮮艷的玫瑰凋落,枝頭殘瓣也被時光漂白了顏色。
好像這一生,從來沒有過那樣一無掛礙的,無牽無念的,快樂。
有時候想著把一切都舍了,去一個有山有水的所在,剃凈了三千煩惱的毛,那樣總該是快樂的。可是,讓別的女人住我的房,睡我的床,打我的孩子,讓我的老公鞍前馬后伺候著,我不舍得。而且,我還掙著工資呢,工資的背后是我十幾年的寒窗苦讀啊,我不舍得。不穿俗世的衣,不吃俗世的飯,不讀俗世的書,不寫俗世的文字,我不舍得。
就算舍得了,又能怎樣?數年前,偶去一寺院,矮小靜默,院子里幾個比丘尼光著頭擇野菜,小聲談笑,當時想著是好,讓人神往的那種好,可是,現在想來,我吃得慣野菜野果,卻耐不得幾個人在一起的生活。我害怕按時念經,按律吃飯,既害怕淹沒在一大群人里面,面目漫漶,又害怕不淹沒在一大群人里面,被孤獨和寂寞拉拽撕扯。若是我一個人住一所茅庵,我又不敢一個人睡覺。怕黑,怕鬼,怕大殿里金妝的佛。
所以,無論怎樣,都不快樂。心里想著要快樂要快樂,但所謂的快樂,又都是騙人的。
直到看見這一地的落葉。它們卷曲著,寥落重復疊復疊。周圍無人走路,自己細密的呼吸聲都聽得清清楚楚。長久以來的心情仿佛一幅暗啞的布,如今這布上綴了一小粒珍珠,一下子讓整塊布都活了,成了流麗的珠灰色。一霎時覺得被人辜負也沒什么,被人傷害也沒什么,被人誤會也沒什么,被人冷落也沒什么,真的,一切都沒什么。就是被命運的大手甩來甩去都沒什么。原先的那種痛苦啊,不安啊,憤怨啊,其實,都是因為一個“我”。覺得“我”被偏待了。就像一只貓,覺得面前有一座魚山,結果這條魚被人拿走了,那條魚被人拿走了,漸漸地,覺得所有的魚都被人拿走了……
可是你看,樹被偏待了,連衣服都被剝光扒凈了,它還在用枝子在灰藍的天上描啊描,姿態曼妙。它的腦子里是沒有這個“我”字的。葉子也被偏待了,風吹雪蓋,可是它還是那樣靜靜地躺著,不苦也不澀,因為它的心里沒有“我”。
世界如虎“,我”便是佛,佛是要舍身飼虎的,佛不痛,是因為他的肉身是個“我”,可他的心里沒有“我”。曾經見到一句話:“看淡自己是般若,看重自己是執著。”以往只覺平常,現在卻覺得像是金聲玉振,在耳邊一圈一圈地響起來了。
據說,倘若舍得把漂亮的琉璃珠子盛在鋼勺里,放在火上烤,珠子里面就會炸,外面一切完好。那炸開的細紋,就像開出的美到極致的花。做人也是如此吧,管它暗紅塵怎樣雪亮,熱春光霎時冰涼,把世情看淡,把自己量輕,然后,小小的,微細的,忘我的快樂便如琉璃珠子里面炸裂的細紋,初時是傷的,疼的,可是一點,一點,漂浮起來,明艷成暗夜里怒放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