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杜尚的難題及其美學(xué)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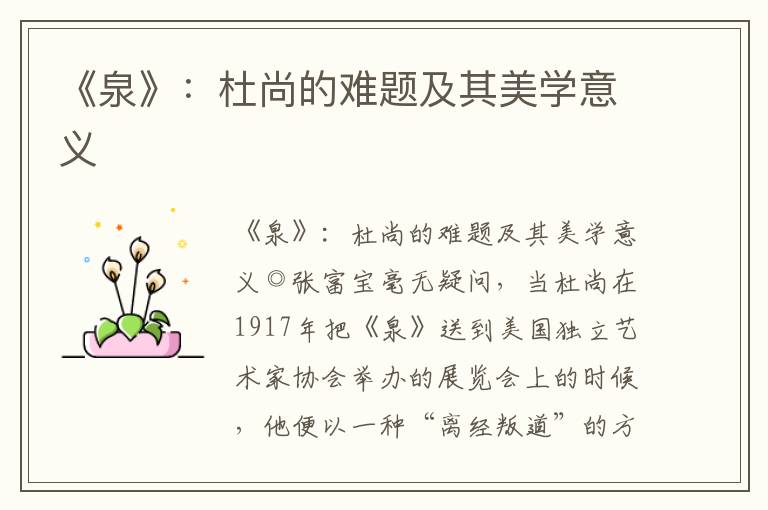
《泉》:杜尚的難題及其美學(xué)意義
◎張富寶
毫無(wú)疑問(wèn),當(dāng)杜尚在1917年把《泉》送到美國(guó)獨(dú)立藝術(shù)家協(xié)會(huì)舉辦的展覽會(huì)上的時(shí)候,他便以一種“離經(jīng)叛道”的方式提出了一個(gè)“杜尚的難題”,給了“藝術(shù)”與“美學(xué)”以當(dāng)頭棒喝。人們一方面為杜尚那種超乎尋常的挑戰(zhàn)姿態(tài)與奇思妙想驚奇不已,另一方面也難免忐忑不安、滿腹狐疑,甚至有人說(shuō)杜尚其實(shí)就是個(gè)騙子、流氓。那么,作為杜尚的代表作的《泉》,究竟是一種藝術(shù)作品呢?還是一件非藝術(shù)品呢?我們?cè)撊绾稳ダ斫狻度纺兀俊度返拿缹W(xué)意義究竟何在?
一、作為藝術(shù)品的《泉》
眾所周知,《泉》一方面臭名昭著而遭人詬病,另一方面卻影響深遠(yuǎn)被奉為圭臬。無(wú)論如何,我們都不能無(wú)視《泉》的存在,在2007年英國(guó)藝術(shù)界評(píng)出的20世紀(jì)5件最具影響力的藝術(shù)作品中,《泉》赫然位列第一(具體排名如下:1.《泉》,馬塞爾·杜尚,1917年;2.《亞威農(nóng)少女》,畢加索,1907年;3.《金色瑪麗蓮》,安迪·沃霍爾,1962年;4.《格爾尼卡》,畢加索,1937年;5.《紅色畫(huà)室》,馬蒂斯,1911年),這也充分說(shuō)明了它的價(jià)值。
事實(shí)上,當(dāng)我們開(kāi)始討論《泉》的時(shí)候,總是會(huì)有意或無(wú)意地去遵循某種既成的美學(xué)規(guī)范或藝術(shù)標(biāo)準(zhǔn),我們心中都有一個(gè)關(guān)于藝術(shù)品的理想答案。當(dāng)我們把《泉》作為藝術(shù)品的時(shí)候,主要的關(guān)注點(diǎn)會(huì)集中在以下幾個(gè)方面。
第一,小便池本身具有一種美的成分,能讓人產(chǎn)生審美關(guān)注,比如它的形式(如有人發(fā)現(xiàn)十個(gè)水眼排列得很好看,是不是意味著“十全十美”?有人認(rèn)為它的造型像是中國(guó)的觀音像),它的顏色,它的質(zhì)地,尤其是在當(dāng)代社會(huì)語(yǔ)境之中,它更是商品美學(xué)的產(chǎn)物(今日的衛(wèi)浴產(chǎn)品,已經(jīng)越來(lái)越成為一種藝術(shù)品),但需要提醒我們注意的是:《泉》的這些美并不是它的核心內(nèi)容和根本主題,《泉》揭示給我們的是另外一種東西。
第二,《泉》里面的小便池已不再叫作小便池,杜尚在給它簽名之后把它“命名”為《泉》,使之變成了“現(xiàn)成品”。這種“命名”是意味深長(zhǎng)的,它給人留下了巨大的闡釋空間。在某種意義上來(lái)說(shuō),藝術(shù)就是一種發(fā)現(xiàn)行為,一種命名行為,一種獨(dú)一無(wú)二的創(chuàng)造行為。在藝術(shù)史上,杜尚第一次發(fā)現(xiàn)、創(chuàng)造了以小便池為內(nèi)容的《泉》,使之具有了超乎尋常的價(jià)值,杜尚之后的任何人如果再重復(fù)杜尚的行為和作品,都只能是一些毫無(wú)意義的復(fù)制。
第三,從外觀上看來(lái),普通的小便池和《泉》并沒(méi)有什么大的區(qū)別,但前者只是一件普通的物品,是機(jī)器生產(chǎn)的產(chǎn)物,具有日常功用,它只是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一種家用器皿,它不會(huì)給人帶來(lái)特別的美學(xué)意義與藝術(shù)價(jià)值;而后者從日常生活中脫離了出來(lái),作為藝術(shù)作品被觀賞,從而“創(chuàng)造了新的思想”,激發(fā)了人們的思考,激發(fā)了人們的想象和聯(lián)想,它讓人驚訝、懷疑甚至惴惴不安。正如杜尚把小便池與《泉》置于人們的思考視野之中一樣,他的后繼者沃霍爾也把布里洛盒子與《布里洛盒子》(1964年展出)拋給了我們,“兩個(gè)東西彼此相像,但意義不同、身份不同”,在阿瑟·丹托看來(lái),“哈維的盒子沒(méi)有沃霍爾的盒子那樣的哲學(xué)深度,出于同樣的理由,莫特鐵廠生產(chǎn)的小便池沒(méi)有《泉》那樣的哲學(xué)——藝術(shù)——力度,《泉》的產(chǎn)生畢竟有助于改變藝術(shù)的歷史。”([美]阿瑟·C.丹托著,王春辰譯:《美的濫用》,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頁(yè))。
第四,《泉》被送到了藝術(shù)展覽會(huì)上(藝術(shù)環(huán)境)進(jìn)行了展覽,它以“挑釁”的姿態(tài)迫使人們從“藝術(shù)”的角度對(duì)它進(jìn)行考量。更進(jìn)一步來(lái)說(shuō),《泉》之所以能成為藝術(shù)品,與杜尚藝術(shù)家的身份是密不可分的。在杜尚之前,小便池的存在并不能給藝術(shù)的發(fā)展推進(jìn)帶來(lái)什么,也并不能給審美觀念的更新帶來(lái)什么;而相反,《泉》的出現(xiàn),卻根本性地改變了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和美學(xué)的觀念,改變了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史的發(fā)展進(jìn)程。
二、作為非藝術(shù)品的《泉》
當(dāng)然,在對(duì)《泉》進(jìn)行討論的時(shí)候,很多人往往是從“常規(guī)”與“成見(jiàn)”出發(fā)進(jìn)行考察的,或者說(shuō),人們往往會(huì)以“慣例”的審美觀念去對(duì)待它。譬如關(guān)于藝術(shù)的概念,美學(xué)家費(fèi)舍爾就認(rèn)為:a.藝術(shù)是手工制作的;b.藝術(shù)是獨(dú)特的;c.藝術(shù)應(yīng)該看上去是美觀的或美的;d.藝術(shù)應(yīng)該表現(xiàn)某種觀點(diǎn);e.藝術(shù)應(yīng)該需要某種技巧或技術(shù)(余虹:《審美文化導(dǎo)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4頁(yè))。這些觀點(diǎn)基本上概括了人們對(duì)藝術(shù)的傳統(tǒng)習(xí)見(jiàn)。那么,由此人們把《泉》視為非藝術(shù)品主要集中在以下四點(diǎn)。
1.藝術(shù)品應(yīng)該是與美聯(lián)系在一起的,要能給人帶來(lái)美的愉悅與美的享受。《泉》以小便池為表現(xiàn)對(duì)象,是丑的、污穢的,不能登大雅之堂。
2.藝術(shù)品應(yīng)該是少數(shù)稟賦超人的藝術(shù)家手工創(chuàng)造的產(chǎn)物,具有獨(dú)一無(wú)二性,但《泉》不是這樣,它是機(jī)器的產(chǎn)物,可以進(jìn)行批量生產(chǎn)。
3.藝術(shù)品應(yīng)該具有特殊的意蘊(yùn)和獨(dú)特的感染力,能創(chuàng)造一種新奇的“意象世界”,而《泉》淺顯、直白,只是一種普通物件。
4.藝術(shù)應(yīng)該來(lái)源于生活,但藝術(shù)同時(shí)要高于生活。像《泉》這樣的“現(xiàn)成品”,似乎毫無(wú)深刻的內(nèi)涵,人人都可以得而為之。
三、“悖論式的思考”:理解《泉》的另一種方式
上述關(guān)于《泉》是否為藝術(shù)品或者美不美的討論,實(shí)際上并沒(méi)有解開(kāi)杜尚式的“難題”。在我們看來(lái),杜尚式的“難題”的提出,其實(shí)是一場(chǎng)思想的革命,它直接指向傳統(tǒng)的藝術(shù)理論和審美標(biāo)準(zhǔn),迫使人們對(duì)“美術(shù)”“美學(xué)”等概念進(jìn)行重新思考,進(jìn)而開(kāi)啟了一種新的藝術(shù)與美學(xué)道路,它至少表明:
1.藝術(shù)不等于美——藝術(shù)可以是丑或其他美術(shù)。
在杜尚看來(lái),傳統(tǒng)的藝術(shù)總是被理解為審美愉悅的東西,藝術(shù)似乎與美是天然聯(lián)系在一起的。《泉》正是對(duì)這種傳統(tǒng)觀念的一種挑戰(zhàn)。《泉》顯示了美嗎?美詮釋了《泉》的意義嗎?顯然不是。事實(shí)上,把“藝術(shù)”與“美”捆綁在一起的觀念早已經(jīng)成為藝術(shù)家與藝術(shù)史家的眾矢之的。藝術(shù)史家H·里德就曾經(jīng)指出:“我們之所以對(duì)藝術(shù)有許多誤解,主要因?yàn)槲覀冊(cè)谑褂谩囆g(shù)’和‘美’這兩個(gè)字眼時(shí)缺乏一致性。……在藝術(shù)非美的特定情況下,這種把美和藝術(shù)混同一談的假說(shuō)往往在無(wú)意之中會(huì)起一種妨礙正常審美活動(dòng)的作用。事實(shí)上,藝術(shù)并不一定等于美。這一點(diǎn)已無(wú)須翻來(lái)覆去地重申強(qiáng)調(diào)了。”(H·里德:《藝術(shù)的真諦》,王柯平譯,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第4頁(yè))而美學(xué)家韋爾施則直接把當(dāng)代社會(huì)過(guò)度的審美化所導(dǎo)致的“非美”歸因于“美”與“藝術(shù)”這兩個(gè)概念的混同與濫用,傳統(tǒng)的藝術(shù)過(guò)于強(qiáng)調(diào)藝術(shù)之為美的方面。
2.藝術(shù)不等于感性——藝術(shù)可以是理性的思考,可以是一種“提問(wèn)”的方式,可以是近乎抽象的觀念。
在傳統(tǒng)的美學(xué)觀念與藝術(shù)理論當(dāng)中,藝術(shù)首先是一種感性的與物質(zhì)的存在(色、形、聲等),它要訴諸藝術(shù)的形式,訴諸人的審美感官,進(jìn)而讓人產(chǎn)生審美體驗(yàn)。但《泉》拋棄了這一點(diǎn),它直接指向人的觀念領(lǐng)域,猶如禪宗中的“當(dāng)頭棒喝”。正如阿瑟·丹托所說(shuō),杜尚的“現(xiàn)成品”意在“證實(shí)美學(xué)與藝術(shù)的最極端的分離”,他生產(chǎn)出了“沒(méi)有美學(xué)的藝術(shù)”“用知性來(lái)代替感性”。《泉》的意義就在于打破成規(guī),讓藝術(shù)徹底從材料與物質(zhì)的束縛中解放出來(lái),從而創(chuàng)造了藝術(shù)的更多的可能性;藝術(shù)可以不再拘囿于“形式”,而是直接進(jìn)行思考。
3.藝術(shù)不等于手工制品——它可以是機(jī)器生產(chǎn)物;藝術(shù)不等于“創(chuàng)造物”——它可以是“現(xiàn)成品”。
在傳統(tǒng)的美學(xué)觀念與藝術(shù)理論中,藝術(shù)從來(lái)都被看作是藝術(shù)家手工制作的產(chǎn)物,它需要藝術(shù)家付出艱辛的勞動(dòng),甚至是經(jīng)歷漫長(zhǎng)的時(shí)間“創(chuàng)造”而成,它是一種典型的“無(wú)中生有”的創(chuàng)造行為,凝聚著藝術(shù)家的個(gè)性、才華和心血,因此它往往是獨(dú)一無(wú)二的、無(wú)法重復(fù)的。比如達(dá)·芬奇的《蒙娜麗莎》即是如此。而杜尚的“現(xiàn)成品”,都是來(lái)源于生活中的已有之物,甚至是機(jī)器批量生產(chǎn)之物,它只是藝術(shù)家的“改造”與“重置”,比如《自行車(chē)車(chē)輪》即是如此,一件普通的物品(自行車(chē)車(chē)輪)被倒置在另外一件普通物品之上(木質(zhì)圓凳),從而變成了一件“作品”。杜尚不無(wú)狡黠地說(shuō):“感覺(jué)輪子的轉(zhuǎn)動(dòng)是一件非常令人欣慰的事”,相對(duì)于輪子的實(shí)際功用,他更喜歡這件作品的外觀。的確,杜尚的“現(xiàn)成品”創(chuàng)作,實(shí)際上是拋棄或懸置了原有之物的實(shí)用功能,從而獲取了不同的意義。
4.《泉》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西方藝術(shù)史的發(fā)展進(jìn)程,它開(kāi)辟了一條全新的后現(xiàn)代藝術(shù)之路,它對(duì)藝術(shù)與生活之間的關(guān)系進(jìn)行了“修復(fù)”與“重構(gòu)”。它表明,藝術(shù)與生活不是截然對(duì)立的,藝術(shù)可以是生活,生活也可以是藝術(shù)。在奧爾特加看來(lái),現(xiàn)代藝術(shù)具有鮮明的“非人化”傾向,它不再追求古典藝術(shù)的和諧、靜謐與逼真的美學(xué)效果,而是強(qiáng)化了藝術(shù)與生活之間的界限,強(qiáng)調(diào)藝術(shù)是高于、凌駕和超越于生活之上的,如畢加索的《哭泣的女子》《亞威儂少女》等作品就是最典型的例證,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再是溫柔的、美麗的、逼真的、鮮活的人體形象,而是變形的、扭曲的、丑陋的、幾何狀的物體形象。而后現(xiàn)代藝術(shù)則摒棄了這種觀念,它強(qiáng)調(diào)藝術(shù)的“生活化”,或者生活的“藝術(shù)化”,生活與藝術(shù)之間的鴻溝被填平了,比如《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如此溫馨,格外不同》(波普藝術(shù))、《輪胎雕花》(裝置藝術(shù))即是如此。
5.藝術(shù)不是少數(shù)人的特權(quán),它可以是大眾的擁有物,在后現(xiàn)代語(yǔ)境中,甚至“人人都可以成為藝術(shù)家”。于是,藝術(shù)終于被揭開(kāi)了神秘的面紗,不再擁有神圣的“靈韻”,而成了日常生活的尋常之物。
同時(shí),對(duì)《泉》的討論也讓我們對(duì)“一件作品美不美”, “是不是一件藝術(shù)品”這樣的提問(wèn)方式心存懷疑。這種是非判斷在面對(duì)《泉》這樣的作品時(shí)往往顯得無(wú)能為力,這正是二元對(duì)立的思維模式的局限。因此,我們主張?jiān)诿鎸?duì)《泉》這樣的作品時(shí),懸置是非判斷,放棄本質(zhì)與定義,即不是簡(jiǎn)單地去肯定或否定,而是以一種更為開(kāi)放的、兼容的視野,以一種悖論性的方式討論其影響和后果、價(jià)值和意義。
四、《泉》的難題與“藝術(shù)的終結(jié)”
1917年,當(dāng)杜尚把便池簽名之后送去展覽,并將之命名為《泉》的時(shí)候,他便以一種獨(dú)特的方式向“藝術(shù)”提出了挑戰(zhàn)。什么是藝術(shù)?什么是藝術(shù)品?什么是美?藝術(shù)是讓人觀看的還是讓人思考的?杜尚似乎要戳破人們思考的紅線,他將“現(xiàn)成品”直接挪用在藝術(shù)的視野之中,幾乎徹底摧毀了人們的傳統(tǒng)觀念。九十年之后,我們似乎還無(wú)法處置杜尚的《泉》,在很多人充滿狐疑地將它視為“藝術(shù)精品”的時(shí)候,我們可曾聽(tīng)見(jiàn)杜尚在歷史的某個(gè)角落里發(fā)出的哂笑?(1962年,杜尚就給漢斯·里希特寫(xiě)信說(shuō):“當(dāng)我發(fā)現(xiàn)現(xiàn)成品時(shí),我想的是氣一氣美學(xué)……我把瓶子架、小便池向他們的臉上砸去,以示挑戰(zhàn),而現(xiàn)在呢,他們卻因?yàn)樗鼈兊膶徝乐蓝鴮?duì)之崇拜。”)杜尚的詰難,直指“藝術(shù)的終結(jié)”。
美國(guó)當(dāng)代著名的藝術(shù)批評(píng)家阿瑟·丹托據(jù)此提出“藝術(shù)終結(jié)論”,在西方學(xué)術(shù)界引起廣泛爭(zhēng)論和探討,他的一些重要論著也相繼被譯為中文。阿瑟·丹托著作的中譯本有:《藝術(shù)的終結(jié)》(歐陽(yáng)英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藝術(shù)的終結(jié)之后——當(dāng)代藝術(shù)與歷史的界限》(王春辰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 《美學(xué)的濫用——美學(xué)與藝術(shù)的概念》(王春辰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不過(guò)就目前的整體研究狀況而言,中國(guó)學(xué)界在這方面的研究還相對(duì)比較薄弱和滯后,對(duì)丹托似乎并沒(méi)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對(duì)其觀點(diǎn)也難免有一些誤解。丹托認(rèn)為,藝術(shù)的終結(jié)其實(shí)是藝術(shù)自我意識(shí)的解放,是歷史進(jìn)入后歷史時(shí)期的一種理想狀態(tài),在這一時(shí)期,藝術(shù)成為生活中的藝術(shù),與人的自然生存有機(jī)結(jié)合,而不是疏離于人的生活和生存。丹托一再闡明,“藝術(shù)”這個(gè)術(shù)語(yǔ)其實(shí)是近代觀念的產(chǎn)物。也就是說(shuō),那些我們今天視為藝術(shù)的東西,在歷史的進(jìn)程中未必被看作藝術(shù),它是逐漸被人“建構(gòu)”起來(lái)加以認(rèn)識(shí)的。由此,近代藝術(shù)史學(xué)的建立和發(fā)展,實(shí)際上是“一門(mén)通過(guò)觀念來(lái)建構(gòu)藝術(shù)的歷史的認(rèn)識(shí)的學(xué)科”。丹托進(jìn)一步把藝術(shù)史分為三個(gè)歷史的宏大敘事模式:在第一階段,追求的是準(zhǔn)確再現(xiàn)的進(jìn)步歷史;到了第二個(gè)階段即是現(xiàn)代主義的階段,追求藝術(shù)自身媒介的純粹性,追求藝術(shù)的純粹性;而到了第三個(gè)階段,也就是后現(xiàn)代主義階段,在藝術(shù)作為視覺(jué)形象的表現(xiàn)載體越來(lái)越趨于觀念化、哲學(xué)化時(shí),藝術(shù)史走向了作為觀念訴求歷史的終端,即意味著藝術(shù)史敘事的終結(jié)。
在阿瑟·丹托看來(lái),藝術(shù)終結(jié)的真正含義指的是“一個(gè)故事已經(jīng)結(jié)束”, “所終結(jié)的是敘事,而不是敘事的主題”,它實(shí)際上是指現(xiàn)代主義的藝術(shù)歷史的敘事正在走向瓦解。藝術(shù)的終結(jié)并不意味著藝術(shù)已經(jīng)奄奄一息或是壽終正寢,也不意味著藝術(shù)的事實(shí)性“死亡”或消失,而是說(shuō)藝術(shù)不再受制于“哲學(xué)的剝奪”,不再必然與美學(xué)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不再局限在某種整一而宏大的敘事結(jié)構(gòu)之中,從而獲得了一種新的可能性,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與自由。看來(lái),阿瑟·丹托對(duì)藝術(shù)的終結(jié)并不像人們通常所理解的那樣憂傷和悲觀,而是充滿了樂(lè)觀與期待。在“藝術(shù)的后歷史時(shí)期”,藝術(shù)創(chuàng)作還將持續(xù)進(jìn)行下去,而且會(huì)呈現(xiàn)出一種復(fù)雜的多元化的特征。“從一種角度講,當(dāng)代是信息混亂的時(shí)期,是一個(gè)絕對(duì)的美學(xué)熵狀態(tài)(美學(xué)擴(kuò)散及小時(shí)候的狀態(tài)),但它也是一個(gè)絕對(duì)自由的時(shí)期”。今天,不再有任何歷史的界限。什么東西都允許。正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說(shuō)的那樣:上帝死了,便沒(méi)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藝術(shù)終結(jié)之后,加在藝術(shù)頭上的各種“緊箍咒”解除了,也沒(méi)有什么不可能。在這種情形之下,藝術(shù)家“將創(chuàng)作出缺乏我們期待已久的那種歷史重要性或歷史意義的作品。當(dāng)人們已經(jīng)懂得什么是藝術(shù)以及什么是藝術(shù)的意義的時(shí)候,藝術(shù)的歷史舞臺(tái)也就完結(jié)了。藝術(shù)家已經(jīng)為哲學(xué)鋪了路,而任務(wù)最終必須被轉(zhuǎn)移到哲學(xué)家手中的時(shí)刻也已經(jīng)來(lái)到。”顯然,丹托在這里繼承了黑格爾的藝術(shù)終結(jié)論,并把它納入到當(dāng)代的現(xiàn)實(shí)情境之中。在《點(diǎn)石成金》(1981年)一書(shū)中,丹托鮮明地指出:“……隨著布里洛盒子的出現(xiàn),(想要定義藝術(shù))的可能性已經(jīng)有效地關(guān)閉,而藝術(shù)史也以某種方式走到了它的盡頭。它不是停止(stopped)而是終結(jié)(ended)了,這是就這樣的意義而言的:它已經(jīng)經(jīng)過(guò)并來(lái)到了這樣一種自我意識(shí),在某種程度上它已經(jīng)成為它自身的哲學(xué):一種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xué)中曾經(jīng)預(yù)言過(guò)的狀態(tài)。”由此看來(lái),藝術(shù)歷史敘事的終結(jié)便不是一種嘩眾取寵的口號(hào)與宣言,而是一種必然會(huì)發(fā)生的事實(shí)。
如果說(shuō)杜尚還在苦苦探尋和追問(wèn)著藝術(shù)的命題,那么安迪·沃霍爾則在杜尚的道路上走得更遠(yuǎn),他完全摒棄了一切偏見(jiàn)和陳規(guī),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進(jìn)行“制作”。他的《布里洛盒子》里有什么歷史?有什么意義?有什么人性的價(jià)值?同樣,《金色瑪麗蓮·夢(mèng)露像》(1962年)印刷著橫豎排各5個(gè)瑪麗蓮·夢(mèng)露照片,都有著黃色的頭發(fā)、鮮紅的雙唇和誘人的膚色,除了印刷造成的明暗度稍有差異之外,這些夢(mèng)露像幾乎都是一樣的。這些夢(mèng)露像可以通過(guò)照相底片無(wú)限制地自我復(fù)制下去,它們已經(jīng)變成為一種純粹的符號(hào)、“無(wú)質(zhì)量的影像”。它們的意義和價(jià)值在哪里?安迪·沃霍爾的創(chuàng)作正是丹托藝術(shù)理論的最好體現(xiàn),因?yàn)槲只魻柺恰皬臍v史的負(fù)擔(dān)下獲得解放的藝術(shù)家”,他可以用他希望的任何方式、為他希望的任何目的,或者不為任何目的而去自由地創(chuàng)作。沃霍爾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驚心動(dòng)魄的、似乎沒(méi)有生命氣息的“物的世界”,他甚至希望自己能像一臺(tái)機(jī)器那樣,不斷去制作。把梵高的《一雙農(nóng)鞋》與沃霍爾的《鉆石灰塵鞋》進(jìn)行比較,我們就能直觀地看到他們之間的巨大區(qū)別。在詹姆遜看來(lái),這種區(qū)別正是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之間的區(qū)別。而哲學(xué)家海德格爾在分析梵高這個(gè)作品時(shí),提出“大地”和“人間”的觀念,認(rèn)為藝術(shù)品就是在兩者之間的空隙裂縫中掙扎求存的。海德格爾說(shuō):“從鞋具磨損的內(nèi)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著勞動(dòng)步履的艱辛。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舊農(nóng)鞋里,聚集著那寒風(fēng)中邁動(dòng)在一望無(wú)際的永遠(yuǎn)單調(diào)的田壟上的步履的堅(jiān)韌和滯緩。鞋皮上粘著濕潤(rùn)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臨,這雙鞋底在田野的小徑上踽踽而行。在這鞋具里,回響著大地?zé)o聲的召喚,顯示著大地對(duì)成熟谷物的寧?kù)o饋贈(zèng),表征著大地在冬閑的荒蕪田野里朦朧的冬眠。這器具浸透著對(duì)面包的穩(wěn)定性無(wú)怨無(wú)艾的焦慮,以及那戰(zhàn)勝了貧困的無(wú)言喜悅,隱含著分娩陣痛時(shí)的哆嗦,死亡逼近時(shí)的戰(zhàn)栗。這器具屬于大地(Erde),它在農(nóng)婦的世界(Welt)里得到保存。正是由于這種保存的歸屬關(guān)系,器具本身才得以出現(xiàn)而得以自持。”這顯然是一種詩(shī)意烏托邦的建構(gòu),它依然執(zhí)迷于“藝術(shù)世界”的創(chuàng)造。但在沃霍爾的《鉆石灰塵鞋》中就看不到這些,它摒棄了詩(shī)意、情感、思考和疼痛,給人帶來(lái)的是一種物戀般的幻覺(jué)和欣快癥,是一種無(wú)時(shí)間、無(wú)深度、無(wú)歷史的事物表象,它顯示了“主體的死亡”的后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征象。后現(xiàn)代社會(huì)是一個(gè)“前所未有的標(biāo)準(zhǔn)化,時(shí)間均勻地流動(dòng),一切服從于時(shí)尚和傳媒的不斷變化”(詹姆遜)的社會(huì),這正是波德里亞所說(shuō)的“仿像的社會(huì)”,它無(wú)疑給藝術(shù)帶來(lái)了毀滅性的打擊。在這里的,傳統(tǒng)的藝術(shù)存在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挑戰(zhàn)。當(dāng)然,阿瑟·丹托并不像阿多諾、波德里亞那樣悲觀、絕望,他希望用自己的理論建構(gòu)為人們理解今天的時(shí)代及其藝術(shù)提供幫助。
如果說(shuō)杜尚是通過(guò)其離經(jīng)叛道的藝術(shù)實(shí)踐通向了“藝術(shù)的終結(jié)”,他無(wú)疑是一個(gè)早慧的天才,他的巨大的示范性效應(yīng),在波普藝術(shù)、行為藝術(shù)、裝置藝術(shù)、大地藝術(shù)、觀念藝術(shù)等領(lǐng)域都得到了很好的體現(xiàn)。時(shí)至今日,他的精神能量還沒(méi)有被窮盡。而阿瑟·丹托則是在理論上對(duì)“藝術(shù)的終結(jié)”進(jìn)行了闡釋和推動(dòng),他以一個(gè)哲學(xué)家的開(kāi)闊的視野為我們展示藝術(shù)史敘事的真相,讓我們頓時(shí)豁然開(kāi)朗。杜尚之后,藝術(shù)沒(méi)有什么不可以,它有完全的自由,甚至有人說(shuō)杜尚提供了一種“反藝術(shù)的藝術(shù)”“反美學(xué)的美學(xué)”;而在阿瑟·丹托之后,人們認(rèn)識(shí)到即使“藝術(shù)”“藝術(shù)史”這樣的概念也不過(guò)是人主觀建構(gòu)的產(chǎn)物,它在特定的歷史時(shí)段必然要走向“終結(jié)”。那么,這些都在表明:無(wú)論社會(huì)如何發(fā)展,藝術(shù)始終都是開(kāi)放的,也是沒(méi)有盡頭的。藝術(shù)終結(jié)之后,藝術(shù)就沒(méi)有了唯一的發(fā)展方向和堅(jiān)實(shí)的邏輯鏈條,也沒(méi)有了固定的風(fēng)格特征和歷史結(jié)構(gòu);在藝術(shù)終結(jié)之后,藝術(shù)沖破了哲學(xué)、美學(xué)以及政治的禁錮,最終成為其所是;在藝術(shù)終結(jié)之后,生活與藝術(shù)的關(guān)系得到新的修正,藝術(shù)不再遙遠(yuǎn)和神秘,甚至人人都可能成為藝術(shù)家。
本文為2015年度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西部項(xiàng)目“后現(xiàn)代文化語(yǔ)境與審美異化問(wèn)題研究”階段性成果,項(xiàng)目編號(hào)15XZX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