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犀牛的胃里》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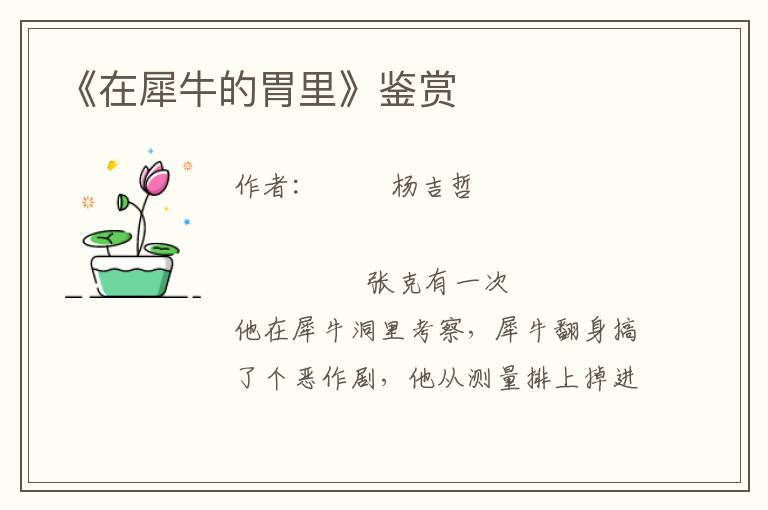
作者: 楊吉哲
張克
有一次他在犀牛洞里考察,犀牛翻身搞了個惡作劇,他從測量排上掉進犀牛潭,一直往下掉,掉進了犀牛的胃底。他想,這回一定是完蛋了;不過能拿犀牛的胃作墳地也算永垂不朽。在等待著死去的那個時刻,他忽然想起“死不瞑目”那個成語,他拿定主意,決不主動閉上眼睛,決不!他果斷地作出這個決定。
他那雙長期在洞穴中鍛煉出來的深邃目光,在此最后時刻居然又發(fā)現一個秘密:犀牛的胃原來也是一個具有獨特景況的溶洞,洞頂、洞壁、洞底,都有各種形態(tài)的堆積。他便仔細觀看做起觀察來了。他很滿意,動手測量,寫下一些數據;還估量犀牛的肚子里有多大的旅游價值。經過他考察的洞已有六百零八個吧,犀牛的胃按序列該排在六百零九。六百零九,問心無愧,也對得起溶巖地質工程師的職稱。于是他又想,這回可以瞑目了,準備慢慢合上眼睛……只可惜那些數據送不出去。
這時他忽然覺得犀牛正把他往外送,怎么哪?難道犀牛終于明白,外面還有許多溶洞需要他繼續(xù)考察?哪有這等好事!中學動物課本站出來提醒他,牛是反芻動物……這一下他真的傷心了,原來犀牛是要送他到口里去咀嚼!咬下來,那該有多痛!
也該他大難不死,犀牛也有疏忽大意,這個五十五歲的小老頭,一個箭步,用跳欄的姿態(tài),越過了犀牛成排的牙齒……
……測量排上,一雙搶救的手伸下來,伸下來,把他抓了上去。他的頭此后禿得相當厲害,有人說就是在那一次,犀牛把他的頭發(fā)當青草吃了。
一位巖溶地質工程師在犀牛洞考察,不慎跌入了犀牛潭,結果便是:工程師差點兒丟掉了生命,詩人得到的比一個生命還多。
與其說這是一個真實事件的描述,毋寧說這是一篇關于人的寓言,是一篇成人童話。在這首散文詩里,犀牛洞作為一種自然背景和物質力量,與人的行為構成了深刻的張弛關系,這種關系的張弛變化就成了一個人的重要經歷和全部命運。在這里,詩人的意向是十分明顯的。他充滿了對人的生命價值和意義的探尋與肯定。“六百零九,問心無愧”。工程師在危難之際這句平靜的獨白,包含著奮斗者多少欣慰!
犀牛洞不啻是一個隱喻。它通過要命的惡作劇演化為象征,從而把人類行為推到了更廣的物質給予和限定之中,使全文的事件敘述具有了不確指性。也許正是這種不確指性方使得生活和藝術得以互相驗證,并把二者區(qū)別開來。我們也才有權對藝術說:這是生活;對生活說:這不象生活。一位工程師在他的生命之旅中考察了六百零九個溶洞,犀牛洞是其中之一,也是它們的全部。從犀牛洞出來他的頭便禿得相當厲害,“有人說就是在那一次,犀牛把他的頭發(fā)當青草吃了”。其實,他的頭發(fā)并不全是交給了一個犀牛洞,而是交給了六百零九個,甚至更多。這種假意的具體場景和事件的給定,是詩的手段。它的典型性正是從這種假意的給定中顯示出來,啟迪人們聯想到主人公整個一生,并進而領悟到:人的生命不正是在對事業(yè)成功的追求中,才使“消耗”獲得了永恒價值么?
值得一提的是,這首散文詩中稚拙的比擬,自娛般的夸張和近乎荒誕的描述,不僅擦亮了主人公的人格光輝,而且還使素樸的語言充滿了諧趣。因此,我們說,那看似樸拙的文采,其實充溢著耐人尋味的詩意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