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宗崩駕疑案新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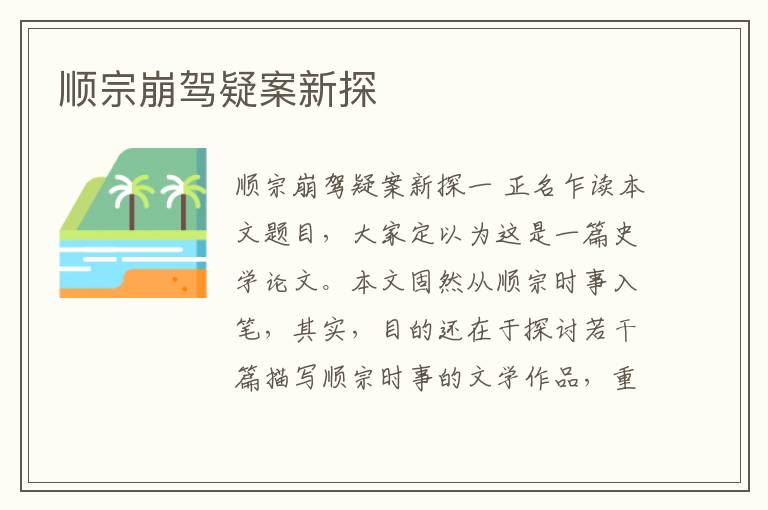
順宗崩駕疑案新探
一 正名
乍讀本文題目,大家定以為這是一篇史學論文。本文固然從順宗時事入筆,其實,目的還在于探討若干篇描寫順宗時事的文學作品,重點是研究李賀《漢唐姬飲酒歌》的題旨,從而說明順宗李誦崩駕的前前后后及其原因,目的在以史證文,以文補史,溝通史學與文學。
二 問題的提出
唐順宗李誦是怎樣死的?
《順宗實錄》(舊題韓愈撰。張國光以為韓愈所撰之《順宗實錄》已佚,今存于韓愈集中的《順宗實錄》,乃是韋處厚所撰,誤為韓愈撰。見《文學評論叢刊》第七輯張國光《今本〈順宗實錄〉非韓愈所作辨》,其說欠妥。)是這樣記載的:
“永貞二年(按即元和元年)正月景戌朔(按《舊唐書·順宗紀》、《資治通鑒》卷二百三十七均作‘丙寅朔’,陳景云《韓集點勘》:‘按順宗之崩在正月甲申,則此月之朔,非景戌也,戌作寅為是’。當從之。)太上皇于興慶宮受朝賀。”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兩點:一,順宗受朝賀日到崩駕日,僅相去十九天;二,實錄僅言“崩”,未書原因,其他史書同此。
順宗崩駕的疑案,在史書中是找不到直接答案的,因為新舊《唐書》的《順宗紀》、《資治通鑒·唐紀》所記,大抵本于《順宗實錄》。韓愈所撰之《順宗實錄》,記及順宗朝禁中事宜,幾經修改、詳正刊去,見路隨《修定順宗實錄錯誤奏》及《舊唐書·路隨傳》。況且《順宗實錄》“未周悉”,記朝中事詳,記禁中事則略,所以,順宗死因,在《順宗實錄》里初未談及。
陳寅恪先生已經注意到李諒《續玄怪錄》與永貞時事有關系,他指出:“蓋其黨類(指閹宦)于永貞之末,脅迫順宗以擁立憲宗。”他從史書的字里行間,綜觀分析,得出這樣的結論,極是。但陳氏以為《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條,乃是假道家“兵解”之詞,以記憲宗被弒之實,(見《順宗實錄與續幽怪錄》,載《陳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館叢稿二編》)卻未為學界公認。卞孝萱同志的《劉禹錫年譜》:“憲宗元和元年正月改元,順宗卒。”附注云:“陳寅恪認為這(企按:指《續玄怪錄》卷一‘辛公平上仙’條)是影射憲宗被殺,誤。他(企按:指李諒)用傳奇表達順宗被殺的隱事,以抒其悲憤,留下珍貴的史料。”后來,章士釗先生《柳文指要》采用了卞孝萱同志的意見,于卷四《晉文公問守原議》的體要部分,確認李諒《續玄怪錄》卷一‘辛公平上仙’條,是記載順宗被弒的“幸存史跡”。
順宗被弒這一歷史疑案,真的成了“劍匣帷影”無可考索了嗎?是否除了《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條外,就沒有其他資料可以助證了嗎?筆者為此而綜采各種史料,旁及唐人文學作品,揆理而論,撰《順宗崩駕疑案新探》,證成近代學者的發見。
三 談談與順宗崩駕有密切關系的三個問題
要探討順宗死因,不能不回溯永貞時事。永貞時事極多,筆者在此先談三個與此密切相關的問題。
首先,誰是永貞政治改革運動的主導者?
封建史家都把永貞時事歸罪于王叔文其人。“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新唐書·柳宗元傳贊》)“惜乎寢疾踐祚,近習弄權。”(《舊唐書·順宗紀》附史臣韓愈言)韓愈《永貞行》也說:“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這實在是冤枉了王叔文的。平心而論,順宗李誦并不象乃父李適那樣剛愎自用,貪婪昏庸,乃是個英睿果斷、極有政治識見的君王。李誦在東宮時,已充分表現出他的政治才干來:
《順宗實錄》云:
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為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奸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侯顏色,輒言其不可。……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
《舊唐書·順宗紀》附“史臣韓愈曰”:
從幸奉天,賊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戰,督勵將士,無不奮激。……嘗侍宴魚藻宮,張水嬉,彩艦雕靡,宮人引舟為擢歌,絲竹間發,德宗歡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為對。每于敷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
德宗晏駕后,李誦登位。他推行了許多改革弊政的有力措施,都是他當太子時早就想實施的政治主張:
《資治通鑒》卷二三七:
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眾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
《順宗實錄》:
“(宮市之患)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
“(五坊小幾張捕鳥雀)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
至于王叔文等人被信用,也是李誦在東宮時長期考察的結果。這個問題,前人述之詳矣。柳宗元《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志文》:“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儲后,凡十有八載,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先帝棄萬姓,嗣皇承大位,公居禁中,訏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銘曰: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毗,邦人是望。”這都是柳宗元稱贊王叔文具有輔弼良才的話。李誦對王叔文也是極為賞識,《舊唐書·韋執誼傳》記載李誦的話:“太子曰:學士知王叔文乎?彼偉才也。”劉禹錫《子劉子自傳》也說:“時有寒雋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新唐書·王叔文傳》:“王伾密語諸黃門,陛下素厚叔文,即由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
順宗登位后,病喑不能語,但內外大事,還是出于他的旨意。“群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新唐書·王叔文傳》)“美人以帝旨傳忠言,忠言授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后下中書。”(《新唐書·劉貞亮傳》)《順宗實錄》載順宗任王叔文為度支鹽鐵副使時的制文云:“朕新委元臣,綜厘重務,爰求弍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為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盡管這個制文是辭臣所作的,然贊語之大旨亦當出于順宗。
由此可見,順宗李誦是永貞政治改革運動的主導者,王叔文則是許多進步政治人物中一個出類拔萃的人才,順宗輔臣中的一個佼佼者。
其次,永貞政治改革運動主要打擊誰?
唐順宗即位后,針對唐德宗時代的腐敗政治,推行了許多有力的改革措施,諸如:召回被德宗貶黜的政治家,薦舉、訪擇“達于吏理,可使從政”的人才,一面安撫愿意服從中央的節度使,一面打擊有野心的藩鎮,悉罷鹽鐵使的進奉,貶斥京兆尹李實,釋放宮女和教坊女伎,禁除五坊小兒捕鳥雀等等,其中,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便是打擊宦官的勢力。擇其要者而言之:一,“詔停內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員官俸錢”。(此事未見于《順宗實錄》,載《冊府元龜》卷五○七邦記部“俸錄”)二,禁罷宮市。《順宗實錄》:“舊事宮中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官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于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名為宮市,而實奪之。”《新唐書·食貨志》:“有赍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估漿賣餅之家,皆撤肆塞門。”宮市弊政,直接受益者乃是宦官。可見,禁罷官市是打擊宦官勢力的重要措施。三,謀奪宦官兵權。《順宗實錄》:“(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檢校右仆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權,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為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為行軍司馬,專其事。”宦官專兵權,是德宗種下的禍根,順宗、叔文等深知其弊,因而果斷地采取了這個措施。王元美說:“而其所最要而最正者,用范希朝為神策行營節度使,而韓泰為司馬,奪宦官之兵權,而授之文武大臣。”(見《讀書記》卷三)王氏對此舉所作的“最要”、“最正”的評價,是極中肯綮的。
再次,永貞政治改革運動主要反對者是誰?
永貞政治改革運動觸及到宦官、藩鎮、貴族官僚集團的根本利益,因而他們瘋狂地勾結起來,先是惡毒地咒罵,繼之而來的是挾持順宗,擁立憲宗,貶斥二王,其勢洶洶。“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詆訶萬端,旁午抅扇,盡為敵仇。”(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最激烈的反對派還數宦黨。《舊唐書·王叔文傳》記載“內官俱文珍惡其(指王叔文)弄權,乃削去學士之職。”又:“初,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權為叔文所奪,中尉乃止諸鎮無以兵馬入。希朝、韓泰已至奉天,諸將不至,乃還。”改革措施時時遭到宦官的阻撓和破壞,接著,就出現了宦官們恣行脅迫順宗內禪,扶持憲宗登位的事件。這一件事,分兩步走:
第一步,七月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純勾當。
第二步,八月庚子,下詔云:“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勑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八月乙巳,皇帝即位于宣政殿。
內禪事,非出順宗自愿,乃是禁中、朝庭腐朽勢力勾結脅迫的結果,《順宗實錄》載此事云:
天下事皆專斷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為之內主,執誼行之于外。朋黨喧嘩,榮辱進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見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臯、裴垍(當為均)、嚴綬等箋表,而中官劉光奇(當為琦)、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啟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人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
這段文字,有些地方講了老實話,說明順宗內禪是宦官挾持、藩鎮脅迫的產物。有些地方,說的卻是假話,如“上固己厭倦萬機”、“惡叔文等”,掩蓋了宦官、藩鎮相互勾結、脅迫順宗的罪惡。事實上,順宗長期以來希圖改革弊政,豈能于推行新政之際“厭倦萬機”呢?順宗和王叔文等人相交十八載,情深誼長,配合默契,豈能“惡之”于一旦呢?這段史事,瞞不過后代史家的眼睛,王夫之曾為之發過議論,說:“憲宗儲位之定,雖出自鄭絪,而亦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諸內豎修奪兵之怨,以為誅逐諸人之地。”(見《讀通鑒論》卷二十五)真是一言破的。
綜上述三問題而觀之:順宗是永貞政治改革運動的主導者,革除宦官專權的弊政,是這場運動的重要目標,因此,政治改革必然遭致宦官的反對,順宗李誦必然遭到宦官的怨恨。王叔文等人是政治改革的具體執行者,固然成為宦黨的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宦官們心里很明白,王叔文等人是順宗起用的,因此,廢順宗、立憲宗,才是從根本上否定政治改革運動的重大決策。我們要研究順宗崩駕的疑案,這三個問題是必須首先弄清楚的。
四 斗爭的激化
憲宗既受宦官擁戴,即位后,自然竭力按照宦黨的要求行事,迅即打擊太上皇李誦信用過的人。首先,貶斥王叔文、王伾,憲宗《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參軍制》:“置馳驛發遣”,迫不及待地把他們兩人發送貶所。接著,貶逐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等人為遠州刺史。
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起驚人的事件。今存之《順宗實錄》對于這件事,只字不提。兩《唐書》和《資治通鑒》卻記錄了這個事件的有關情況。
《舊唐書·劉澭傳》:
授秦州刺史,以普潤為理。及順宗傳位,稱太上皇,有山人羅令則詣澭言異端數百言,皆廢立之事。澭立命系之,令則又云,某之黨多矣,約以德宗山陵時,伺便而動。澭械令則送京師,杖殺之,后錄功賜其額曰保義。
《新唐書·劉澭傳》:
憲宗立。方士羅令則詣澭營妄言廢立,以動澭。命系之,辭曰:吾之黨甚眾,公無囚我,約大行梓宮發兵,無不濟。澭械送闕下,殺之,錄功,號其軍曰保義。
《資治通鑒》卷二三六:
(永貞元年)冬十月,舒王誼薨。山人羅令則自長安如普潤,矯太上皇誥,征兵于秦州刺史劉澭,且說澭以廢立。澭執送長安,并其黨杖殺之。
上述史料,比較可信。宦官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曾把涉及他們利害的大量永貞時事強行刪削,但是,刪削總不能盡凈。而那些被他們遺留下來的史料,卻為我們探求歷史真相,提供了線索。羅令則游說劉澭的史料,諸史所載,互有異同,卻又互為補充。它們明白告訴我們,在永貞元年十月時,山人羅令則到劉澭處進行游說,有五點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矯稱太上皇誥;(二),向劉澭征兵;(三),說廢立之事;(四),聲稱其黨甚眾;(五),約于李適歸葬時行動(企按:應劭《風俗通義》云:“皇帝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其時李適廟謚未定,當以《新唐書》所記為是。)這個案件表明:以順宗、王叔文為一方的要求改革政治的人物和以憲宗、宦官為一方的貴族官僚集團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并沒有隨著憲宗登位而緩和,也并不因貶斥兩王、劉、柳而告終。相反,斗爭還在繼續,擁護順宗的大有人在,他們還在四出活動,力圖挽救殘局。因此,這個案件既是永貞時代矛盾激化的具體表現,更是日后宦黨殘酷戕害進步人物的導火線。我們只要排出一個時間表,就可以從中窺見其秘奧。
永貞元年
十一月壬申,貶韋執誼為崖州司馬。憲宗《貶韋執誼崖州司馬制》:“朕初臨萬邦,務于宏大,每存容恕,冀有悛心,而乃不顧憲章,敢行欺罔,宜投荒服,以儆無良。”
十一月,改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準、程異等七人為遠州司馬。改貶的原因,見《資治通鑒》卷二三六:“朝議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為刺史,貶之太輕。”
元和元年
正月,賜王叔文死。史書或云:“明年誅之”,或云“賜叔文死”。明年,即指元和元年。賜死日期,史載不明,筆者認為當在順宗崩駕之前后。
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
加重對王叔文、韋執誼、劉、柳等人的處置,是永貞元年十月羅令則案件促成的。李忠言、牛美人從此在史書上消失,當屬“某之黨多矣”而株連的。(兩人是被殺,還是遭貶斥,史書并未明言;在文學作品中,卻露出一些端倪。張國光同志在《今本〈順宗實錄〉非韓愈所作辨》一文中就認為柳宗元的《梁丘琚贊》是悼念李忠言之被殺害,可信;李賀《漢唐姬飲酒歌》借著對唐姬的贊美,似是歌頌牛美人,并暗示了她的去向,詳見下文“八”。)“矯太上皇誥”、“說廢立之事”,更是順宗遽死的原因。羅令則到秦州刺史劉澭處”說廢立之事”,約請劉澭發兵,這不僅威脅著憲宗的皇位,而且宦黨也將當作芟除的直接對象。因此,案發后,以俱文珍、劉光琦等人為代表的宦黨,在憲宗的支持下,必然采取一系列的嚴厲措施。于是,叔文命死,劉、柳等人遠斥,牛、李隔絕,李誦被幽閉在興慶宮,乃至最后被弒戮。
斗爭激化的結局,致使順宗慘遭不測。一張時間表,確實給人們以很多值得深思的啟示。
五 文學作品中的佐證(一)——李復言《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條
一手難以遮天。史書是官修的,固然可以憑借“王權”任意刪削史料,但歷史事實卻是無法改變的。宮闈雖秘,總得外傳,順宗崩駕的疑案,卻在同時代人的文學作品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用不同的方式,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來。中唐時代文人筆下涉及順宗崩駕的作品,有好幾篇,李復言的《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條,絕非孤文單證。這些文學作品,很值得我們認真加以研究。我們可以把它們和今存之史料,相互參證,互為補充,從而把那些已被宦官們刪削掉的歷史事實,或被封建史家歪曲掉的歷史真相,重新揭示出來。
陳寅恪、卞孝萱、章士釗諸人都認為李復言《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條,假傳奇以記唐代帝王被弒的事實,筆者贊同其說,不再贅述。另拈出兩點,補證此說。
(一) 李復言唯恐別人不明自己的文意,特地在行文中多次點明本文不是描寫奇誕古怪的鬼神故事,乃是表現人世間的“天子”死于非命。這些提示性的文字,分散各處,容易忽視,如果把它們集中在一起,用意十分顯明。如:
“王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測者也,辛(原為幸字,按上下文意,當為辛字)君能一觀。’”
“(臻)曰:‘固不識我,乃陰吏之迎駕者。’”
“將軍曰:‘升云之期,難違頃刻,上既命駕,何不遂行?’”
“秘不敢泄,更數月,方有攀髯之泣。”
文中一再點明這是“天子上仙”。“攀髯之泣”,用了《史記·封禪書》中的典故:“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后官從上者七十余人,龍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后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唐代詩人亦常用墮髯、號弓指帝王崩駕,如元稹《順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挽歌詞》:“號弓那獨切,曾感昔年招。”《憲宗章武孝皇帝挽歌詞》:“觸鱗曾在宥,偏哭墮髯前。”李復言作文妙在“卒章見義”,文末的“秘不敢泄,更數月,方有攀髯之泣”,畫龍點睛地說明唐宮中的這一場弒戮,是秘密地進行的,隔了一段時間,才公開發喪。
(二) 李復言即李諒,排行第六,與白居易同年中舉,極友好,常有詩歌往還。(說見卞孝萱《<續玄怪錄>作者及寫作年代探索》,載《江海學刊》總第三十二期)永貞元年三月,他受王叔文的賞識,任命為度支鹽鐵使巡官,五月,因王叔文的推薦,改任拾遺,直到元和元年春,尚在任上。卞孝萱同志引白居易詩,以為李諒于永貞元年春已任拾遺之職,時序有誤。按:王叔文于貞元二十一年(即永貞元年)三月丙戌,詔充度支鹽鐵副使,于永貞元年五月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柳宗元作《為王戶部薦李諒表》:“竊見新授某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強以有禮,敏而甚文,求之后來,略無其比。臣自任度支等副使,以諒為巡官,未及薦聞。至某月日,荊南奏官敕下赴本道。諒實國器,合在朝行,臣之所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冀它日公卿之任。”則李諒之任拾遺職,當在五月辛卯之后。然其時花事已過,白居易招“李六拾遺”至華陽觀賞花飲酒,是不可能的事。白居易于永貞元年任校書郎,直到元和元年冬調任周至縣尉以前,曾在華陽觀居住過。《自城東至以詩代書戲招李六拾遺、崔二十六先輩》:“應過唐昌玉蕊后,猶當崇敬牡丹時,暫游還憶崔先輩,欲醉先邀李拾遺。”《華陽觀桃花時招李六拾遺飲》:“華陽觀里桃花發,把酒看花心自知。”這兩首詩告訴人們:白居易于華陽觀招飲李諒,時當元和元年春,其時李諒還在京師任拾遺職。自此以后到元和六年任彭城宰以前,李諒的行蹤還不很清楚。唯《續玄怪錄》卷四“定婚店”云:“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歧,求婚必無成而畏。元和二年,將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見議者……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按照《續玄怪錄》的慣例,李諒往往于故事結尾處,記下自己的官職和行蹤,《定婚店》一文中題其店的“宋城宰”,或即李諒,這與白居易《李諒除泗州刺史……制》所云的“三宰劇縣”亦合。
從以上行蹤可以看出,李諒在永貞時代受知于王叔文,先任度支鹽鐵使巡官,后改任拾遺,直到元和元年春,尚在長安,后因坐叔文黨,出為地方官。元和二年,任宋城宰,六年,任彭城宰。在長安時期,曾風聞過順宗崩駕的消息,因而隔了一段時間(四、五年),借用傳奇形式,在迷離恍惚的情節中,煞費苦心地把這個歷史事件記錄下來。
六 文學作品中的佐證(二)——柳宗元《晉文公問守原議》
世綵堂本《柳河東集·晉文公問守原議》題下注云:
唐自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公問守原于寺人尤甚。公此議雖曰論晉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宦者之禍。逮憲宗元和十五年,而陳弘志之亂作,公之先見至是驗矣。
這段注文,鉤玄提要,確是道出了柳宗元《晉文公問守原議》的題旨。至于“公之先見至是驗矣”一語,卻很不的當。柳宗元這篇文章,寫于被竄逐南隅之后;他卒于元和十四年,當然是見不到陳弘志作亂事。《晉文公問守原議》并不是預言性的言論,乃是追言德宗、憲宗過失的文字,寓意深遠:
柳宗元云:“不宜謀及媟近”,意在追責德宗、憲宗謀及蝶近、委政宦官的政治錯誤。
柳宗元云:晉文公的行動,影響到后代,致使漢代出現“弘石得以殺望之”,意在追數德宗、憲宗寵信宦官的錯誤。永貞時,宦官領神策兵,掌軍權,釀成王叔文被殺、韋執誼被貶的惡果,這與“弘石得以殺望之”有什么兩樣呢?王鳴盛說過:“假令叔文計得行,則左右神策所統之內外八鎮兵自屬于六軍,天子可自命將帥,而宰相得以調度,亂何由生邪?”(見《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王氏的推想和柳文的用意,是一脈相承的,都指出宦官之亂的根源在于君王的縱容。
柳宗元云:“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這是文章結尾的兩句話,很不好理解。《春秋》許、趙之義,究竟是什么?章士劍《柳文指要》卷四云:“義猶有進,《左傳》宣公二年,趙穿弒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盾,宣子名也。”“又,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實。之二事者,皆赫然弒逆案也。”章氏并沒有對《春秋》原義加以探究,僅引述《左傳》的文字,直接指稱這二件事為逆案,并由此而涉想到永貞逆案,這顯然是誤解了《春秋》原義,誤解了柳宗元文意的。按《春秋》曰:“(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又云:“(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孔穎達疏曰:“經書趙盾弒君,而傳云靈公不君,又以明于例,此弒宜稱君也。弒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許止身為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弒。二者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為教之遠防也。”由此可知,《春秋》記趙盾、許世子止弒其君二事,并非“赫然弒逆案”;《春秋》許、趙之義,乃是良史秉筆直書,以深責執政之臣,垂教化于后世。那么,柳宗元為什么要在本文結尾提到這二件事呢?世彩堂本《柳河東集》的注者,固然看到宦官作亂的一面,但是,他們并不理解《春秋》許、趙之義,也未懂得柳宗元寫作本文時運用《春秋》大義的意圖。其實,柳宗元在這里反用了《春秋》許、趙之義,隱而不露地揭示中唐時代缺乏“良史”,沒有人敢于把永貞時代“君不君”、“臣不臣”的逆亂事件秉筆直書在史冊中。而造成“弒君”逆亂事件的主兇,恰恰正是那些“媟近”者,為此,柳宗元要在《晉文公問守原議》一文的結尾,著明“晉君之罪”,亦即著明釀成宦者之禍的唐德宗、憲宗的罪過。柳宗元于永貞時,參與樞機,親躬密近,后來雖遭貶斥,與友朋還時有往還,因此對宮禁秘事,時有所聞。然而憲宗登基,宦官專權,天下鉗口,柳宗元不能明言,因而藉《春秋》大義,痛心疾首地點出永貞時臣弒君、子弒父的現實,慨嘆“良史”之不存。
七 文學作品中的佐證(三)——劉禹錫《子劉子自傳》
劉禹錫遭貶以后,為避免政敵的讒毀,語多諱避。他在七十一歲時,多病,因自為銘傳,略述平生歷履出處,云:“東宮即皇帝位。是時太上久寢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能召對。宮掖事秘,而建桓立順,功歸貴臣。于是叔文首貶渝州,后命終死。”臨近絕命,他可以說說心里話,因此,《子劉子自傳》一文,記事近真,評騭公允,是我們研究永貞時事的寶貴資料。
前人對于“宮掖事秘”這段文字,往往著眼于“內禪”事,但詳按史書,可知劉禹錫運用“建桓立順”的歷史事件是有深意的。
《后漢書·梁冀傳》:
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
《后漢書·質帝紀》:
(本初元年)閏月甲申,大將軍梁冀潛行鴆弒,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九歲。
“建桓”即指此,“生殺予奪”之權,操之于外戚梁冀之手。
《后漢書·順帝紀》 :
(延光四年)十一月丁巳,京師及十六郡國地震。是夜,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于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年十一。
“立順”即指此,廢立之權,全由宦官操縱。
綜觀這二個歷史事件,包含著這樣幾種意義:一,弄權者任意廢立皇帝;二,弒前帝,立后帝,三,弄權者為宦官和貴戚集團。“建桓立順”既然出于陰謀和暴力,可見劉禹錫運用這個歷史典故,就暗示著所謂的順宗“內禪”事件的背后有陰謀。這一場陰謀,既包括宦官勾結貴族官僚集團脅迫順宗內禪,也包括這些人弒戮順宗的事實,否則,劉禹錫運用這個歷史典故就很不確切。聯系上下文意看,劉禹錫是把“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和“于是叔文首貶渝州,后命終死”,當作因果關系來表現的,說明王叔文“首貶渝州”是脅迫順宗內禪的結果,王叔文“后命終死”是和順宗被害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劉禹錫的《子劉子自傳》,也為我們探索順宗崩駕疑案提供了重要線索。
八 文學作品中的佐證(四)——李賀《漢唐姬飲酒歌》
李長吉歌詩中,有一首《漢唐姬飲酒歌》頗費解。我們如果把它和順宗崩駕疑案聯系起來考察,則《漢唐姬飲酒歌》一詩的題旨,可以迎刃而解;同時,又可以為疑案之平質提供佐證。
《漢唐姬飲酒歌》詠漢代董卓廢弒少帝的故事。李賀決非僅僅在發思古之幽情,實際上是他借作詩以攄寫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產生的憤懣感情。詳考李賀一生,僅歷二帝崩駕。德宗于貞元二十一年病逝,史有明文;順宗于元和元年正月突然“崩駕”,死因不明。上文,我們已經根據今存之史料、近代學者的研究成果,推斷出順宗死于非命。那末,李賀《漢唐姬飲酒歌》一詩,也正好為我們提供順宗崩駕的證據,盡管這種佐證是通過詩歌藝術形象表現出來的。試看:
“御服沾霜露,天衢長蓁棘。”
這兩句詩,用的是漢代伍被諫淮南王的話:“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沾衣也。”(見《漢書、伍被傳》)御服沾露,喻帝位已失;天衢長棘,喻國是多艱。李賀時代,只有唐順宗在群兇脅迫下進行“內禪”,被幽居在興慶宮咸寧殿時,才過著這種“御服沾霜露,天衢長蓁棘”的生活。
仗劍明秋水,兇威屢脅逼。
強梟噬母心,犇厲索人魄。
這是一幅董卓、李儒威逼、殺害漢少帝的圖畫。然而,這里有一個問題不好解釋。按《說文解字》:“梟,不孝鳥是也。”張華《禽經注》:“梟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啄母目翔去也。”董卓、李儒威逼少帝,用“犇厲索人魄”形容之,很恰當;然而用“強梟噬母心”表現董、李的罪行,卻不合情理。筆者往日讀長吉詩至此,曾記下“必別有所指”的話。所指為何?只得付諸闕如,存疑俟考。現在,聯系永貞時事,重讀此詩時,才恍然大悟。李賀在詩里,確是借詠董卓廢弒少帝事,喻指當代生活。四句詩,分明是一幅憲宗、宦官和貴族官僚集團勾結起來威逼、殺害順宗的圖畫。作如是觀,《漢唐姬飲酒歌》的詩意,就豁然貫通。正因為憲宗李純有負于人子之情,很怕人觸及他的隱私。《舊唐書·崔群傳》載:“群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加孝德二字。群曰:‘有睿圣則孝德在其中矣。’竟為鎛所構,憲宗不樂,出為湖南觀察都團練使。”將這段史料和李賀詩“強梟噬母心,犇厲索人魄”共讀,難道還不能悟出一些道理來嗎?
“金隱秋塵姿,無人為帶飾。
玉堂歌聲寢,芳林煙樹隔。”
“妾身晝團團,君魂夜寂寂。
蛾眉自覺長,頸粉誰憐白?”
這一位被喻作“唐姬”的女子是誰?她就是唐順宗即位后進行政治改革的得力助手牛美人。
《新唐書·鄭絪傳》:
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絪草立太子詔,絪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頷乃定。
《新唐書·劉貞亮傳》:
會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后下中書。
李肇《國史補》: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
這個女子后來命運如何?史載不明。根據永貞時斗爭激化的政治形勢推測,她在順宗被幽閉、殺害以后,失去政治上的倚托,宦黨一定不會放過她,定象王叔文等歷史人物一樣,遭罹厄難。李賀通過歷史典故,塑造了唐姬的藝術形象,表達了詩人對牛美人這個歷史人物的同情和贊頌。
九 結語
探討反映順宗時事的文學作品的意義,在于闡明這些作品的題旨、作者的用意和匠心,為順宗崩駕質疑提供線索,證成李誦死于非命的觀點。而探討順宗崩駕疑案的史學意義,在于深入揭示唐代宦官之禍的嚴重性。歷代史家都以為唐代帝王之廢立,受制于宦官,當始于穆宗。《新唐書·僖宗紀贊》首創其說,云:“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司馬光說得更為具體:“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歷狎暱群小,劉克明與蘇佐明為叛。其后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晦為之魁杰,至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見《資治通鑒》卷二六三)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采取此說,云:“宦官自從殺唐憲宗、立唐穆宗以后,對皇帝有廢立和生殺的權力。”撥開順宗崩駕的迷霧,可見唐代宦官對皇帝有廢置之權,早從廢弒順宗、翊戴憲宗就開始了的,種下這種惡果的人,當然是唐德宗。宦官握兵權,干預朝政,勾結地方藩鎮,這正是中唐以后政治濁亂、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永貞時代政治改革慘遭失敗,進步政治人物慘遭貶謫、殺戮,順宗的突然崩駕等一系列歷史事件,無一例外,都是由宦官專權所直接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