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的現身:翟永明的土撥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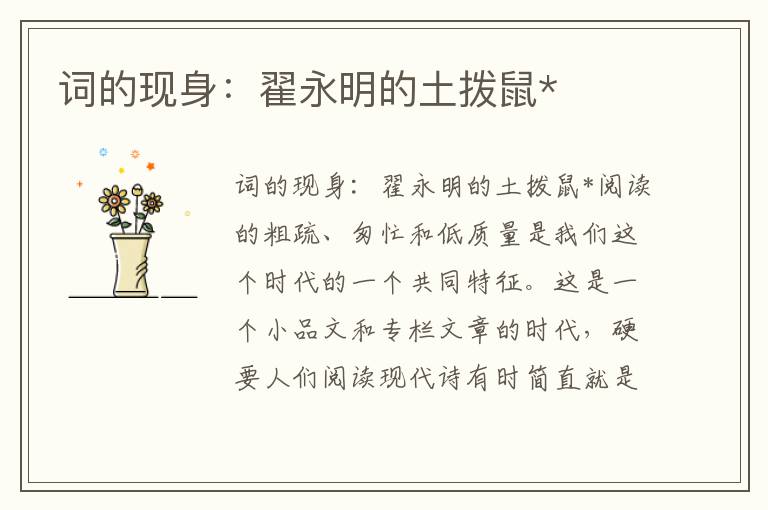
詞的現身:翟永明的土撥鼠*
閱讀的粗疏、匆忙和低質量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共同特征。這是一個小品文和專欄文章的時代,硬要人們閱讀現代詩有時簡直就是一種懲罰。最近這幾年的趨勢表明,無論將詩歌寫作理解為詞的縮削還是詞的擴張,詩人所使用的都是少數人的語言(minority language),這種語言在定義上就包括了對公眾閱讀和消費性閱讀的斷然抵制。所以詩人不必指望自己的作品擁有成千上萬的讀者。問題是同時代的詩人相互之間閱讀作品,大抵也同樣是粗疏、匆忙和低質量的,往往是初讀之后憑印象(我們都知道詩人的印象是由他自己的寫作積習產生的)表明一下喜歡或不喜歡,絕少加以深究。在這樣一種閱讀風尚中,福樓拜所神往的“詞的奇境”要想得以現身,可能性極小。
現身正是翟永明《土撥鼠》這首詩著力處理的一個關于“詞的奇境”的主題。我和翟永明交情甚篤,所以打算在閱讀之前先引用一些私人性質的背景材料,意在把這首詩的前寫作過程也劃入閱讀的括弧之內。《土撥鼠》發表在1992年第1期《今天》上,不過我早在1989年冬天就讀到了這首詩的手稿。我幾乎是未加思索地立即喜歡上了這首詩,但閱讀似乎也就到喜歡為止——在正常情況下,喜歡一首詩就意味著取得了不必重讀的合法權利。直到今年4月我閱讀裝幀精美的翟永明個人詩集時,才又想起了《土撥鼠》。原因很簡單:我在這本篇幅達267頁的詩集里找不到這首詩。這讓我納悶,因為我知道翟永明本人也很偏愛這首詩。不久我收到她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談到《土撥鼠》是怎樣寫出來的:“說到‘詩外’起因,那是我和何多苓剛結婚不久時寫的,那段日子他經常唱一首歌,即海涅的一首詩:‘為了生活我到處流浪,把土撥鼠帶在身旁。’我非常喜歡,……土撥鼠給了我寫作沖動,可以說我是一揮而就寫出了這首詩。”
我通常信賴的是那種強調距離的、有節制的、不透明的閱讀,亦即作者不在場的零度閱讀。我在這里引用私人性質的詩外材料,無疑會對我所信賴的閱讀行為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擾。但我認為這種干擾對于閱讀《土撥鼠》這首詩也許是必要的。并不是每一首詩都適合零度閱讀。
一首詩加另一首詩是我的伎倆
一個人加一個動物
將造就一片快速的流浪
起首第一段就出現了兩次“一加一”,仿佛是在暗示,作者沒有采取零度立場來寫作這首詩。那么,存在著一個里奇(Adrienne Rich)式的女性主義寫作立場嗎?里奇曾經說過,她自身“分裂成寫詩的女孩,一個界定自己在寫詩的女孩,和一個經由她與男性的關系而界定的女孩。”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將里奇的這種分裂性質的個人處境解釋為更廣泛的女性寫作處境,解釋為一個歷史寓言,這就是:在女性主義成熟之前,女人的寫作“沒有能力停止借由她們與男性的關系來界定自己的這種處境”。我們在早前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以及西爾維亞·普拉斯(Sylvia Plath)的寫作生涯中都可以清晰地辨認出上述處境:女性詩人的自我描述越是逼真、越是強烈、越是感人至深,就越是被整體的分裂力量所拆解和撕碎。女人的自我描述無法在人性的完整光輝中單獨結蒂,因為語言游戲是由男性控制的,生活中男性的狀況(男性的多余或欠缺)是語言游戲中的自變數,而女性的描述則被迫成為因變數。也許正是這種自變數與因變數的相互重疊,形成了新歷史主義者稱之為“厚描”(thick description)的“無法忘卻的語言”,作為對女性自我描述中那深淵般的“無言”的一種補償。女性分離主義的立場正是由此發展出來的,麥金倫(Catharine Mackinnon)站在這一立場上說:“我想為女人提出一個尚待實踐的角色,我所根據的是一個未被抑止的聲音所可能訴說的,未曾被聽過的話語。”
我之所以在這里就女性寫作立場做出一番回顧,一方面是由于我強烈地感受到了女性身份確認問題所包含的角色焦慮(role anxiety)和角色反抗(role resistance),我的意思是,假如我讀到的詩是一個女人寫的,我恐怕就不得不首先澄清某些東西,而這種澄清在我閱讀一個男性詩人的作品時是壓根兒不會碰到的。對此,法國當代女作家埃萊娜·奚克蘇(Hélène Cixous)的感受相當沉痛:“當有人向你談起女人,你總得有所回答而且就像在對一項指控做出回答一樣。”另一方面,翟永明在寫作《土撥鼠》之前寫過不少影響極其廣泛的女性詩作(例如組詩《女人》),這種情況我們在閱讀《土撥鼠》之前必須加以考慮。
但這并不意味著《土撥鼠》這首詩里面存在一個確切無疑的、不妥協的女性主義寫作立場。相反,我認為《土撥鼠》表明翟永明的寫作正在經歷從歷史場景到個人潛意識場景的微妙變化(這與奚克蘇近年來所經歷的變化恰好形成反向對照)。從表面上看,《土撥鼠》所處理的素材與流行的女性詩歌并無多大差別,詩中充斥著奔突的激情、流浪、情人的痙攣、夢境、寂寞、受傷、訣別這樣的日常用語。但我注意到,這些流行的、日常的詞既沒有被導向高度神經質的自我描述,也沒有費力地去辨認伍爾夫(A.V.Woolf)式的“主要敘述者”的女性特定身份。換句話說,日常的詞即使是在非日常的氣氛中也沒有采取圣詞(The Word)的立場,這是由于作者審慎地將敘述聲音處理為他者語言,并在他者中現身,從而回避了女性詩人特有的角色焦慮。
一首詩加另一首詩是我的伎倆
“一首詩”可以理解為正在書寫的某一首詩(在此處是《土撥鼠》),寫作從一開始就帶有自相指涉的性質。“另一首詩”顯然是指海涅的那首有關土撥鼠的詩,翟永明在寫給我的信中提到了它(看來私人材料有時確實能派上用場,但我必須趕緊申明:我對這些材料的引用到此為止)。我認為海涅的詩在這里其實是不純的和變化的,因為對于翟永明來說,詞在觸及她時不僅是變成了歌曲的詞,而且是那種變成了中文的德文。這里或許發生了某種意味深長的文本顛覆,如果我們將“加”字所起的作用考慮進來,并對用法突兀的“伎倆”一詞稍加留意的話。當然,我所說的文本顛覆僅限于詞的范圍,不涉及身份識別問題。埃萊娜·奚克蘇在閱讀另一位女作家的出色作品時曾說:“我發現了一個卡夫卡,這個卡夫卡是女人。”但我以為翟永明被海涅觸動時未必想在海涅身上認出一個女海涅來。考慮到海涅是個德國詩人,我還要加上一句,翟永明也不會因為海涅的觸動而產生種族認同危機。角色焦慮在《土撥鼠》一詩中并不存在。讀者所看到的只是一個詩人觸及另一個詩人,一首詩加另一首詩。不是女人借由與男人的關系現身,也不是中國人在異國幻象中現身,而是詞的現身。
詞的現身是一個令人神往的詩歌夢想。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將詞的現身視為最高虛構真實,葉芝將其看作宇宙的舞蹈,濟慈(JohnKeats)則把它理解為美與真的完全融合。但是詞的現身是并無實體的現身,所以必須給詞一個身體或一個物,使詞的現身可以被指出、被辨識、被印證。于是,我們在史蒂文斯的作品中讀到了田納西州的一只壇子,從濟慈的頌歌中讀到了夜鶯和希臘古甕,并且從葉芝的詩作讀到了他對舞蹈與舞中人做出的區分。引人深思的是,葉芝對兩者做出的區分是以反問方式提出來的,含有不可區分的強有力暗示。保羅·德曼(PauldeMan)敏銳地嗅到了其中純形式的、方法論的意蘊,他進而把詞的現身理解為閱讀的基本秘密。
在翟永明的《土撥鼠》中,我們所看到的詞的現身是由土撥鼠代現的。撇開美學風格方面的種種差異不論,僅就符號的替代功能而言,翟永明筆下的土撥鼠與葉芝《在學童中間》最后一小節的舞中人頗為相似:兩者所代現的都是生命中難以顯現的非存有(non-being)。但我認為指出兩者之間深刻的相異之處也許更能說明問題。葉芝刻意將舞中人處理為面具化的、幾乎沒有細節的“純身體”,用以承受宇宙的神秘律動。而翟永明借由土撥鼠所代現的那種生命中難以呈現的境況,則是關于個人生活和個人寫作的。這意味著,土撥鼠同時指涉詞的現身與愛的現身。而且,土撥鼠來自另一首詩,也可以說來自一支歌(來自何多苓的優雅嗓子),屬于敘述聲音中的他者聲音,其現身使作者的自我描述聲音一下子變得無名無姓、面目全非,難以被單獨辨認和傾聽。這也許正是作者(即詩中的主要敘述者)想要面對的一種局面:主要敘述者可以用“他者語言”來敘述,也可以將自我中隱而不顯的部分交給這個“他者”代現,從而完成自我形塑。使人迷惑的是,土撥鼠并非一個意象、一個象征物、一個隱喻或一個寓言,它僅僅是現身(準確地說是代為現身)。它來了,但無人知道它想把主要敘述者帶到何處去。
一個人加一個動物
將造就一片快速的流浪
“加”在這首詩中所起的反常作用一波三折,值得細細琢磨。不妨使閱讀停下來,對此做出一番外科手術式的拆解分析。首先,“加”的邏輯含義被取消了。這里的“一個人加一個動物”,其結果很可能會少于獨處狀態中的一個人或一個動物,因為存在著人性與動物性相互替換、相互剝奪的可能性。這是否在暗示,兩者相加是一個減少過程?詞減少了土撥鼠,而土撥鼠的現身也并沒有使一個人或一個詞變得更多。也許我們經由對“加”的反向解碼已經觸及了《土撥鼠》這首詩的根本秘密:作者在詞與感官、形式與經驗、自我與他者的相加過程中得到的并非各方之“和”,而是一種難以解釋的“差”。顯而易見,土撥鼠所代現的正是生命本身的某種深度欠缺,各方相加得出的“差”。土撥鼠在翟永明的筆下處于無可棲居的流浪和逃亡狀態,大地上沒有它的居所。而我們都知道,人類對生命的確認總是聯系著對居住形式的關懷,城市、村莊和家庭無一不是因為這種關懷才得以形成的。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引用詩人荷爾德林(Friedrich H?lderlin)的思想,指出語言是人在大地上的居所。換言之,即使是在言說和書寫行為中,人的生存也不是無場所的,“而是被雙重鑲進本文作為一個具體的境遇”。可以說,沒有居所的生存狀態是“非存有”。
重新回到對“加”的分析,我們也許會相當自然地將這個詞與“家”諧音這一點考慮進來。這也許是巧合,也許是刻意為之,我想作者大概潛意識中一直惦記著土撥鼠無處棲居這一傷感的事實。無論如何,現在“一個人加一個動物”這句詩可以被讀成:一個人,家,一個動物。只要我們愿意停頓,土撥鼠就有一個能被讀出和聽到的聲音的“家”。盡管作者在第二節中指出:
這首詩寫我們的逃亡
但作者真正關切的事情是土撥鼠于何處棲居。尋找棲身之地這一隱秘主題被條分縷析地暗中織入了整首詩的布局。在第一小節中,我們發現土撥鼠的棲身之地是通過一個詞的諧音(加/家)來暗示的。在第二節詩中,棲身之地似乎與一幅畫有關(不要忘了何多苓是畫家):
午夜的腳掌
迎風跑過的線條
第三節出現了夢境:
秋冬的環境夢里有土撥鼠
在第四節,即全詩的最后一節中,土撥鼠在“月光下”現身,“整個身體變白”。作者的結尾兩行詩點明土撥鼠的真正棲身之地是“平原”。
它來自平原
勝過一切虛構的語言
隨著尋找棲身之地這一主題的層層遞進,土撥鼠的流浪生涯也經歷了從詞的現身到愛的現身、從接近人類到獨自離去的變遷過程。
我和它如此接近
它滿懷的黑夜滿載憂患
沖破我一次次的手稿
作者深知土撥鼠無論作為詞之代現,自我中的他者之代現,還是作為生命中的非存有之代現,都是同樣珍貴的。因此作者想要用聲音、畫面、文本和夢境來挽留它。但土撥鼠是留不住的,“它來自平原”。它作為一個迷人的代現寄居在詞的奇境里,但最終卻從讀音、線條和文本逃了出來,從純形式、從虛構的語言逃回到它自己的真實身體。
這首詩敘述它蜂擁的毛
向遠方發出脈脈的真情
“蜂擁的毛”顯然是一種修辭用法上的故意夸張,意在強調身體的純生理特性。看來代替詞語現身已經衍變為身體本身的顯現。應該如何對待這個身體呢?詞曾經描述了這個身體,但詞不能變成這個身體。作者告訴我們:這是身體世界向詞的世界訣別的時刻。
這些是無價的:
它枯干的眼睛記住我
它瘦小的嘴在訣別時
發出忠實的號叫
“枯干的眼睛”避開了淚水和墨水。“號叫”當然是土撥鼠自己的聲音,但身體的聲音在從詞的聲音中分離出來后,是否如作者所說仍然“忠實”于詞的世界,這個問題有其復雜的一面。借由詞的現身,我們看到了各種各樣的身體:布萊克的老虎,濟慈的夜鶯,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y)的“綠色的朱頂雀”,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的鷹,以及我們在《土撥鼠》這首詩中讀到的翟永明的土撥鼠。詩人們為自己所創造的異類身體發明了一種語言,但這些身體卻拒絕說這種語言。因為身體的世界“現在構成了一種真正的自然,這個自然在說著話,在發展著一種將作家排除在外的活生生的語言”。
閱讀行為同樣有可能將作者完全排除在外。當翟永明試著用土撥鼠的“他者語言”來敘述自我時,她感覺到這個作者正在“離我而去”,如果沒有完全剝奪自我描述的聲音的話,也肯定會使之減少。寫作就是減少自我,即使整個世界與這個自我相加也是徒勞的。如果容我把前面提到的關于“加”的外科手術式拆解分析推向極端的話,“加”甚至不是一個詞或一種讀音,而是一個數學符號:+。但前面的討論已經表明這一符號難以執行正常的數學功能(它不表示一個增多過程),所以我們不得不從宗教喻指的角度去看待它:一個十字架。這與土撥鼠所代現的生命中的非存有構成了“可怕的對稱”:重與輕,死與愛,定在與流散。
在極端的意義上,上述拆解分析似乎還可以進行下去。十字架可以分解成“一”和“丨”。這一“越來越少”的拆解分析過程如果想要達到“少到不能再少”的程度,就必須逼出一個“〇”來。土撥鼠從廣義上講屬于穴居動物,因此,考察這首詩中的“洞穴意象”或許是合情合理的——洞穴也就是“〇”。我們很快就在詞的世界中發現了它:
它滿懷的黑夜滿載憂患
沖破我一次次的手稿
但要在身體世界中找到洞穴意象則不那么容易,除非我們將閱讀和討論引向性別政治的領域,并且武斷地認定土撥鼠有一個女性身體,然后再在普拉斯的一句詩“你的身體傷害我就像世界傷害著上帝”的引領下去讀《土撥鼠》中的兩行詩:
小小的可人的東西
在愛情中容易受傷
傷口在這里有可能被當作一種性別政治的特權,將身體世界的洞穴意義呼喚出來。但是下面兩行詩對這種讀法則提出了一個反證:
我指的是骨頭里奔突的激情
能否把它全身隆起?
這兩行詩所呈現出的凸起,可以很方便與德里達的“陽物理體中心論”(phallogocentrism)聯系起來,發展出男性身體的視域。我們甚至可以將上述兩類相互否定的讀法“加”起來,斷言土撥鼠有一個男女同體的變性身體。
夠了!盡管我已經提到這里的閱讀和討論是完全排除了作者的,但仍然太過分了,顯得像是在缺席謀害作者。當然,我可以為上述讀法(我稱之為外科手術式拆解分析法)找出足夠的理論依據。例如,我可以引用史皮瓦克(G.C.spivak)的一段話來說明我為什么要從拆解一個詞入手,建構起某一種閱讀立場(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正是我本人回避的立場)。史皮瓦克的這段話是:
……如果遇到一個詞,似乎包含了不能解決的矛盾,而且由于是一個詞,有時被用來起這種作用,有時被用來起那種作用,從而表明缺乏一種統一的意義,這時我們就要琢磨這個詞。……我們要追尋它深入文本中,發現文本不再作為一個隱蔽的結構,而是在揭示其自我超越性、其不可決定性。
我不過是盯住了“加”這個詞進行琢磨。無論當代理論多么富于啟示性,它仍然含有暴力的成分。常常是理論想把作品讀成什么,作品就似乎是什么。比方說,我想從《土撥鼠》這首詩中讀出世俗政治的影子世界,我就找出詩中的“逃亡”一詞施行外科手術;假如我想讀到多角戀的隱私故事,只需從“情人的痙攣”或“兒子”下手。
也許這就是閱讀的瘋狂。從中我看到的是詞語世界的分裂,而且是閱讀和寫作共同參與的分裂。前面提到過女性作家在借由與男性的關系界定自我時感受到自我描述的分裂。翟永明避開了這種分裂,但她在土撥鼠代現的“詞的奇境”中經歷了更真實的分裂。我能充分理解她的處境,她的深刻的無力感:在土撥鼠的世界里,她的自我敘述縱然避開了性別政治的分裂,但必須承受詞的分裂。我想我們大家都會深感無力。詞現身之后歸于分裂,人性的完整光輝則被“別的聲音”和“別的身體”帶到了“詞的他方世界”。我很慶幸在那里種族、階級、性別和國籍等方面的劃界行為不起作用。說到底,我們不過是一群詞的朝圣者,迷途者。
我樂于看到翟永明的土撥鼠在詞的他方世界再度現身。正如我樂于看到威廉·布萊克的老虎在博爾赫斯的詩篇中現身。
*土撥鼠
一首詩加另一首詩是我的伎倆
一個人加一個動物
將造就一片快速的流浪
我指的是骨頭里奔突的激情
能否把它全身隆起?
午夜的腳掌
迎風跑過的線條
這首詩寫我們的逃亡
如同一筆舊賬
這首詩寫一個小小的傳說
意味著情人的痙攣
小小的可人的東西
把眼光放得很遠
寫一個兒子在布置
秋冬的環境夢里有土撥鼠
一個清貧者
和它雙手操持的寂寞
我和它如此接近
它滿懷的黑夜滿載憂患
沖破我一次次的手稿
小小的可人的東西
在愛情中容易受傷
它跟著我在月光下
整個身體變白
這首詩敘述它蜂擁的毛
向遠方發出脈脈的真情
這些是無價的:
它枯干的眼睛記住我
它瘦小的嘴在訣別時
發出忠實的號叫
這是一首行吟的詩
關于土撥鼠
它來自平原
勝過一切虛構的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