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dāng)代詩的升華及其限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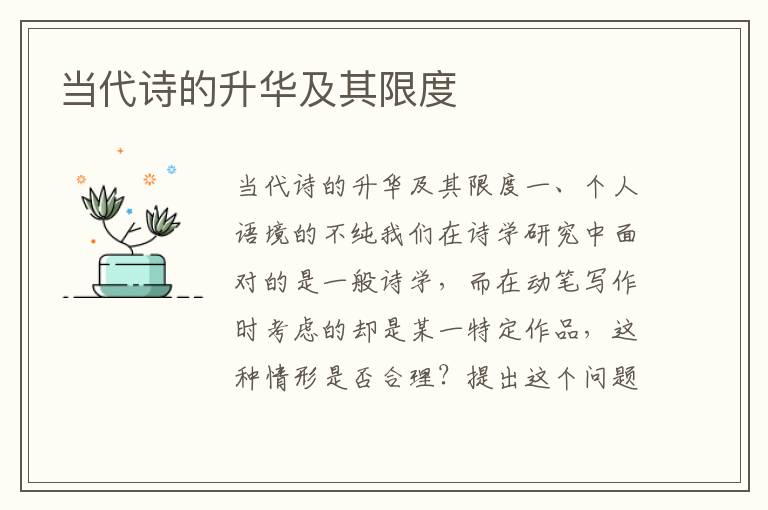
當(dāng)代詩的升華及其限度
一、個(gè)人語境的不純
我們?cè)谠妼W(xué)研究中面對(duì)的是一般詩學(xué),而在動(dòng)筆寫作時(shí)考慮的卻是某一特定作品,這種情形是否合理?提出這個(gè)問題,部分是由于在當(dāng)今漢語詩界一個(gè)人既寫詩又從事詩學(xué)批評(píng)的情況似乎已相當(dāng)普遍,部分則是考慮到有時(shí)我們對(duì)如何理解一個(gè)詞感到?jīng)]有多少把握——很明顯,對(duì)于公共理解、一般詩學(xué)和不同的特定作品,有時(shí)一個(gè)詞表達(dá)了迥然不同的意義。這看上去像是一個(gè)技術(shù)性的問題,但其中所包含的困惑卻是難以回避的。我想這里首先有一個(gè)語境問題。一般詩學(xué)所面對(duì)的是由交叉見解所構(gòu)成的具有可公度性(commensurability)的共識(shí)語境,而在某一特定文本中起作用的則主要是個(gè)人語境。也許對(duì)個(gè)人語境起源的不純加以質(zhì)疑是必要的,因?yàn)檫@一質(zhì)疑通常會(huì)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個(gè)人生存的特殊處境和深度經(jīng)驗(yàn),在其中,詞與物的關(guān)系所呈現(xiàn)出來的直接真實(shí)往往帶有令人不安的單純性質(zhì)。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yàn)閱渭儽旧碛锌赡芫禄優(yōu)楦R艋蜞l(xiāng)愁的袖珍形式,亦即一種由集體記憶加以維系的個(gè)人記憶的替代品;也有可能因制度語境的壓抑和扭曲而發(fā)展成為真正的噩夢(mèng)。英國作家赫胥黎(A.L.Huxley)在《美妙的新世界》一書中描寫的一個(gè)場景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一間陽光明媚的房子里擺滿接通電源的鮮花,一群孩子被帶進(jìn)來后,人人都本能地?fù)湎蝓r花,而電閘就在孩子們的手碰到鮮花的一剎那拉下。這種情形重復(fù)一千次后,鮮花與電流在概念上就緊緊黏合在一起:這不僅僅是事實(shí)的簡單呈現(xiàn),或噬咬人心的痛楚經(jīng)驗(yàn),也是一種具有固定含義的“反常的常識(shí)”。換句話說,鮮花與電擊的聯(lián)系既是物與物之間的聯(lián)系,又是詞與物、詞與詞的聯(lián)系,未知世界與已知世界的聯(lián)系。由于它已內(nèi)在化為個(gè)人語境,無疑將作為修辭的噩夢(mèng)在孩子們的一生中起作用。
這當(dāng)然是反常語境迫使正常語境產(chǎn)生變形的一個(gè)極端例子,但它有助于說明個(gè)人語境的不純。詞與物的初始聯(lián)系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單純,就其起源而言早已布滿了外在世界所施加的陰影、暴力、陷阱。對(duì)我們這代人來說,只要提到像“麻雀”這類詞在五六十年代意味著什么就足夠了。麻雀每年吃掉多少糧食的統(tǒng)計(jì)數(shù)字一經(jīng)發(fā)表,“麻雀”一詞在我們成長時(shí)期的個(gè)人語境中就成了“天敵”的同義詞,為此不惜發(fā)動(dòng)一場曠日持久的麻雀戰(zhàn)爭,與其說麻雀屬于鳥類,不如說它屬于鼠類。必須指出的是,這種米勒(J.Hillis Miller)所說的“按事先規(guī)定好的神學(xué)假定”去理解一個(gè)詞的反常途徑,不僅指向世俗政治和現(xiàn)實(shí)人生場景,而且指向精神和心理的領(lǐng)域,構(gòu)成了善惡對(duì)立的二元修辭體系。根據(jù)這一體系對(duì)意義的“事先規(guī)定好的神學(xué)假定”,個(gè)人對(duì)事物的認(rèn)知和判斷成了對(duì)詞做出分類處理的一個(gè)過程。例如:“麻雀”一詞劃歸惡、“葵花”一詞則體現(xiàn)了善。在這里,詞的世俗性意義無論朝向善惡的哪一向度,都含有某種特異的精神疾病氣味,它是不祥的,因?yàn)樗耸求w制話語的產(chǎn)物,也是人性表達(dá)的一部分。
詞與物的聯(lián)系是怎樣被賦予超字典的反常意義的,這種意義又是如何在公共理解中固定化、功利化,并對(duì)個(gè)人語境造成巨大壓力的,這恐怕主要是社會(huì)語言學(xué)范疇的問題,我無意加以深究。我所關(guān)切的是對(duì)個(gè)人語境的不純加以質(zhì)疑能否給個(gè)人寫作帶來活力。無論在詞的精致化、詞作為集體記憶、詞作為歷史噩夢(mèng)的哪一種可能性中,我所理解的嚴(yán)肅的個(gè)人寫作都意味著呈現(xiàn)生存的未知狀態(tài)。不過問題在于,一個(gè)詩人當(dāng)然可以通過規(guī)定上下文關(guān)系來規(guī)定詞的不同意義,但這也許只是一個(gè)幻覺,因?yàn)樵娙瞬荒艽_定,具體文本所規(guī)定的詞的意義一旦進(jìn)入交叉見解所構(gòu)成的公共語境之后,在多大程度上還是有效的。令人沮喪的是,一方面?zhèn)€人語境難以單獨(dú)支撐意義,另一方面它又無力排斥公共理解強(qiáng)加的意義。例如“麥子”一詞在已故詩人海子的后期詩作中頻繁出現(xiàn),只要我們細(xì)讀原作就能發(fā)現(xiàn),海子是在元素和詞根的意義上使用這個(gè)詞的。但后來的情況卻表明,“麥子”一詞進(jìn)入公共理解后,因其指涉過度泛濫而成了那種空無所指的“能指剩余”,就像一只魔術(shù)袋,可以從中掏出種種稀奇玩意兒,但又似乎是空無一物。一個(gè)詞的信息量從來沒有包含如此多的群眾性,以及族系相似性(familial resemblances),其意義的傳遞無論是經(jīng)由誤讀或仿寫,還是通過空想或移情,都明顯帶有非意義刺激出來的儀式氣氛。顯而易見,我們?cè)谶@里遇到的并非如何理解一個(gè)詞、一首詩或一個(gè)詩人這樣的問題,我們遇到的是一種綜合的社會(huì)癥候,它相當(dāng)詭異地同時(shí)證明了詩意對(duì)公眾的強(qiáng)烈感染力以及伴隨這種詩意感染力所產(chǎn)生的深刻的無力感,詩意的獨(dú)特性越是傳遍公眾的理解,就越不是原有的詩意本身。也許這里有一種薩特(Jean-Paul Sartre)式的奇怪反諷,即“勝者為敗”的邏輯——詩人所贏得的正是他所失去的。
二、自動(dòng)獲得意義
我將上述癥候稱之為升華。
升華(Sublimation)似乎是一個(gè)具有特殊魅力的詞。從本義上講它是一個(gè)物理學(xué)、化學(xué)術(shù)語,用以指稱以下現(xiàn)象:某些熔點(diǎn)和沸點(diǎn)接近的固體物質(zhì),受熱之后外觀上不成液體而直接成為氣體,待冷卻后氣體復(fù)又直接成為固體。當(dāng)然,升華一詞后來在心理學(xué)、倫理學(xué)、美學(xué)和文學(xué)等領(lǐng)域被廣泛借用,在修辭轉(zhuǎn)義的歷史過程中,這個(gè)詞的人文內(nèi)涵顯然已超出了它在自然科學(xué)方面的字源本義。將作為人文用語的升華與作為自然科學(xué)術(shù)語的升華加以比較,其差異頗能說明問題:兩者都是指事物從一種狀態(tài)轉(zhuǎn)化為另一種狀態(tài),但后者僅限于對(duì)轉(zhuǎn)化現(xiàn)象做客觀描述,前者則含有主觀滋生的意思并涉及價(jià)值判斷(升華后的狀態(tài)在道德或美學(xué)價(jià)值上高于升華以前的狀態(tài))。
需要說明的是,我在使用升華一詞來指稱本文所討論的當(dāng)代漢語詩的種種癥候時(shí),并不奢望這個(gè)詞具有一般理論術(shù)語通常具備的準(zhǔn)確性和嚴(yán)謹(jǐn)性。我有意不在技術(shù)上做出界定,因?yàn)樯A作為綜合的社會(huì)癥候?qū)嶋H上難以被界定,我寧可將其視為一個(gè)變項(xiàng),用以說明詞與物的聯(lián)系在不同語境中的狀況和性質(zhì)。升華無疑意味著有什么東西起了變化,就當(dāng)代詩而言,首先起變化的是語言的性質(zhì)。像前面提到的海子后期詩作,“麥子”一詞的意義變形并不是一個(gè)孤立的例子,海子的不少作品在公眾理解中升華后,其可貴的元素般的語言品質(zhì)要么蒸發(fā)為某種與天地精神獨(dú)往來的空曠氣息,要么變成了流行性的傷感和鄉(xiāng)愁。張棗在談到公眾對(duì)詩歌的冷漠反應(yīng)時(shí),有一個(gè)相當(dāng)生動(dòng)的說法:冷漠可以把這些詩作像燈一樣關(guān)掉。其實(shí)公眾對(duì)詩歌的過于熱烈的反應(yīng)又何嘗不是如此!想想人們?cè)诩w交出耳朵、頭腦、良心和淚水的升華狀態(tài)下閱讀詩歌,對(duì)當(dāng)代詩人意味著什么吧。我認(rèn)為,在升華之后的讀者用意中,作者用意很可能像燈一樣被關(guān)掉。其次,隨著語言性質(zhì)的變化,詞與物的類比關(guān)系也起了變化。在上述例子中,“麥子”作為一個(gè)詞與作為物自身,兩者之間已無必然聯(lián)系。麥子所指稱的物,在性質(zhì)上可以是玉米、谷子或別的什么,只要這個(gè)“所指”能帶來還鄉(xiāng)沖動(dòng),帶來對(duì)家園村莊、對(duì)古老土地、對(duì)養(yǎng)育物產(chǎn)的感恩心情。詞升華為儀式,完全脫離了與特定事物的直接聯(lián)系,成了可以進(jìn)行無限替換的剩余能指。這種情形使人聯(lián)想到列維-斯特勞斯(C.Levi-Strauss)在《生的與熟的》一書中對(duì)大洋洲原始宗教用語“Mana”一詞的描述:“……它同時(shí)是力量與行動(dòng),質(zhì)量與狀態(tài),名詞與形容詞及動(dòng)詞;既是抽象的又是具體的,既是無所不在的又是有局限性的。實(shí)際上Mana是所有這些東西。但是,不正是因?yàn)樗皇沁@些東西中的任何一個(gè),它形式簡單,或更確切地說,是個(gè)純象征,因而能承擔(dān)起任何一種象征內(nèi)容?”
這里的象征內(nèi)容顯然具有可以無限替換的性質(zhì)。列維-斯特勞斯認(rèn)為“這樣的內(nèi)容能夠接受任何一種價(jià)值”,因?yàn)橄馦ana這類詞自身“僅會(huì)有零度象征價(jià)值”。
博爾赫斯(J.L.Borges)也曾在小說《阿萊夫》中,從觀看與遺忘的立場對(duì)語言的上述性質(zhì)加以討論。阿萊夫與Mana相似,它作為一個(gè)包容萬象的點(diǎn),可以既不重疊,也不穿透地容納現(xiàn)象與行動(dòng)的“無窮數(shù)集合”。它的名字篡奪了人的名字。意味深長的是,博爾赫斯認(rèn)為一個(gè)被看見過的、具體存在的阿萊夫是一個(gè)假的阿萊夫。他的意思是,阿萊夫作為一個(gè)詞是假詞,它所集合起來的歷史也是假歷史。我想到詹明信(F.Jameson)在討論后現(xiàn)代文化現(xiàn)象時(shí)做出的一個(gè)斷言:在假歷史的深度里,美學(xué)風(fēng)格的歷史取代了“真正的歷史”。
我可以毫不費(fèi)力地從大陸當(dāng)代詩作中找出數(shù)量驚人的詞,與Mana和阿萊夫加以比較。家園,天空,黃金,光芒,火焰,血,頌歌,飛鳥,故土,田野,太陽,雨,雪,星辰,月亮,海,它們?cè)谏A狀態(tài)中,無一例外地全部呈現(xiàn)出無限透明的單一視境,每一個(gè)詞都是另一個(gè)詞,其信息量、本義或引申義,上下文位置無一不可互換。一句話,這些詞彼此可以混同,使人難以分辨它們是詞還是假詞。問題不在于這些詞能不能用、怎么用,是不是用得太多了——因?yàn)閷懽鞑⒉皇菍ふ蚁∮性~匯,而是對(duì)“用得太多”的詞進(jìn)行重新編碼。我認(rèn)為問題在于,詞的重新編碼過程如果被升華沖動(dòng)形成的特異氛圍所籠罩,就有可能不知不覺地被納入一個(gè)自動(dòng)獲得意義的過程。對(duì)于嚴(yán)謹(jǐn)?shù)膫€(gè)人寫作而言,重新編碼意味著將異質(zhì)的各種文本要素、現(xiàn)實(shí)要素嚴(yán)格加以對(duì)照,詞的意義應(yīng)該是在多方質(zhì)疑和互相限制中審慎確立起來的,即使在它們看上去似乎是不假思索的信手拈來之物、靈感所賜之物,信馬由韁難加束縛時(shí)也該如此,原因很簡單:意義應(yīng)該是特定語境的具體產(chǎn)物。但對(duì)于升華過程來說,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那里,意義似乎是外在于任何具體語境的一個(gè)純客體,它超然物外卻又像“物”一樣存在,事先就是成熟的、權(quán)威的、完形的,不必重新編碼。在這種情況下,寫作不過是已知意義和未經(jīng)言明狀態(tài)之間的一種中介過渡。我不知道這里的已知意義是不是假意義,但我知道一個(gè)自動(dòng)獲得意義的詞往往是假詞。這些無辜的詞,它們成了列維-斯特勞斯所說的“純象征”,自身沒有任何質(zhì)量,甚至在被當(dāng)作假詞的時(shí)候似乎也不是真的。它們被濫用了,被預(yù)先規(guī)定的價(jià)值和意義,被公共理解,也許還被寫作本身濫用了。這種濫用達(dá)到失控的程度,就會(huì)使詩的寫作、批評(píng)和傳播成為一個(gè)耗盡各方歧見、去掉懷疑立場的過程。這不僅因?yàn)樵~成了以上所說的假詞之后,其指涉說變就變,“這樣輕而易舉地倒映出各種色彩,未免……太變色龍一樣了”;還因?yàn)樗凶兓瘜?shí)際上都被導(dǎo)入了一個(gè)不變的方向,借用多多一首詩的題目來說即“鎖住的方向”——所謂詞的升華,只能是混濁變向純凈,黑暗變向光明,地獄變向天堂,墮落變向救贖,俗念變向圣寵,或然變向必然,這樣一個(gè)單一走向的演變序列。
三、從反詞去理解詞
在單一向度的演變序列中詞所獲得的意義通常是類型化的。我們都知道,類型化意義有一個(gè)二元對(duì)立的基本結(jié)構(gòu)。詞的升華由于預(yù)先規(guī)定了單一變化方向,詞不僅自動(dòng)獲得意義,而且自動(dòng)獲得這一意義的對(duì)立面。兩者都是類型化的,屬于同一結(jié)構(gòu)中的兩極。它們的對(duì)立有時(shí)涉及價(jià)值判斷,有時(shí)是不同語境的對(duì)比,有時(shí)帶著急迫的世俗功利性要求。但上述對(duì)立很可能轉(zhuǎn)化為并無實(shí)質(zhì)內(nèi)容的純粹修辭現(xiàn)象,因?yàn)橐饬x的對(duì)立在這里完全可以和詞的修辭性對(duì)立混用。換句話說,寫作在升華過程中所經(jīng)歷的從黑暗到光明、從地獄到天堂、從肉體到精神的種種變化,究竟是意義和價(jià)值的變化,還是得來不費(fèi)功夫的措辭表演,兩者很難加以區(qū)分。就常識(shí)而言,我們往往是從反詞去理解詞,例如,從短暫去理解長久,從幽暗去理解明亮,從邪惡去理解善良,從災(zāi)難去理解幸福。詞與反詞在經(jīng)驗(yàn)領(lǐng)域的對(duì)立并非絕對(duì)的,它們含有兩相比較、量和程度的可變性、有可能調(diào)解和相互轉(zhuǎn)換等異質(zhì)成分。但在一個(gè)將經(jīng)驗(yàn)成分悉數(shù)過濾掉的類型化語境中,對(duì)立則是孤零零的、針鋒相對(duì)的,我想這已經(jīng)不是詞與詞或詞與物的對(duì)立,而是意義、價(jià)值判斷之間的二元對(duì)立。在這種類型化的語境中從事寫作,詩人完全可能以“反對(duì)什么”來界定自我,而無須對(duì)“反對(duì)”本身所包含的精神立場、經(jīng)驗(yàn)成分、變異因素等做出批評(píng)性的深刻思考,因?yàn)椤邦愋突恼Z境”已經(jīng)將這一切過濾掉了,只留下孤零零的反對(duì)。至于意義、價(jià)值顯然可以自動(dòng)獲得。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就曾經(jīng)說過,“一個(gè)與邪惡斗爭或抵制它的人幾乎會(huì)自動(dòng)地把自己當(dāng)成是善良的,從而回避自我分析。”
正是由于這個(gè)以反對(duì)什么來界定自我的過程回避了自我分析,因此所謂的界定自我,可以方便地轉(zhuǎn)化為升華自我。這給當(dāng)代詩的寫作帶來了真正的混亂。我指的是寫作立場的混亂,精神起源的混亂。其實(shí)許多詩人的寫作根本談不上什么精神起源,他們往往是從青春期沖動(dòng)、從短暫地風(fēng)靡一時(shí)的種種時(shí)尚、從廣告形象設(shè)計(jì)和修辭表演效果以及從江湖流派意識(shí)中,獲得反對(duì)立場。反對(duì)在這里主要是一種姿態(tài),有無深刻的精神內(nèi)涵倒在其次。我認(rèn)為,這是一種時(shí)過境遷的、寄生性質(zhì)的反對(duì),詞的意義寄生在反詞上面。先有了反詞,然后詞才被喚起,被催生,被重新編碼。問題是,反對(duì)邪惡一旦成為界定善良自我的必不可少的前提,那么就邏輯而言,下面兩種可能都難以排除:其一,因?yàn)樾皭旱拇嬖冢瑢?dǎo)致了我們對(duì)邪惡的反對(duì);其二,我們?yōu)榱朔磳?duì)邪惡而發(fā)明了邪惡(例如:為了反對(duì)體制的或他人的邪惡而發(fā)明了自我的邪惡)。這里是否有一種弗賴(Northrop Frye)所說的“可怕的對(duì)稱”呢?因?yàn)橛刑焯茫阅軌蛱枚手睾魬?yīng)一個(gè)地獄的存在。也許需要證明的不是天堂,而是地獄。我們對(duì)天堂知之甚少,但對(duì)地獄卻知道很多,可以反復(fù)發(fā)明地獄。而且,以反對(duì)地獄來界定天堂中的自我,不正是為了記住地獄嗎?因?yàn)槲覀冊(cè)谄鹪从诘鬲z的寫作中所處理的那個(gè)“天堂般的自我”,實(shí)際上并不帶來對(duì)于記憶中的地獄的尼采式“主動(dòng)遺忘”。詞無力喚起對(duì)于丑惡現(xiàn)實(shí)的遺忘。對(duì)詞的升華來說,天堂與地獄是并存的對(duì)稱的語境。
我不知道人們是否已經(jīng)足夠清醒地認(rèn)識(shí)到,由于有了丑惡現(xiàn)實(shí),才會(huì)有詩人內(nèi)心的美麗童話,這個(gè)典型的顧城式邏輯完全可以自動(dòng)顛倒過來,改寫為:由于有內(nèi)心的美麗童話,所以必須有丑惡現(xiàn)實(shí)與之對(duì)應(yīng)。這樣的邏輯一旦被推向極端的理解,我們就很難分清,在顧城后來提出的一個(gè)命題“殺和被殺都是一種禪”中,究竟是因?yàn)橛辛爽F(xiàn)實(shí)行為“殺和被殺”,才有了內(nèi)心之“禪”;還是因?yàn)橛卸U,才有殺和被殺?顧城后期作品《城》中有一首短詩涉及上述命題:
殺人是一朵荷花
殺了就拿在手上
手是不能換的
殺人在文明的語境中顯然是反文明的。但荷花將殺人轉(zhuǎn)換到一個(gè)準(zhǔn)宗教的透明語境。由于兩種語境的重疊指向一個(gè)單向度的升華過程,殺人就是荷花,詞變成了反詞。也許詞和反詞同時(shí)被取消了,正如在善惡合一的過程中單獨(dú)的善、單獨(dú)的惡都被取消了。只剩下禪。我不知道禪是不是一個(gè)中性的容器,一個(gè)像漏斗那樣的物,世上的信仰和知識(shí)它無所不包,但無一不被漏掉。只剩下容器本身。器物在時(shí)間中戰(zhàn)勝了精神,刀戰(zhàn)勝了詞。“拿在手上”,我想作者在這里刻意強(qiáng)調(diào)了某種表演性、可觀看性。“手是不能換的”,頭顱能不能換呢?在詞升華到禪的境界之后,殺和被殺作為文本事件,與作為現(xiàn)實(shí)事件的殺和被殺能不能換?一個(gè)具名的人殺死另一個(gè)具名者,與匿名狀態(tài)下的一群人殺死另一群人能不能換?給殺和被殺一個(gè)禪或童話的美麗語境,一束荷花的意象,與殺和被殺在國家機(jī)器、國家理性構(gòu)成的制度語境中進(jìn)行,兩者又能不能換?
“手是不能換的”。但握在手中的鮮花和刀卻可以換。嚴(yán)格地講,我提出“能不能換”這樣的質(zhì)疑并不是針對(duì)自傳意義上的顧城的,而是針對(duì)某種詭異的語境現(xiàn)象。我認(rèn)為,顧城后期作品中的個(gè)人自傳性語境與類型化的語境是混而不分的。問題的詭異之處就在這里。在一個(gè)類型化的整體語境里,每一個(gè)人的個(gè)人自傳性語境都具有可換性。換句話說,殺和被殺升華為一朵荷花后,可以遞到我們當(dāng)中任何一個(gè)人的手上,剩下的問題只是,拿什么去換?也許必須加以質(zhì)疑的是,這里的荷花對(duì)應(yīng)于自動(dòng)賦予意義和價(jià)值的類型化語境,它與殺人的重疊,實(shí)際上取消了殺與被殺的特定性、個(gè)人自傳性,使之成為禪的透明視境中發(fā)生的詞與行為之間的一樁轉(zhuǎn)譯事件。我歷來認(rèn)為,善與惡是具體的、個(gè)別的承諾。一旦取消其具體性,對(duì)承諾本身的解釋就可以從正變到反,只要能找到一個(gè)可以通約的意象。我無意從教義上討論禪的善惡觀,因?yàn)槎U在這里其實(shí)只是那種漏斗性質(zhì)的升華語境:任何事物(例如殺與被殺這一類世俗場景)裝進(jìn)去之后,都從單一的荷花中漏出來。
為現(xiàn)實(shí)中的災(zāi)難尋找一個(gè)像荷花那么美妙的拿在手上的“可公度意象”,難道這就是當(dāng)代詩人想干的嗎?我想有些詩人不這樣干。當(dāng)鮮花、刀、麥子、夜鶯、鴿子、向日葵之類的“超驗(yàn)所指”在人們手上像走馬燈似地?fù)Q來換去時(shí),陸憶敏的兩句詩:
我站在你跟前
已洗手不干
含有不容置疑的拒絕意味。翟永明也在某些被廣泛閱讀的詩作中對(duì)手的動(dòng)作做了深思熟慮的處理:她的手通常是縮回去的,交叉著抱在胸前。呂德安的手“疲于一種交換”。孟浪的手出現(xiàn)在強(qiáng)制性的統(tǒng)治語境中:
……手和手
被銬在一起……
張棗的手則帶有南方詩人特有的恍惚迷離氣質(zhì),使人分不清是作者本人的手,還是他者的手。請(qǐng)將《卡夫卡致菲麗絲》中的一行詩“我奇怪的肺朝向您的手”和《楚王夢(mèng)雨》中的一行詩“讓那個(gè)對(duì)飲的,也舉落我的手”,與下面這句詩對(duì)照起來讀:
……沒有手啊,只有余溫。
手在上述不同語境受到了限制,無論它是作為一個(gè)幻象,還是作為現(xiàn)實(shí)。問題不在詞與物、詞與反詞能不能轉(zhuǎn)譯,而在我們是否對(duì)轉(zhuǎn)譯的語境做出必不可少的限制。
四、對(duì)于圣詞的抵制
為什么要對(duì)轉(zhuǎn)譯的語境做出限制?
首先,存在著文本世界與現(xiàn)象世界相互轉(zhuǎn)譯的可能性。轉(zhuǎn)譯的過程如果被強(qiáng)化到詞等同于歷史硬事實(shí)的程度,詞的及物性就會(huì)不加限定地被當(dāng)作滋生現(xiàn)實(shí)的手段強(qiáng)加給寫作,使寫作過程成為不僅提供美學(xué)許諾,而且提供造物許諾的一個(gè)能量轉(zhuǎn)化過程。詞的命名功能在這里傾向于變?yōu)樾袆?dòng)本身。但事實(shí)上,以為通過強(qiáng)調(diào)能量轉(zhuǎn)換、強(qiáng)調(diào)造物許諾就能使靜態(tài)的詞行動(dòng)起來,進(jìn)而由詞的行動(dòng)帶來物自身的行動(dòng),這根本就是一種幻覺。我們?cè)谶@種情形中看到的不僅是意義自行增值的惡性循環(huán),而且也是詞的世界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的自動(dòng)轉(zhuǎn)譯。問題是詞在自動(dòng)轉(zhuǎn)譯中給出的造物許諾無法兌現(xiàn),卻帶來了種種期待,要求,英雄幻覺,道德神話,它們共同構(gòu)成了集體精神成長史的消費(fèi)奇觀,并且最終轉(zhuǎn)化為一種以焦慮為主要特征的社會(huì)癥候。令人不安的是,無法兌現(xiàn)的造物許諾作為有待釋放的潛在能量,完全可以既為個(gè)人寫作,也為消除個(gè)性的“一般書寫形式”不加區(qū)分地提供摹仿資本(Mimetic Capital)。“一般書寫”是為整體性所支配的,帶有明顯的美學(xué)上的極權(quán)主義傾向。
其次,自動(dòng)轉(zhuǎn)譯有一個(gè)本體論詩學(xué)的前提:圣詞先于尋常詞語。圣詞所指涉的是寫作中的絕對(duì)起源,即先于個(gè)別書寫的“一般書寫形式”。就詩人與他所隸屬的歷史“通過語言構(gòu)成的”交換關(guān)系而言,圣詞旨在提供使人類經(jīng)驗(yàn)類型化、整體化的升華動(dòng)力。從某種意義上講,圣詞的基礎(chǔ)是“特許的檔案式預(yù)想”與二元對(duì)立邏輯的分析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事先假定有一個(gè)絕對(duì)支點(diǎn)(“不可解釋的阿基米德點(diǎn)”)來制約思想的形成過程、表達(dá)過程,以防不規(guī)范的語句突然出現(xiàn)。圣詞正是這種性質(zhì)的絕對(duì)支點(diǎn)。陳東東在其不分行的詩篇《地理》中寫道:
用簡潔的一個(gè)詞占有又饋贈(zèng)一切花園和思想迷宮……
“占有和饋贈(zèng)”是圣詞的特權(quán)。為排除詞的異質(zhì)成分,信息被全部轉(zhuǎn)譯成圣詞,然后分配給尋常詞語。當(dāng)然,圣詞只是在輸入的信息易于分類、能自動(dòng)推斷出事實(shí)含義并自動(dòng)與現(xiàn)實(shí)的變易特性相協(xié)調(diào)時(shí)才起作用。圣詞的這種作用類似于巴爾特(Roland Barthes)所討論過的“零度詞語”賦予已知事物的強(qiáng)化作用。對(duì)此,德里達(dá)(Jacques Derrida)表明了另一種看法,他認(rèn)為語言所包含的信息“產(chǎn)生于自身的蛻化”,因此可以提供一大堆現(xiàn)實(shí)。換言之,信息與現(xiàn)實(shí)的相互轉(zhuǎn)譯并無一個(gè)圣詞所代表的絕對(duì)起源可以追溯,除非我們對(duì)圣詞的追溯受到尋常詞語種種用法的限制。圣詞的那種“占有又饋贈(zèng)”的特權(quán)必須被充分質(zhì)疑,必須加以限制。海子后期詩作中頻繁出現(xiàn)的“太陽”一詞顯然是先于觀看、照耀、升起和落下的圣詞。我注意到海子與此同時(shí)對(duì)一種特殊生命狀態(tài)“瞎”的強(qiáng)調(diào)。我認(rèn)為海子是在尋找必不可少的語境限制。他在九位盲人的身上找到了太陽的盲點(diǎn):一種朝向內(nèi)部黑暗的、深具穿透力的觀看。我感覺到了“太陽”與“瞎”之間的語境張力。類似的情形在海子的《金字塔》一詩中也可看到:
人類的本能是石頭的本能
消滅自我后盡可能牢固地抱在一起
沒有繁殖
也沒有磨損
詩中的“石頭”是一個(gè)零度狀態(tài)的圣詞,孤立、靜止、不起變化。海子在這首詩的第一段就寫道:
如果這塊巨石
此時(shí)紋絲不動(dòng)
被牢牢鍥入
那首先就移動(dòng)
別的石頭
放在它的周圍
上述詩行是對(duì)維特根斯坦(L.J.J.Wittgenstein)一則札記的重新書寫,海子只是作了分行的技術(shù)處理(順便提一下,《金字塔》這首詩是題獻(xiàn)給維特根斯坦的)。這里,作為圣詞的石頭紋絲不動(dòng),但“別的石頭”卻可以移動(dòng),而石頭一經(jīng)移動(dòng)就從圣詞變成了尋常詞語。石頭由此獲得了相互扭結(jié)的兩組陳述:在陳述A中,石頭是不可移動(dòng)的;但在陳述B中,石頭卻是可以移動(dòng)的。兩組陳述都與石頭這個(gè)詞的已知意義相吻合,但彼此卻是對(duì)立的。詞在這里是對(duì)詞自身的一種抵制。我認(rèn)為沒有必要一定要為這種抵制發(fā)明一個(gè)得到公認(rèn)的反詞立場,不僅因?yàn)樵~抵制自身屬于寫作過程中的個(gè)人秘密,帶有“符號(hào)的無法識(shí)讀性”(Unreadability);尤其因?yàn)樵~對(duì)詞自身的抵制往往會(huì)被轉(zhuǎn)譯為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抵制,兩種抵制摻雜在一起,使人難辨真相。海子似乎注意到了這一點(diǎn),因此他在詩中兩次寫道:“經(jīng)書不辨真?zhèn)巍薄!督鹱炙愤@首詩表明海子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到,并不存在一個(gè)共同的反詞立場。
五、不可公度的反詞立場
在一般詩學(xué)中,在公眾的閱讀期待中,存在著先于個(gè)人寫作的前意義,這個(gè)事實(shí)并不帶來沮喪。因?yàn)橐粋€(gè)中性的、毫無現(xiàn)實(shí)傾向性的理想詞語空間對(duì)于讀者、批評(píng)家和詩人都不存在。一些當(dāng)代詩人為了純潔詞語,重溫詞作為事物起源的古老夢(mèng)想,重建詞的烏托邦,其寫作受到命名沖動(dòng)的鞭策,因而采取全然無視公眾見解以及當(dāng)代批評(píng)的極端立場。另一些詩人與此相反,他們急迫地要使個(gè)人語境獲得公共性質(zhì),也許過于急迫了。這兩種傾向在大陸當(dāng)代詩歌的寫作進(jìn)程中都產(chǎn)生了實(shí)際影響,發(fā)展出各自的風(fēng)格類型、寫作模式、流派主張及其種種變體。兩種傾向都各有道理,但局限性也非常明顯:按照前者的主張去寫作,詩人有可能失去處理身邊素材——這些日常素材往往含有大量的群眾信息——的能力;而如果遵從后者的主張,功利性和表演性又肯定會(huì)危及詞的精神品質(zhì)。問題是上述局限性在實(shí)際寫作過程中,完全有可能被見解各異的詩人當(dāng)作自己的美學(xué)風(fēng)格特征加以炫耀,也就是說,將局限性發(fā)展成得到公認(rèn)的反詞立場,發(fā)展成一般風(fēng)格。
這會(huì)不會(huì)印證前面已經(jīng)引用過的詹明信的一句話:美學(xué)風(fēng)格的歷史取代真正的歷史?我認(rèn)為,關(guān)鍵在于詩人應(yīng)該對(duì)寫作過程中的反詞立場是否類型化保持足夠的警惕,因?yàn)榉丛~立場往往是與寫作中的身份確認(rèn)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的。反詞立場一旦類型化,詩人的身份就會(huì)成為面具或注冊(cè)商標(biāo)之類的“客觀識(shí)別標(biāo)記”。現(xiàn)在的流行看法是,一個(gè)詩人要想“有效地”、“合法地”從事寫作,必須預(yù)先澄清反詞立場,獲得公認(rèn)的、易于識(shí)別的類型化身份。比如說,一個(gè)具有本土派身份的中國詩人在確立反詞立場時(shí),似乎不得不以“世界詩”為敵。但所謂的世界詩只是一個(gè)假想敵,從中發(fā)展出來的反詞立場反過來證明了“本土派詩人”身份的不純。與此類似的其他一些概念,如傳統(tǒng)派,鄉(xiāng)土詩人,尋根派,自白派,洋務(wù)派,邊塞詩人,城市詩人,江南才子派,口語詩人,整體主義,東方主義,后現(xiàn)代派詩人,新狀態(tài)寫作,所有這一切似乎都是為了便于識(shí)別身份,為了使反詞立場得到公認(rèn)而提出來的,它們也許有助于說明某些共同現(xiàn)象,有助于劃界行為,但對(duì)理解真正的個(gè)人寫作實(shí)際上很少起作用。
能不能這樣說:一個(gè)詞無論在信息量、價(jià)值判斷、修辭功能等方面包含了怎樣的公共性質(zhì)都不必回避,因?yàn)樵~的混雜不純實(shí)際上能夠?yàn)楫?dāng)代詩的寫作帶來現(xiàn)實(shí)感和活力。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為詞的意義公設(shè)(Meaning Postulates)尋找不可通約、不可公度的反詞。也就是說,反詞立場的確立不是一般詩學(xué)、不是群眾理解、當(dāng)然也不是身份認(rèn)同這類準(zhǔn)政治行為的事,它純屬于詩人自己。詩人通過對(duì)詞的意義公設(shè)的被動(dòng)認(rèn)可及奴隸般的服從(艾略特就曾指出過,好的詩人應(yīng)該是語言的奴隸而不是它的主人),隱身于現(xiàn)實(shí)世界,隱身于人群之中;但詩人與此同時(shí)又通過對(duì)反詞的個(gè)人化理解得以從人群中抽身離去,保留至關(guān)重要的孤獨(dú)性和距離感。我在這里所說的反詞,不應(yīng)該被狹義地界定為詞與詞之間自行產(chǎn)生的語義對(duì)立,而應(yīng)該從廣義上被理解為文本內(nèi)部的對(duì)應(yīng)語境。我的意思是,反詞是體現(xiàn)特定文本作者用意的一個(gè)過程,這個(gè)過程將詞的意義公設(shè)與詞的不可識(shí)讀性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精心設(shè)計(jì)為一連串的語碼替換、語義校正以及話語場所的轉(zhuǎn)折,由此喚起詞的字面意思、衍生歧義、修辭用法等對(duì)比性要素的相互交涉,由于它們都只是作為對(duì)應(yīng)語境的一部分起臨時(shí)的、不帶權(quán)威性的作用,所以彼此之間僅僅是保持接觸(這種接觸有時(shí)達(dá)到迷宮般錯(cuò)綜復(fù)雜的程度)而既不強(qiáng)求一致,也不對(duì)差異性要素中的任何一方給予特殊強(qiáng)調(diào)或加以掩飾。
我想舉兩個(g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我所理解的個(gè)人化的反詞立場。一個(gè)例子是前文已經(jīng)提到的海子后期寫作中出現(xiàn)的“瞎”這個(gè)詞,這是海子為他自己狂熱歌頌的“太陽”所設(shè)置的一種反詞性質(zhì)的生命狀態(tài)。“瞎”與公眾所理解的黑暗不是一回事。因?yàn)樵诠娦缘暮诎抵刑柺侨毕撸@是暫時(shí)的黑暗,暗含了“太陽就要出現(xiàn)”這樣一種希望;而海子的“瞎”則是將太陽本身包括進(jìn)來的一種個(gè)人的、徹底的、生命意義上的黑暗。瞎作為太陽的反詞,指涉了生命現(xiàn)象與自然現(xiàn)象的對(duì)立,內(nèi)在視境與表面視境的對(duì)立。對(duì)此加以深究就能理解為什么海子后期詩篇中的太陽是歌唱性的,而非可視性的。因?yàn)橄故撬廾模灾荒苋A聽、去歌唱,把太陽轉(zhuǎn)化為白熱化的聲音。我想指出的第二個(gè)例子是張棗《入夜》這首詩中的一行詩:
花朵抬頭注目空難
空難在這里被處理為花朵的反詞。可以從三個(gè)互有關(guān)聯(lián)的層次上理解作者的用意。其一,從空間關(guān)系看,“花朵抬頭注目”指出了一個(gè)向上的意圖,而“空難”則是向下的、崩潰的。其二,兩者的空間接觸后面隱藏著作者對(duì)時(shí)間的識(shí)讀。花朵與一個(gè)完整的自然時(shí)間過程(從生長、開放到凋謝)相對(duì)應(yīng),空難則對(duì)應(yīng)于一個(gè)反自然的、工業(yè)文明的時(shí)間過程。按照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理解,空難發(fā)生的一剎那屬于“時(shí)間零”(絕對(duì)時(shí)間),空難在這一時(shí)間里看上去酷似一朵花:夜空中的災(zāi)難之花,潰散之花,機(jī)器產(chǎn)品的故障之花,包含了宇宙的全部恐懼。其三,作者真正關(guān)切的是人性問題。在傳統(tǒng)中國詩中,以花喻人是一種常見的、幾乎已成陳腔濫調(diào)的修辭用法,對(duì)此作者不僅不回避,反而用“抬頭注目”予以特殊強(qiáng)調(diào)。我想詩人張棗無法接受空難的基本后果:空無一人。所以他讓花朵在詩句中執(zhí)行了代人現(xiàn)身的功能。對(duì)花朵而言,死于空難的人也許人人都曾經(jīng)是賞花人,但現(xiàn)在人去花在,他們當(dāng)中無人還能看到花朵,所以花朵反過來看人——從修辭策略上講,被看變成了看。讀者從中可以感受到作者悲天憫人的獨(dú)有情懷。而這種情懷顯然不是“以花喻人”之類的傳統(tǒng)修辭用法所能單獨(dú)呼喚出來的,如果作者在這里沒有為這類常見的修辭用法提供一個(gè)像“空難”那樣的個(gè)人化的反詞的話。
1995年9月于華盛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