苔花·牡丹·經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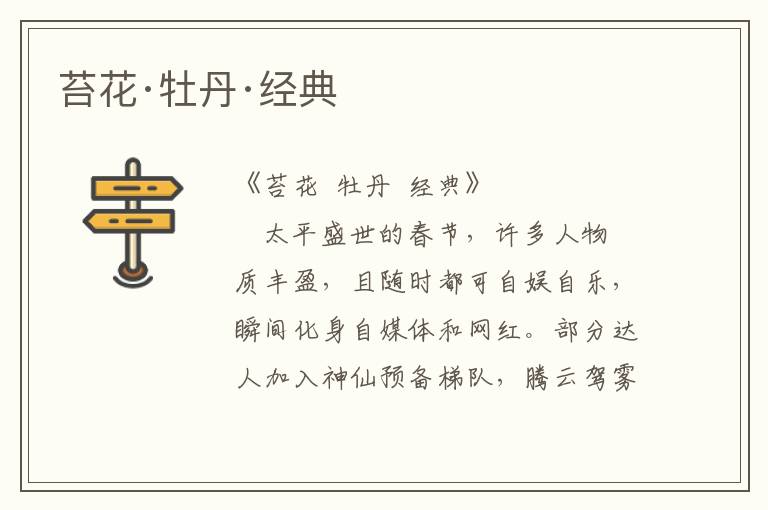
《苔花 牡丹 經典》
太平盛世的春節,許多人物質豐盈,且隨時都可自娛自樂,瞬間化身自媒體和網紅。部分達人加入神仙預備梯隊,騰云駕霧,或跨國過境、逍遙快活,或煮茶北岳、種豆南山。健康排行榜前列的水果堆在家里乏人問津,春節晚會逐漸成了過年的新衣。不少人心浮氣躁,身心“彈簧”也因慵懶變成“鋼絲”,假期大多盯手機、玩小程序,忙著敘舊迎新搭人脈,有時連紅包也忘了搶。兒時的年味漸行漸遠,淡得幾乎忘卻,甚至不老金曲《難忘今宵》也難以帶出往日的激情。
不料,2018年正月初一至初三央視綜合頻道黃金時段突然閃出一匹黑馬——大型詩詞文化節目《經典詠流傳》,一時間點亮了億萬人的雙眼,以至于眾人合唱“今夜無人入眠”。
近幾年,我國電視中傳統文化類節目一波一波,持續不斷。新鮮出爐的《經典詠流傳》以現代流行音樂作經典詩詞伴侶,一時贏得萬眾矚目,好評不斷,后來居上,挺立潮頭。甚至在網絡上力壓春晚,持續刷屏。趁著閑暇,搖著手機,我看完了三期16首詩詞的演唱。
作為新時代中國電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文化節目,央視1套推出的《經典詠流傳》,在時空選擇、國際化策劃、時尚化手法、破局與創新效果諸方面,幾乎沒有懸念地贏得洛陽紙貴。演出現場,主持人提要、舞美造勢、傳唱人表演、觀眾亮燈、鑒賞團評點等,效果都出乎意料的好。有人譽其為超出想象,替全國電視臺樹立了一個示范;有人稱其是中華傳統文化傳播的一張有聲名片。的確,成功者自有其因。用央視的廣告語解密:《經典詠流傳》將部分古詩詞和近代詩詞配以現代流行音樂,帶領觀眾在一眾唱作歌手的演繹中領略詩詞之美。“和詩以歌”的形式將傳統詩詞經典與現代流行相融合,讓經典具有新時代屬性。
節目的亮點之一在于今人將現代漢語與古文結合,創作歌詞,讓古人智慧閃耀的同時,又加入了當代的哲思。應該承認,《經典詠流傳》作為泱泱大國的第一檔詩詞文化節目,用現代方式給觀眾帶來傳統文化的感動,謀求傳統文化與當代讀者交流,與外來文化溝通。如四國音樂家用中英文演唱的完整的唐詩《登鸛雀樓》,就讓人大開眼界。資料披露,央視還準備把這檔節目做成全民傳唱經典的一種文化導引行為。這立意不可不謂高大精準。且這種“和詩以歌”的形式,讓人物和故事極具家國情懷、價值引領,也容易讓傳統經典再次成為當下的流行。初心可嘉,功莫大焉。
以一個晚上的傳播就超過前300年接受量的清代袁枚《苔》詩為例。“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這本是一首普通的詠物詩,口語、白話、詼諧、率真,20個字如此暢曉、平實、白描,盡顯出大文豪煉如不煉的“性靈”本領,使人一下子就聯想到唐代王之渙的“白日依山盡”,杜甫的“青春作伴好還鄉”,劉禹錫的“惟有牡丹真國色,開花時節動京城”。詩中“青春”本意就是青苔,“牡丹”則歷來代表大富貴。所以,在末句生發勵志之意后,鑒賞者引申出青春芳華和向上情懷,編導者著力挖掘思想深度和現實意義。說實話,當《苔》詩出現在節目的剎那間,我腦海里浮現出故鄉盛傳的一副對聯。其故事是,杜甫好友、詩書畫三絕的廣文館博士鄭虔被貶臺州司戶參軍后,曾設館授徒,但當時“臺州地闊海冥冥,云水長和島嶼青”,人文閉塞,學生受教困難。鄭先生負氣出走,學生鍥而不舍追隨,最后在一個小山村里,由先生考對聯的方式,決定去留。當先生吟出上聯“石壓筍斜出”,學生中即有人接出下聯“谷陰花后開”。自然,廣文先生留在了臺州,臺州教育從此啟蒙,村子也遂以“留賢”命名。這對聯與《苔》詩可謂異曲同工、千古共義。
不過,興奮之余,深思之后,總覺得整臺節目稍偏于經典之形,尚不及《見字如面》《中國詩詞大會》《朗讀者》注重經典之心,來得純粹、清爽、演繹到位。我私心以為,如果創作方法和編排藝術能進一步改進和完善的話,這檔節目的中國夢可能更加圓滿。故班門弄斧,略陳陋見。
首先,引用鑒賞團成員的話說:“這里的每一首歌和每一首詩的背后都有一段人生,都與亙古綿延的文化傳統相接,無論承載的是輝煌還是失落,都變成無以復加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成為我們民族文化的自信和驕傲。”但很遺憾,這里所說的背后故事多數屬于傳唱人,客觀上不可避免地造成喧賓奪主。例如,奧運冠軍孫揚,香港娛樂圈大腕汪明荃和羅家英,臺灣“民謠之父”胡德夫,88歲中國第一代鋼琴家巫漪麗,他們感人肺腑的事跡蓋過了經典作品本身的故事。而且多首經典作品在演繹中,有意無意地被引導、放大到傳唱人的故事上。
其次,經典作品的界定標準需要統一,演繹方式值得推敲。如對經典詩詞語句任意加減改編,在前面、中間、后面移植上現代詞語,拉郎配似的揉合成流行歌曲的做法,肢解了原著,曲解了原意。這種對經典作品動手術、掐頭去尾、割裂原作、異化編輯的“詠流傳”,讓人難以理解和接受。曾記否,我國戲劇舞臺上,曾把歷史英雄曹操演變成了奸人。由于戲劇、電視普及力度十分強大,極易以訛傳訛、誤導后人,以至于今天眾多百姓對曹操還是這樣的看法。如果經典詩詞也被這樣處理的話,那么歷史覆轍會不會重蹈?流傳下來的還是經典原著嗎?
另外,舞臺上伴奏樂器“豐富”“時尚”,新老、中外、長幼參與者才情橫溢,詩詞內容難免被歌曲、器樂、演員的表演形式所掩蓋、沖淡,詩詞的韻味和意境難免跑調、走味。觀眾墜入五彩繽紛、耳目迷離的綜藝大觀中,連作品本來面貌都模模糊糊、張冠李戴,不知經典在哪個云深處,經典又怎能真正流傳?當然,編導主觀上是為了體現“詠流傳”,但太強的現代感、表演化、綜藝性,反而讓經典的厚重多有缺失,使觀眾陶醉表演,忘記經典。
再者,古典詩詞本來就是用來唱的,且前人自有前人之唱法。據我所知,我國經典詩詞研究前輩如吳梅、唐圭璋、施蜇存、萬云駿、華鐘彥等,均有師承有序的精彩唱法,這些唱法亦已傳授給學生,如鐘振振等。現在節目所選的當代流行曲譜,雖然本意應該是基于中國古典詩詞因可唱而誕生、借可唱而流傳的本來面貌,但在客觀效果上,卻丟失了傳統唱法的原汁原味,黯淡、甚至消退了經典本身的許多光芒。尤其對師承有序的現代唱法選擇忘卻和拋棄,很有可能造成古法吟唱的斷層和永遠失傳。要知道,那也是珍貴的經典啊,怎不令人惋惜。如果節目能把這些吟唱方法介紹和演示出來,則經典傳唱才能真正“詠”流傳。否則,只是斷代的詠、隔代的傳。況且,現場演示的部分現代傳唱流于淺薄,失卻了經典之高雅,大煞風景。雖然有的曲子的確好聽,很鼓舞人,但這樣偏偏更容易誤導觀眾。
另外,鑒賞人的解讀多在經典外圍轉悠,有時蜻蜓點水、隔靴搔癢、泛泛而談,缺少對經典本身字詞句的詮釋、典故運用的品味、詩意詞境的點化、寫作背景的解說、現實意義的闡發,難免有嘩眾取寵之嫌。說得極端些,這套節目是借經典之名傳現代演唱,且下足了功夫,而對經典內涵的傳承得過且過、淺嘗輒止。甚至是編導匠心獨具、表演爐火純青的一場文藝“演出”。只不過整個節目披了另一件時尚的新衣,換了個娛樂玩法。
經典作品該如何流傳?學者們一直在不懈努力。我以為,經典之傳承必須首先尊重經典,敬畏前人。若用現代曲子歌詠古代經典,前提要有靈魂觸動、由心而生,吟唱要神形兼備。否則,也是對前人的大不敬,是對經典的褻瀆。說句玩笑話,像現在央視這樣演下去,即使前人無語,我們不用付版權費,作品不失傳,其經典真身也很快會變成化身。
至于谷建芬老師譜曲的50首《新學堂歌》,由于基本保留了經典詩詞的意境,又吻合了時代的韻律,好聽易唱,因此,得到普遍認可,是影響好、傳播廣、大成功的范本。我的故鄉有一首流傳千古的禪詩“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傳承經典欲避免緣木求魚、泥牛入海之虛空,而得到羚羊掛角、香象渡河之真意,唯有在經典內用功。“一言半句便通玄,何用經書千萬篇。人若不為形所累,眼前即是大羅天。”
同樣,也以《苔》作喻:《經典詠流傳》節目盡管陽光燦爛、春風和熙,但目前仍屬“苔花”。前三期能夠流傳的恐怕也就是《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登鸛雀樓》《苔》《枉凝眉》《將進酒》等少數幾首。因此,需要假以時日完善和提高,以期真正演變為牡丹。我相信,有“行業領域最頂級的一批團隊參與節目”,國色天香的盛開一定指日可待。如果可能,建議這檔節目改用“經典詠嘆調”命名,這樣更契合音樂節目原義。因為“詠流傳”是主觀意愿,所選的經典作品卻是客觀性存在,并不以“一眾唱作歌手”的意志、喜好為轉移。現在的節目,熱鬧是熱鬧,好看也好看,而且憑借聲光電科技搶眼球,十分煽情,但鮮衣怒馬總難持久。
當我還在手機上寫這篇小文時,虹橋新天地早已是一片燈海,“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元宵燈會正在上演。窗外,小區庭院里“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是啊,又到了“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的踏春季節。信息傳來,明天開始,每周六的央視綜合頻道將繼續播出《經典詠流傳》第N期。我平居靜慮,仿佛聽到了經典詩詞春天的腳步聲,鏗鏘有力,漸行漸近。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讓我們一起努力,共同珍惜這美好的新時代,更好地享受前人饋贈的詩詞之真善美,虔誠地敬畏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帶給我們的無比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