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與《老子》國學(xué)經(jīng)典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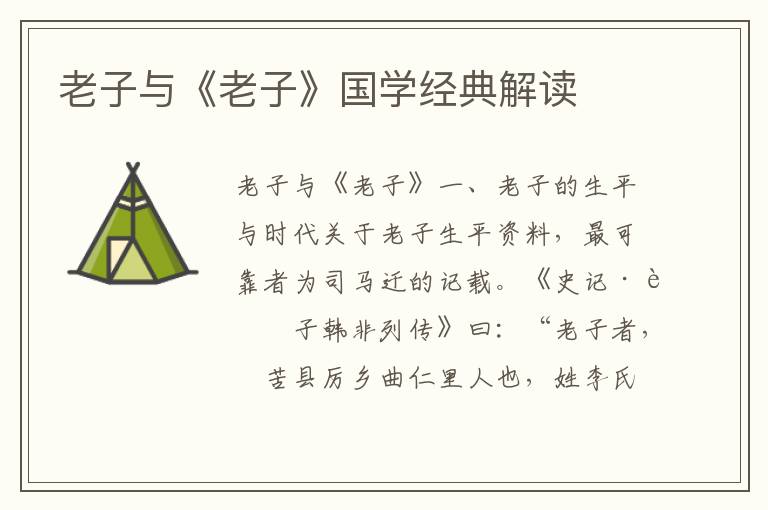
老子與《老子》
一、老子的生平與時代
關(guān)于老子生平資料,最可靠者為司馬遷的記載。《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xiāng)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唐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引《朱韜玉札》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xiāng)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疏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年而生。”又《玄妙內(nèi)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乃割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jīng)》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眾理,達成圣孳,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宋裴骃《史記集解》引《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按:《地理志》苦縣屬陳國者,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今檢《地理志》,苦實屬淮陽郡。苦音怙。《正義》按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jié)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xiāng)祠,老子所生地也。”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曰:“老子修道德,其學(xué)以自隱無名為務(wù)。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guān),關(guān)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余歲,或言二百余歲,以其修道而養(yǎng)壽也。”《正義》:“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dāng)時世亂,逃世耕于蒙山之陽,莞葭為墻,蓬蒿為室,杖木為床,蓍艾為席,菹芰為食,墾山播種五谷。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結(jié)合史籍所載,老子從早年起就在東周王朝任史官——守藏史(又稱柱下史),掌管史冊典籍,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約在中年時期,受到王朝貴族迫害,一度罷官,逃居魯國避難數(shù)年。后來,老子又被召回復(fù)職。約在五十多歲時,在東周王朝內(nèi)戰(zhàn)中失敗的王子朝,攜帶王朝史冊典籍逃往魯國避難,史冊典籍既失,老子亦去其職。老子在東周時間較長,見東周王室衰微,便離周去秦。西行途中,經(jīng)函谷關(guān),遇守關(guān)令尹喜(又稱關(guān)尹或關(guān)令尹喜)。尹喜求為其著一部書,老子著道德五千余字。即今所言《道德經(jīng)》,亦稱《老子》。尹喜慕老子之學(xué)識,便“去吏而從之”。老子西去后,隱居秦國,后人只知其壽命很長。司馬遷說:“蓋老子百有六十余歲,或言二百余歲。”此為傳言和推測,皆不實之詞,但說他因“修道而養(yǎng)壽”則為可信。
二、《老子》其書及版本
(一)《老子》一書相關(guān)問題
《老子》,又稱《道德經(jīng)》、《道德真經(jīng)》、《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國先秦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為其時諸子所共仰,是道家哲學(xué)思想的重要來源。道德經(jīng)分上下兩篇,原文上篇《德經(jīng)》、下篇《道經(jīng)》,不分章,后改為《道經(jīng)》三十七章在前,第三十八章之后為《德經(jīng)》,并分為八十一章。是中國歷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學(xué)著作。
梁啟超在評胡適《中國思想史大綱》時,用“六條證據(jù)”斷言《老子》一書出自戰(zhàn)國之末。其后,顧頡剛、錢穆、張壽林、張季同、羅根澤、馮友蘭、熊偉、張西堂等學(xué)者撰文,認定《老子》為戰(zhàn)國時書(見《古史辨》第四、六冊等)。他們所依據(jù)的不外乎是思想源流、時代精神、語體文風(fēng)、語言方式、流播方式、學(xué)者引述、民俗習(xí)慣等,以此判斷其為戰(zhàn)國時書。如梁啟超認為,老聃是一個拘謹守禮的人,與《五千言》中那種反禮的精神相悖,所以《老子》不像為老聃所書。老聃有一句話為:“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三十八章),似不可能是老子的話。并從《老子》中找出了“萬乘之君”、“取天下”、“仁義”等詞,認為不是春秋時人所能作,而是戰(zhàn)國時的用語,并認為《墨子》、《孟子》中未論及老子。羅根澤認為,《墨子》提出“尚賢”,而老子提出“不尚賢”,那么,“不尚賢”這一否定判斷不可能在“尚賢”之前出現(xiàn)。錢穆認為:“孔、墨均淺近,而老獨深遠;孔、墨均質(zhì)實,而老獨玄妙。以思想之進程言,老子斷當(dāng)在孔、墨之后。”另一些學(xué)者從文體上來論證《老子》,馮友蘭說《老子》是一種經(jīng)體,是戰(zhàn)國時的作品,不同于春秋時期的“對話體”(如《論語》)。而顧頡剛認為《老子》是賦體,是戰(zhàn)國時的新興文體。羅根澤和馮友蘭從私家著述的角度提出,戰(zhàn)國前無私家著作和私人著述等。上述看法幾乎剝奪了老子的著作權(quán)。
我們認為,或許正因為老子深知禮的弊端,才由知禮到反禮的;至于戰(zhàn)國詞語問題,是《老子》在流傳中后人的增益而已;“尚賢”在先秦文獻中不獨為墨子的專利;老子的“幽深”并不能說明其時代一定居孔、墨之后,因為誰也不敢說《易》不幽深;而且孟子未提到《老子》,不等于《老子》就必然不存在。因為,孟子也未提到《易》,而莊子也未提到《孟子》,這并不能證明《易》、《莊子》是偽作。至于文體,我們認為《老子》的節(jié)奏韻律更像是一種哲理詩的“詩體”,似更接近于《詩三百》的“詩體”。《詩三百》篇的“詩體”在春秋時期早已存在,為什么《老子》就一定要在戰(zhàn)國時期才能誕生呢?至于戰(zhàn)國以前無私家著作,私人著作當(dāng)自《論語》始的說法隨意性太大,經(jīng)不起推敲。當(dāng)然,認為《老子》一書成于春秋末,確是老子所作的學(xué)者也有不少,如胡適、唐蘭、郭沫若、呂思勉、高亨、陳鼓應(yīng)等(見《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輯)。他們堅持認為,《老子》出于老聃之手,是春秋末年老子出關(guān)時所寫的“五千言”。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呂思勉的意見,他在《先秦學(xué)術(shù)概論》中認為:“《老子》書辭義甚古,又全書之義,女權(quán)皆優(yōu)于男權(quán),俱足證其時代之早。”又在同頁注中指出:“全書皆三四言韻語,間有散句,蓋后人所加,與東周時代之散文,截然不同。一也。書中無男女字,但稱牝牡,足見其時之言語,尚多與后世殊科。二也。”并認為《老子》并非南方之學(xué),而是北方之學(xué)。
1973年,從馬王堆三號漢墓中發(fā)現(xiàn)了帛書《老子》的兩種抄本,世稱甲本和乙本(《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甲本字體處于篆隸書之間,不避“邦”字諱(漢高祖劉邦),所以,斷其抄寫年代當(dāng)在高帝之前。乙本字體是隸書即今體,避“邦”字諱,但仍用“盈”(惠帝)和“恒”(文帝)字,可見其抄寫年代應(yīng)在高帝時期,當(dāng)與甲本相隔不遠。甲本與乙本距今都已經(jīng)兩千多年,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老子》一書的抄本之一。《老子》帛書的發(fā)現(xiàn),證明了《老子》絕非漢代的作品,至少在秦代之前就已經(jīng)流傳。
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戰(zhàn)國楚墓大批竹簡(《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竹簡《老子》距今2300余年,是迄今為止最古老的抄本。不僅發(fā)現(xiàn)諸多不同于通行本的思想言述,而且將《老子》的年代比帛書《老子》往前推進了一百多年,推翻了老子成書“晚出說”,證明《老子》的時代起碼當(dāng)在戰(zhàn)國中期甚至更早。不妨說,依據(jù)《史記》和前人的考釋,以及新出土的郭店本《老子》,似乎可以基本肯定老子是春秋末期人,他擁有著上下篇五千言的《老子》的著作權(quán)。
因此,可以說,《老子》一書為老聃所著的私家著作,它并非對話體,而是一種哲學(xué)詩或詩性哲學(xué),在其流傳過程中,為后人所修改,其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時代老聃的思想。
(二)《老子》的版本
現(xiàn)存《老子》的版本,以帛書甲、乙本為最早。甲本文字,不避漢高祖劉邦諱,可證它是劉邦稱帝以前抄寫的。乙本避劉邦諱,但不避惠帝劉盈、文帝劉恒諱,可知它是劉邦稱帝以后,劉盈、劉恒為帝以前抄寫的。甲、乙本皆分二篇,乙本篇末標出《德》3041字,《道》2426字,合計5467字。甲本尾題殘缺不明。兩本都不分章次。
東漢時成書的《老子河上公章句》,分八十一章,上篇道經(jīng)三十七章,下篇德經(jīng)四十四章,河上本復(fù)于每章章次之首冠以“章題”二字。魏王弼《老子注》,只分八十一章,并無章題名稱。唐初傅奕校定《道德經(jīng)古本篇》,據(jù)宋代謝守灝《混元圣紀》記載:傅奕考核眾本,勘數(shù)其字。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安丘望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岳得之。其中項羽妾本迄今仍有相當(dāng)高的學(xué)術(shù)價值。另尚有題為西漢末嚴遵撰的《道德真經(jīng)指歸》,章句頗與諸本不同,今存殘本,但有人認為是后人偽托。
現(xiàn)存《老子》的版本,除漢初帛書本外,還有許多版本流傳。約略統(tǒng)計,石刻14種,其中以唐太宗時虞世南校寫的石刻《老子》為最古。其次為唐中宗景龍二年(708)易州龍興觀道德經(jīng)碑。唐寫本《老子》殘卷,散見于各地保存的敦煌經(jīng)卷中,為數(shù)頗多。今見木刻諸本中,以宋刊《老子道德經(jīng)河上公章句》為較古,商務(wù)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有影印本。明正統(tǒng)《道藏》搜集《道德經(jīng)》本文及漢、魏、唐、宋、金、元、明眾注本,總計有41種之多。
歷代學(xué)者研討和考釋《老子》的著作不下千百家,但存者少佚者多。其中主要有:
戰(zhàn)國末年,喜黃老刑名之學(xué)的韓非,最早著《解老》、《喻老》,西漢《老子鄰氏經(jīng)傳》、《老子傅氏經(jīng)說》、《老子徐氏經(jīng)說》以及《劉向說老子》等,均已散失。
東漢時,道教成立,河上公《老子章句》宣揚練氣可以久壽長存;《老子想爾注》強調(diào)學(xué)道練形,能致長生。魏晉時期,何晏作《老子道德經(jīng)》,王弼撰《老子注》,闡發(fā)以虛為主、以無為本的玄學(xué)觀念。
南北朝時,佛學(xué)和道教并盛,佛門亦耽玄理,釋氏注解《老子》的很多。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劉宋時,釋惠琳、釋惠嚴各注《老子道德經(jīng)》2卷,釋慧觀撰《老子義疏》1卷。《舊唐書·經(jīng)籍志》著錄:鳩摩羅什撰《老子注》2卷。梁武帝蕭衍篤信佛法,誓為佛門弟子,亦著《老子講疏》6卷。
唐代,因皇帝與老子同姓李氏,故大力提倡道教,設(shè)置崇玄學(xué),令生徒論習(xí)《道德經(jīng)》,道俗學(xué)人,先后注《老子》的名家有孫思邈、傅奕、尹知章、成玄英、唐明皇、李榮、強思齊、杜光庭等。強思齊《道德真經(jīng)玄德纂疏》20卷,以唐明皇御注并疏為主,集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注,成玄英和強思齊疏,彌補了成玄英《老子疏》已亡之缺。
宋代注解《老子》亦多名著,道士陳景元撰《道德真經(jīng)藏室纂微》10卷,范應(yīng)元撰《老子道德經(jīng)古本集注》2卷,有《續(xù)古逸叢書》影印宋刊本,明《道藏》未收。司馬光著《道德真經(jīng)論》,第一章無名、有名、無欲、有欲,皆于“無”與“有”字下斷句,與先儒不同。王安石喜讀《老子》,作《老子注》,第一章句讀與司馬光相同,但王安石闡釋“道”時,認為“道有體有用,體者,元氣之不動;用者,沖氣運行于天地之間”,以氣一元論解釋“道”。司馬光則認為“道生一”,道是虛無,即自無入有。王安石子王雱、同黨呂惠卿、陸佃、劉仲平皆有《老子注》。彭耜撰《道德真經(jīng)集注》18卷,所引注本,或存或亡。其臚列解老者諸姓名,亦為珍貴的史料。到了元代,吳澄作《老子注》,更定為六十八章,獨成一家言。明代焦竑撰《老子翼》,采集韓非以后解《老子》者64家,并附以焦氏《筆乘》,共成65家,各取精語,于諸家注中推為博贍而有理致。并附《考異》,識其異同。
清代畢沅撰《老子道德經(jīng)考異》,以唐傅奕授定本為底本,參校河上公、王弼、顧歡、陸德明、彭耜、《永樂大典》、焦竑《考異》等,間有不合于古者,則折中眾說,以定所是。但畢沅《考異》,詳于宋元諸本,忽于唐本。近人羅振玉針對畢沅這個缺陷,撰《道德經(jīng)考異》,他根據(jù)景龍本、開元御注本、廣明本、景福本等四個唐石刻本以及六朝和唐寫本殘卷10種撰成。他說,上下二經(jīng)八十一章中,未見唐抄者才四章耳。唐以后諸本,不復(fù)闌入,期與畢書相輔而行。這是該書的特色。羅本再加上馬王堆漢墓帛書本、焦竑和畢沅《考異》,則漢、唐、宋、元、明諸本《老子》文字的異同,都可以考定了。
現(xiàn)在的通行本是以王弼本為底本的。至于現(xiàn)代人的注本,可以參考的書籍比較多,如朱謙之的《老子校釋》,陳鼓應(yīng)的《老子注釋及評價》,陳松如的《老子說解》,劉笑敢的《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任繼愈的《老子繹讀》等。
老子是世界文化名人,故《老子》的外文譯本亦多。世界上《老子》譯本有260多種:德文有64種,英文有83種,法文有33種,荷蘭文19種,意大利文11種,日文10種,西班牙文10種,丹麥文6種,俄文、瑞典文、匈牙利文、波蘭文各4種,芬蘭文、捷克文各3種,冰島文2種,葡萄牙文、越南文、世界語各1種。(這是統(tǒng)計到20世紀80年代的數(shù)字),其海外發(fā)行量居中國傳統(tǒng)文化經(jīng)典之首,在國外翻譯出版的版本也很多。
從現(xiàn)有資料看,西方人開始真正接觸《道德經(jīng)》是19世紀。只有巴黎的保羅·佩里奧1912年撰文說,《道德經(jīng)》曾在7世紀譯成梵文,但無版本可尋。確切的資料表明,西方第一個譯本是1842年巴黎出版的斯坦尼斯拉斯·朱理安《老子道德經(jīng)》法文本。1870年萊比錫出版了維克多施特勞斯的《老子道德經(jīng)》,它是第一個德文譯本。1921年出版了衛(wèi)禮賢《老子道德經(jīng)》,學(xué)者認為這一本是比較忠于原文的德譯本。1884年倫敦出版的鮑爾費的《道書》是最早的英文譯本。1891年理雅各的《道書》譯本由牛津出版。1898年美國芝加哥出版的保羅·卡魯斯《老子道德經(jīng)》譯本,被認為是質(zhì)量較好的譯本。
20世紀初,老子思想在西方逐步傳開,普及程度較前有所提高。例如老沃爾特·高爾恩《老子譯本》1904年第一版,1913年第三版,1922年重印。1934年倫敦出版的亞琴·章利英譯本《道和德〈道德經(jīng)〉及其在中國思想中的地位研究》,對《道德經(jīng)》在西方的傳播有較大影響,重印過多次。由中國人自己翻譯的英文《道德經(jīng)》在西方有一定影響的主要是胡澤齡的譯本,1936年在成都出版。林語堂1948年在紐約出版了《老子智慧》。1959年初在倫敦出版了《道德經(jīng)》。《道德經(jīng)》譯本雖然很多,難以統(tǒng)計,學(xué)者認為譯文質(zhì)量較好,有重大影響的本子是詹文錫1963年在紐約出版的《老子之道》。還有1977年美國密執(zhí)安大學(xué)出版林保羅的《老子道德經(jīng)及王弼著英譯》。他在序言中說:“各種外文譯本已有70種至80種之多,而且至少是世界上每一種語言有一種譯本。”自1973年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出版以后,海外也掀起了一股研究老子熱。研究老子其人其書,各種注本及英文譯本大量出現(xiàn)。
三、老子的思想體系
《老子》以“道”解釋宇宙萬物的演變,含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老子哲學(xué)與古希臘哲學(xué)一起構(gòu)成了人類哲學(xué)的兩座高峰,老子也因其深邃的哲學(xué)思想而被尊為“中國哲學(xué)之父”。老子的思想被莊子所傳承,并與儒家和后來的佛家思想一起構(gòu)成了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內(nèi)核。
《老子》主要思想脈絡(luò):究天道立人事,立天道推人道,包含思想完整性,堅持深刻全面性,實現(xiàn)天之道與人之道的合一性,即獨異于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亦即老子說的“備天”思想。
老子道學(xué)理論是理論中的理論是哲學(xué),哲學(xué)中的哲學(xué)是科學(xué)——大道哲學(xué)。從大道哲學(xué)的視野出發(fā),老子道學(xué)的主要觀點:
(1)“道之為物”、“有物混成”(混成論)的宇宙萬物本體論。
(2)“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道生萬物(生成論)宇宙自然生態(tài)論。
(3)“象帝之先”的先見之明的認識論。
(4)大小不二、首后不二、內(nèi)外不二的異常深刻圓融的相對論。
(5)“執(zhí)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的逆向思維方法論。
(6)“修之于身”、“無欲,以觀其妙”、“有欲,以觀其徼”妙徼齊觀的“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審人事”的直覺類比的縝密觀察審證論。
(7)“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的宇宙萬物本源論。
以及“道法自然”、自然法于自然的理論;慈愛萬類,天下為公,天下一家的宇宙胸懷;天人合一、與道合真的理想追求(把獨異于人的老子天人合一觀概括為“五同性”思想:同源性、同構(gòu)性、同律性、同歸性、同一性);現(xiàn)實的理想天堂——地球天堂之理想;起點“和”、過程“和”、結(jié)果“和”的根本三和中態(tài)方法論;以“圣人恒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的本體立場;“修之于天下”的平民化圣人人格——人人可以超凡入圣,升華人生;“無為而無不為”——無為而治的正邦治國思想(道治、德治、仁治、義治、禮治、法治)六治合而為一的以正治邦,“以奇用兵”的萬不得已的兵治(是一套完整的辯證統(tǒng)一的安邦治國思想體系);“可以為天地母”——大道科學(xué)為一切科學(xué)之母。所以李約瑟說“內(nèi)在的未誕生的最充分意義上的科學(xué)”,實際上是“玄之又玄”與實之又實辯證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的最充分意義上的科學(xué)。
老子之道曲高和寡。《老子》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老子有預(yù)見性,懂得他的思想難為常人所解。
其實老子是在“黃帝之道,老子言之”,是黃帝破天荒提出“道”這個概念,作為老子自己的哲學(xué)思想體系的核心。它的涵義博大精深,可從歷史的角度來認識,也可從文學(xué)的方面去理解,還可從美學(xué)原理去探求,更應(yīng)從哲學(xué)體系的辯證法的方法論去思維。哲學(xué)家們在解釋“道”這一范疇時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認為它是一種物質(zhì)性的東西,是構(gòu)成宇宙萬物的元素;有的認為它是一種精神性的東西,同時也是產(chǎn)生宇宙萬物的泉源。不過在“道”的解釋中,學(xué)者們也有大致相同的認識,即認為它是運動變化的,而非僵化靜止的;而且宇宙萬物包括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的思維等一切運動,都是遵循“道”的規(guī)律而發(fā)展變化。
老子說“道”產(chǎn)生了天地萬物,但它不可以用語言來完整說明,而是非常深邃奧妙的,并不是可以輕而易舉地加以領(lǐng)會,這需要一個從“無”到“有”的循序漸進的過程。“道”是可以用言語來表述的,但是道就是不可固定于那個具體事物的那個“道”;也是說可以在具體的事物之中或也可在具體事物之外而變動不居。“名”如果可以用文辭去命名,那道就是恒“名”;但道有其捉摸不到的變化運動性,依其運動變化著的相應(yīng)特征事物也不是道的名字了,其所依附的法則是道、其名不再是道,為此,道隨其依附的作用性態(tài)不同,必須依其廣義上另取其名——即非恒名,依其所關(guān)聯(lián)在一體的事物就是相應(yīng)事物的名字了,如太陽、地球、人體等。“無”可以用來表述天地之道同物混沌未開之際的狀況,也可說“道”合化存在于事物的運化之中與之上,因為“無”太微小了,人們無法用肉眼見到與用手觸摸得著,而且“無”還在永無止息地在作功;而“有”則是宇宙中肯定存在著的萬物。因此,要常從“無”的過程中去觀察領(lǐng)悟“道”的奧妙;要常從“有”中去觀察體會“道”的端倪。無與有這兩者,來源相同而名稱相異,都可以稱之為玄妙、深遠。它不是一般的玄妙、深奧,而是玄妙又玄妙、深遠又深遠,是宇宙天地萬物之奧妙的命門,從“有名”的奧妙到達無形的奧妙,“道”是洞悉一切奧妙變化的門徑,是開啟人類智慧和探索自然奧妙的鑰匙,因為道的運化作功是周而復(fù)始的,其玄妙之門就是陰陽屬性的正能態(tài)同負能態(tài)相互作用的盈虧消長的位移循環(huán)不息,才能化生萬物的樞機(事物相互作用化生控制中心)。關(guān)于“道”的循行關(guān)系準則的理論,在老子以前就已經(jīng)有雛形了,老子應(yīng)是集大成者。是學(xué)者的使命感,關(guān)乎社會的運作,因此必須為道正名。這個道也就有廣義與狹義的了,而廣義的道認為是“大象無形”,應(yīng)以“執(zhí)大象”的方式才能把道執(zhí)掌操作,其“大象”屬于導(dǎo)向的宏觀邏輯意義,是告訴人們?nèi)绾蔚卣J識道和運用道的方法。而狹義的道是能夠具體運用的道。
老子認為,為學(xué)是求知識,為道是求智慧。真正的智慧是理性、邏輯的一種體驗方式,只有通過得“道”的方法才能悟到“道”。老子的“道”,與基督教的上帝是極其接近的概念,但拒絕了基督教上帝與神的完全虛無的迷信色調(diào),走上了具有自然科學(xué)的軌道上。道非人格化、非神的上帝化身,而上帝是人格化的、神圣化的,道是無可比的議題,講起來難度也就大了許多。“道”雖是哲學(xué)的概念,除用于表示規(guī)律、法則的含義之外,還有自然和社會事物中的運用之道,如地球的橢圓形運轉(zhuǎn)軌道、現(xiàn)代使用的信頻之道、各種事物的運輸之道、人體內(nèi)外的功信與物質(zhì)納新吐故之道,有了這些道的存在,世界才動了起來。否則無道的法則規(guī)范和現(xiàn)實的道的作用,世界人類無法進行功信和物質(zhì)的傳輸交流、交換和交易,則萬物無以生存運化。如果其前的哲學(xué)解辯,把道作超思維、超邏輯的泛虛釋義的話,很可能又把老子的道再一次地卷入唯心論的漩渦。單憑《老子》“無”的錯解就潛在著一種被神化的內(nèi)涵,一旦社會有了需要,它可以轉(zhuǎn)變?yōu)橐环N宗教的核心理念。例如在道學(xué)中,人們?yōu)榈赖姆椒òl(fā)展成為道教修行的方法,老子的《道德經(jīng)》演繹成道教各類迷信的經(jīng)書。很可惜的是老子在那時把“無”講得太含糊了,但不能求全責(zé)怪老子與老子的那個時代,責(zé)任在老子的后學(xué)們,不了解老子的道的真正底蘊,以致老子的智慧在目前還上不了稱為文明古國的科技雅堂。那就令人深思了。
“道”是黃帝及老子提出的哲學(xué)概念,而老子的哲學(xué)理論都是圍繞著“道”而展開的。過去幾十年,哲學(xué)界長期爭論老子的道是物質(zhì)還是精神,老子哲學(xué)是唯物論還是唯心論。其實老子的道既是物質(zhì)又是精神的有機合體,是“天地之始”、“萬物之母”、“人體始終”,即宇宙自然和人類社會的根本原理。老子的哲學(xué)是道物論,是“唯道是從”的道物辯證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