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國(guó)恩《出走記》東方文學(xué)名著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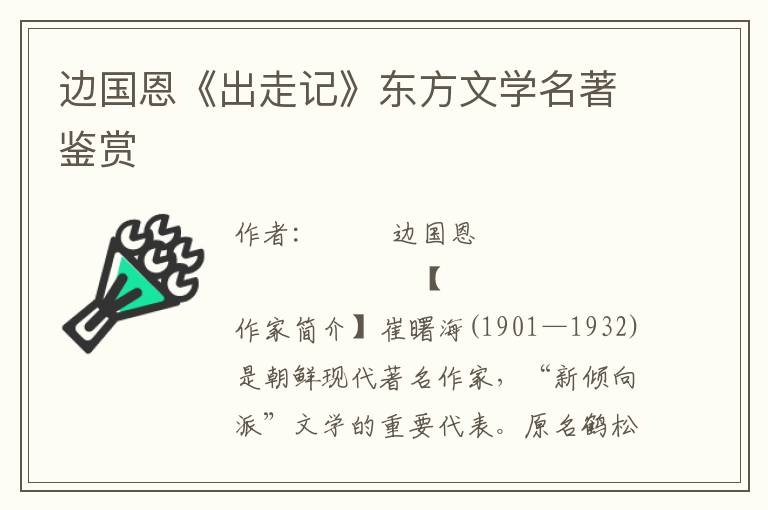
作者: 邊國(guó)恩
【作家簡(jiǎn)介】崔曙海(1901—1932)是朝鮮現(xiàn)代著名作家,“新傾向派”文學(xué)的重要代表。原名鶴松,1901年出生于咸鏡北道津郡(現(xiàn)名金策郡)的一個(gè)貧苦農(nóng)民家庭。早年喪父,與母相依為命,因交不起學(xué)費(fèi),只讀了3年小學(xué),他便中途輟學(xué)。為生活所迫,于1917年流浪到中國(guó)東北,做苦工,當(dāng)小販,飽嘗了人間的辛酸。在艱難竭蹶之中,他奮力拼搏,刻苦自學(xué),閱讀了大量的文學(xué)作品,深受日本小說家國(guó)木田獨(dú)步的作品和俄國(guó)文學(xué)作品的影響而走上文學(xué)創(chuàng)作道路。
1923年,他返回祖國(guó),參加于1922年成立的朝鮮第一個(gè)無產(chǎn)階級(jí)文藝團(tuán)體“焰群社”(即“新傾向派”)的活動(dòng),并成為最優(yōu)秀的代表之一,隨后,在《朝鮮文壇》雜志上發(fā)表自傳體短篇小說《故國(guó)》(1924)。1925年,他與趙明熙、李箕永等人發(fā)起成立“朝鮮無產(chǎn)階級(jí)藝術(shù)同盟”(簡(jiǎn)稱“卡普”),并積極投入創(chuàng)作活動(dòng),相繼發(fā)表了《出走記》、《樸石之死》、《饑餓與殺戮》、《大水之后》等短篇小說。這些作品大多反映朝鮮人民的痛苦生活,揭露反動(dòng)統(tǒng)治階級(jí)的罪惡,以生動(dòng)的形象來表現(xiàn)生活,因而崔曙海也就成為當(dāng)時(shí)朝鮮文壇上“新傾向派”的中堅(jiān)作家。他的短篇小說《出走記》被視為“新傾向派”的典型作品,也是作家的代表作。爾后,崔曙海又寫了《血痕》、《紅焰》等數(shù)十個(gè)短篇小說,匯編在《血痕》、《紅焰》兩個(gè)短篇小說集里。1927年以后,他還寫了一些文藝評(píng)論文章,如《勞動(dòng)大眾與文藝運(yùn)動(dòng)》、《文藝與時(shí)代》、《內(nèi)容與技巧》等。
與同期作家相比,崔曙海在藝術(shù)上的突出個(gè)性主要是:善于塑造個(gè)性鮮明、形象生動(dòng)的普通勞動(dòng)者的典型;擅長(zhǎng)通過景物的描寫來渲染氣氛和烘托主題,收到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情景交融的最佳效果,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現(xiàn)代朝鮮文學(xué)史上,是崔曙海第一次成功地在其代表作《出走記》中塑造了已經(jīng)覺悟、具有反抗精神的勞動(dòng)者的形象,對(duì)當(dāng)時(shí)和日后的朝鮮文學(xué)產(chǎn)生了直接的影響,為他以后的作家提供了寶貴的藝術(shù)借鑒。他與其他“新傾向派”代表作家一起,被譽(yù)為朝鮮無產(chǎn)階級(jí)文學(xué)的先驅(qū)。
《出走記》,李圭海譯,載《崔曙海小說集》,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9年出版。
【內(nèi)容提要】金君!每次信你都這樣關(guān)心我全家,使我感激萬(wàn)分。然而我不能聽從你的忠告,因?yàn)榈谌呤求w會(huì)不到萬(wàn)一的。現(xiàn)在我就把我離家出走的理由告訴你。
我背井離鄉(xiāng)已經(jīng)5年了。那時(shí)我扶老攜幼來到間島(即中國(guó)東北)。到間島還沒過一個(gè)月,險(xiǎn)惡的風(fēng)浪就無情地?fù)湎蛭壹襾砹耍悍N地?zé)o錢去買,只好租種中國(guó)人的田地,到頭來仍舊是赤貧如洗。我終于被逼上了街頭,跑遍了大街小巷替人家修炕、砌灶,勉強(qiáng)餬口。修炕的生意也時(shí)斷時(shí)續(xù),靠它是過不了日子的,無奈,年邁的母親只好去砍柴,妻子替人家春米。看到這般情景,我的眼淚奪眶而出。母親和妻子挨餓,還要受到人家的蔑視,我真難過極了。我每次打工回來遲了,母親總是眼淚汪汪地這樣說:“怕今天要餓壞啦,……我能夠看到你不愁兩餐飯,死了也瞑目啦。”妻子總是沉默不語(yǔ),大事小事都依著我。這更使我可憐她,心想,“我連起碼的生計(jì)的把握也沒有,為什么要討老婆呢?”過去我還置信“勤勉招福”這句金玉良言,現(xiàn)在我可不信它了。我家三口誰(shuí)不勤勉呢?可是貧窮一天天加重。有一件永遠(yuǎn)不能使我忘記也是我有愧良心的事:一次,大著肚子的妻子在廚房偷吃東西。當(dāng)時(shí)我見到她時(shí),“妻子,一句也不響,非常尷尬,垂頭喪氣地坐在那里,嘆了幾聲,臉上微紅,向外走出去了。”等妻子走出,我到灶口,找到了一塊桔子皮,“皮上的牙齒印還歷歷可數(shù)。”“金君!……拾起路上的桔子皮來充饑,可見她是餓到了什么地步!如何地渴望吃到點(diǎn)東西!何況她是懷孕的人呢?”
金君!我做過大頭魚的生意,還做過豆腐生意。在做豆腐生意時(shí),我的孩子降生了,可就別提我多么悲痛、悽慘、焦躁了。一邊是豆?jié){凝結(jié)不成豆腐,一邊是孩子哇哇地哭著要吃奶,“母親只管捶胸哭個(gè)不休,妻子也垂頭喪氣,差點(diǎn)兒哭出來。”我想,“這樣的生活,真不配有孩子。”
不管怎樣苦,還得做豆腐生意,可是沒柴禾,就得拿鐮刀背著山主人去上山砍柴。黃昏時(shí)分上山,夜深人靜背柴下山,“妻子用頭頂著,我背著,在漆黑的深夜,從山腳斜坡路上走下來。有時(shí),滑了腳,撞在石頭上,翻了跟頭跌倒在柴捆底下。妻子一聲不響地把頭上的柴捆放下,把壓在柴捆底下掙扎著的我,用盡力氣攙扶起來……”“母親背了孩子早已來到山腳下,瑟瑟地戰(zhàn)抖著等著我們了。”鄰居們譏笑我們,有時(shí)山主還到警察局去控告我們偷柴。那些警察便不問青紅皂白,就到“我家來搜查、追問,以至于打人。然而,我沒處訴苦。”
“金君!我真想拿起寒光閃閃的利刃把家小一個(gè)個(gè)的殺死,免得她們活一天受一天的罪,連我也自盡了事;要不然,做個(gè)藏刀行竊的強(qiáng)盜。”可就在這時(shí),我感覺到有一種思想在我腦海里醞釀著,“它像春草的萌芽一樣在我的腦海里逐漸滋長(zhǎng)起來。”“我在已往的人生過程中對(duì)社會(huì)是誠(chéng)實(shí)的……然而社會(huì)辜負(fù)了我們,不但沒接受我們的忠誠(chéng),反而以侮辱、蔑視、虐待來對(duì)待我們。我們是受了它的騙了。……我們活到今天并不是自由的,而成了某種險(xiǎn)惡的社會(huì)制度的犧牲品。”“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先要活下去。……打垮造成這個(gè)險(xiǎn)惡環(huán)境的源流。”基于這樣的思想,使我脫離家庭,拋下妻兒老小,“前往比絕壁更加險(xiǎn)惡的X線陣地去”。
“金君!……我是有良心的人,……從我離家那一天起,家小更要陷入到水深火熱的窮境里去。……她們總有一天連鬼也不知道地會(huì)餓死在雪地里或泥坑里。”想到這些,我的熱淚直淌,心痛欲碎了。但掉淚有什么用,天大的痛苦也要忍耐下去,要和它搏斗。“金君!這就是我出走家庭的大概情況。”
【作品鑒賞】“家庭”,這個(gè)人類社會(huì)的細(xì)胞,多么親切,又多么珍貴。然而,在舊社會(huì)每個(gè)家庭卻不一樣: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的。《出走記》的主人公樸君的家的的確確是不幸的。小說就是以主人公向摯友金君來函作答的方式,生動(dòng)地描寫了樸君離家出走踏上革命道路的原委,詳盡地展現(xiàn)了樸君家庭的不幸。作品宛如一幅筆力蒼勁,色彩濃重的水墨畫,透過那些貧困、憤懣、悲壯氛圍的畫面,隱約看到主人公斑斑血跡,道道傷痕,窺見吃人的舊社會(huì)的兇殘,同時(shí)也看到了天下的窮苦人在血泊中掙扎出來,朝著光明的新世界奮力挺進(jìn)的身影。
樸君原是一個(gè)勤勞、憨厚,“對(duì)未來抱著希望、憧憬著新的世界”的人,但在災(zāi)難深重的朝鮮,他已無法忍受日本殖民主義的重壓和本國(guó)剝削階級(jí)的盤剝,為了不使家庭毀滅,扶母攜妻來到間島(中國(guó)東北)。但是,在異鄉(xiāng)的幾年中,這個(gè)“家庭的棟梁”“無力養(yǎng)活家口”。他租不到田地,也找不到工作。為不使全家喪生,只好替人修炕、打短工、做零活……“勉強(qiáng)餬口”。堂堂五尺漢子,連家口都養(yǎng)活不了,為此,樸君哭過多次。他說:“我也是人,是有感情的人,對(duì)于我愛之如命的自己家庭遭受蹂躪,我怎能無動(dòng)于衷呢?!”一直把“勤勉招福”當(dāng)作金玉良言的樸君,憑著自己的一身力氣,砍柴、割草、打馬料、做大頭魚生意、磨豆腐……樣樣臟活重活都干,只求個(gè)溫飽。可是,就這么拼死拼活地掙扎,還是不能茍延全家的性命。“充滿著生氣”的樸君,“理想化成了泡影”,“日子卻過得一天比一天困難”。“接連兩三天挨餓的情形已不僅是一次兩次了。”秋去冬來,春過夏至,苦難的日子沒個(gè)盡頭。尤其使人慘不忍睹的是懷孕的妻子在灶火旁偷吃撿回家的桔皮。他“拿著桔皮的手顫抖起來,看著牙印的眼睛潮濕了。”他難過,他慚愧,他凄惋,“為什么還要埋怨這樣的妻子呢?像我這樣沒有良心的家伙哪里有呢?”他慚愧極了,覺得“沒有什么面目去見妻子”,不時(shí)地痛哭起來。回憶起妻子自從嫁到他家,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白天黑夜,風(fēng)里雨里,春夏秋冬不停地干啊干。“眼淚一滴滴地落在地上”,裙帶濕了又干,干了又濕。分娩幾天的妻子同他一起推磨,砍柴,費(fèi)勁地把柴頂著回來。“母親不知什么時(shí)候早已背著孩子等在那里,身子凍得簌簌地發(fā)抖”,嘴里說:“現(xiàn)在才來,我以為又……”
是啊,在死亡線上煎熬的樸君一家,何時(shí)才能見到天日?他們勤勞,卻不能維持生計(jì);他們誠(chéng)實(shí),但換不回溫飽,真是“上天無路,入地?zé)o門”。社會(huì)逼他全家到這般地步,對(duì)于樸君一家,對(duì)于全世界的受苦人,就如同樸君所說“或者是拿起刮刀連我在內(nèi)把一家都?xì)⒐猓獾迷僖惶焯焓茏铮换蛘呤悄闷鹂斓冻鋈プ鰪?qiáng)盜,免得再挨餓。”但樸君既未自殺,也未去做賊行兇,而是選擇了另外一條路——痛徹肺腑出走,踏上革命的征途。
每當(dāng)他回憶往事,獨(dú)自思考時(shí),總有一種思想在腦海里萌動(dòng),就像春草一樣的萌芽在滋長(zhǎng)著。他痛切地感到:就勤勉和良心而論,沒有誰(shuí)能比上他一家,然而“社會(huì)欺騙了我們,社會(huì)拒絕了我們的忠實(shí),相反,卻侮辱、蔑視、虐待了我們。”為了“履行這個(gè)時(shí)代的民眾的義務(wù)”,他覺得“哭泣,已經(jīng)為時(shí)過晚了;悲哀,只是表明我們過分懦弱,”便毅然作出抉擇,踏上拯救社會(huì)的革命道路。
小說突出的特色是在矛盾沖突中發(fā)展情節(jié)。作品雖短,容量有限,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受到局限,但作者取長(zhǎng)避短,合理安排情節(jié),避免了這種體裁帶來的局限。作者從富有典型意義的生活中截取某一橫斷面,把為數(shù)不多的兩三個(gè)主要人物集中在一個(gè)特定的環(huán)境中,利用主人公的思想斗爭(zhēng)的激烈,內(nèi)心世界的復(fù)雜推進(jìn)情節(jié)的發(fā)展。
細(xì)節(jié)的描寫是小說的又一特色。雨果曾說過,人心是藝術(shù)的基礎(chǔ)。正是因?yàn)樽髡咧O熟人的心靈,懂得人物的內(nèi)心活動(dòng)在作品中的地位,他才能夠純熟地運(yùn)用這一手法收到使人難忘的藝術(shù)效果。
一天,樸君看見妻子在廚房里吃什么,“看到我時(shí)嚇一跳,很快就把手里拿著的東西丟到灶洞里去了。這時(shí)候,我心中感到一陣不快”。這個(gè)細(xì)節(jié)描寫,令人聯(lián)想到許多,全家人已經(jīng)餓了三天,樸妻居然在廚房里偷吃東西,自然會(huì)引起對(duì)她的懷疑、怨恨和憎惡來。但在灶洞里撥翻,發(fā)現(xiàn)的竟是一塊留著牙印的桔皮。這一細(xì)節(jié)襯出樸妻的可愛之處。樸君怎能不慚愧,不怨恨自己,不流淚呢?
上山砍柴這一細(xì)節(jié)也是催人淚下的。窮困中的夫婦在危難之時(shí)互相體貼之情躍然紙上:“妻子用頭頂著,我背著,在漆黑的深夜,從山腳斜坡路上走下來。有時(shí),滑了腳,撞在石頭上,翻了跟斗跌倒在柴捆底下。妻子一聲不響地把頭上的柴捆放下,把壓在柴捆底下掙扎著的我用盡力氣攙扶起來。……”乍看上去,這一細(xì)節(jié)好像是在說明,其實(shí)是寫他們生活之艱難,也同樣有助于深化作品的主題。
小說以主人公向摯友來函作答的形式,讀來質(zhì)樸、自然,但在悲劇主題中蘊(yùn)含了作者對(duì)舊社會(huì)的悲憤控訴和有力批判。所有這些,都顯示了崔曙海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