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王祥夫先生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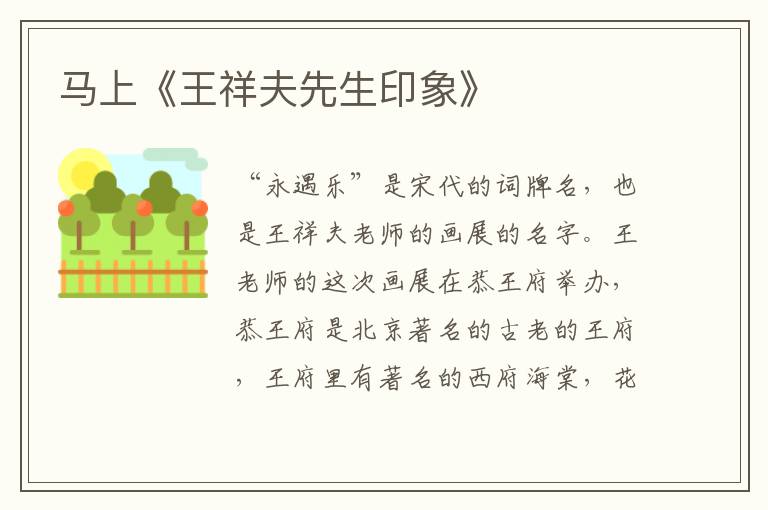
“永遇樂”是宋代的詞牌名,也是王祥夫老師的畫展的名字。
王老師的這次畫展在恭王府舉辦,恭王府是北京著名的古老的王府,王府里有著名的西府海棠,花開時節(jié),一派錦繡。
第一次見到王先生便是在恭王府。那天北京真是很熱,且因剛剛下過雨,又很潮濕,王府中后花園里一片蟬鳴,簡直是震耳欲聾。
因為游人多,我在游人里擠來擠去,幾乎是一路小跑來到了安善堂。因為是第一次和王先生見面,又因為遲到,我有點害羞,一進(jìn)展廳就忙著看畫。剛看幾幅,遠(yuǎn)遠(yuǎn)看見一個黑墨鏡戴著帽子的中年人走來,步速不快,走起來卻十分有氣場,是王先生。
王先生也已經(jīng)看見了我們。他對我們說:“天太熱了,我們到外面坐會兒。”于是我們到外面長廊聊天,準(zhǔn)確地說,是我在聽他和其他朋友聊天。
說話間天色漸晚,我們便去了附近飯店。吃飯間, 我只看王先生,看他吃菜喝酒。王先生可以說是酒豪,兩杯白酒下肚,本來就紅的臉,更紅潤了,連鼻尖都紅了起來。我想他要是生起氣來,表情會像《紅胡子》里的三船敏郎,瞪著眼睛。但是王先生平時脾氣很好,而他那天的心情就更好。
席間,我們挨著坐,因為我自幼學(xué)畫,后來大學(xué)改學(xué)電影,大家一邊說話一邊喝酒一邊聊文學(xué),我不怎么敢插話,于是我只好聊自以為比較擅長的電影。我們從國內(nèi)當(dāng)下的電影聊到意大利新現(xiàn)實主義,從《紅高粱》聊到《都靈之馬》,我驚奇地發(fā)現(xiàn)王祥夫先生的電影修養(yǎng)高深,讓自詡學(xué)了十幾年電影的我汗顏。
看畫,品茶喝酒,真是相見歡,相見恨晚。酒逢知己,我們便都喝了不少,但是誰都沒醉,帶著些許酒意,我們來到王先生住處,向他求字。賓館無筆墨,于是我開始翻弄自己的書包,找出一支方便毛筆來,王先生眼尖,看見我書包里鼓鼓囊囊一堆東西:“你書包里都帶了什么?”
于是我把書包里的東西一樣一樣掏出來。一個塑料鉛筆盒,里面有英雄鋼筆一支、紅色水彩筆一支、自動鉛筆一支、印章一枚、削筆刀一把、鉛筆若干,筆記本電腦一臺、皮質(zhì)手賬本兩本,其中一本夾了一支毛筆,另一本夾了護(hù)照,兩本都是鼓鼓囊囊的,感覺本子要從皮套里掙脫出來。那天恰好帶了兩本書,一本厚得像字典的《古樂之美》,另一本是《悲劇的誕生》,尼采的書里還夾了一個鍍銅的書簽,書簽的一半露在外頭。
我把這些東西掏出來,一一擺在桌上,
王先生忽然笑起來:“這是我看過的裝備最全的,太有意思了!我要寫一篇小說,就叫《馬上》。”
我當(dāng)時想,我在王先生筆下又會是什么模樣呢?
王祥夫先生屬于那種入世很深作家,他的作品似乎都是入世的,他經(jīng)常畫的也往往是生活常見之物:蘿卜、鱸魚、青筍,但他的畫意又是超脫的,出世的。在大家都在紛紛做加法的時候,他似乎在忙著做減法,他的畫作和他的短篇小說一樣,總是用筆墨很少,是寥寥幾筆,卻禪意無窮。借用南懷瑾大師的話說,應(yīng)該是: “三千年讀史,不外功名利祿;九萬里悟道,終歸詩酒田園。”
我是學(xué)畫的,又喜歡文學(xué),恭王府看他的畫,我真是高興,后來又讀他的小說,還是高興,后來,我們竟然很長時間沒見面,但一直靠文字往來。我寫小說,往往想著電影,我做電影,往往又想著小說。好像是,做了很多漫無目的的事情,讀了很多看起來無用的書,但是現(xiàn)在看起來,所有走過的路都不是徒勞,而讀過的每一本書都不是無用的。我把打印出來的小說初稿拿給王先生看,王祥夫先生竟然是我的第一個讀者,他說我的小說是“正如你自己說,細(xì)節(jié)少了一些。總體說,風(fēng)格是新的”。王先生這么說,我高興,也清楚他是在鼓勵我。
我經(jīng)常想,也許是今年,或許是明年,我們再去恭王府那里坐坐,喝喝茶,在海棠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