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瑋《吉狄馬加:土地和生命的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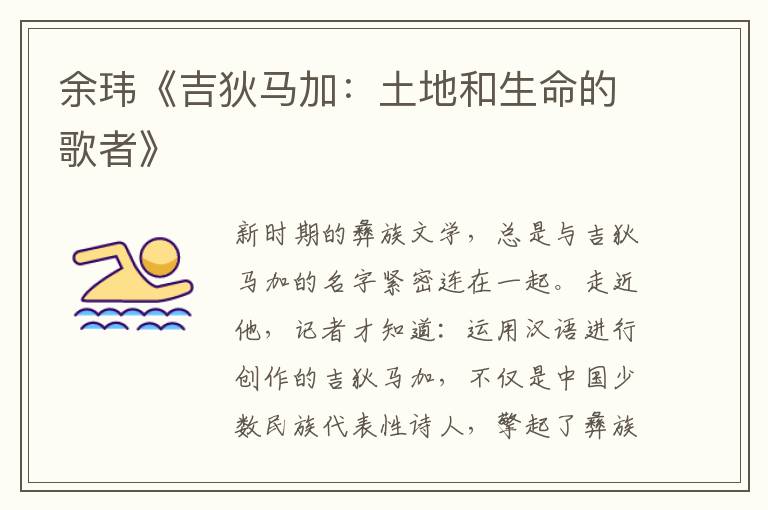
新時期的彝族文學,總是與吉狄馬加的名字緊密連在一起。走近他,記者才知道:運用漢語進行創作的吉狄馬加,不僅是中國少數民族代表性詩人,擎起了彝族新時期文學史上的第一面大旗,同時他也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國際性詩人。與他聊天,濃濃的詩人氣質撲臉而至,一個彝人漢子豪爽和率真的“鋒芒”畢露。難怪著名詩人流沙河說:“吉狄馬加的詩使我驚奇,使我看見靈魂在跳舞。”
他肥肥的身子坐靠、更確切地是陷在沙發上。或雙目閉合地沉思,或激情飛揚地暢談,很有氣場,整個講述充滿詩性,顯然他是一個感情豐沛的人。與他侃詩,讓人回到自己的文青歲月。他坦陳:“詩歌創作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精神活動,我想我只要活在這個世界,詩歌就是我生命的一種存在方式。換一種方式說,我的生命中不能沒有詩。”在記者心目中,吉狄馬加就是一個嫁給詩的男人。
根深深潛植于大涼山的土壤
剛一落座,記者就提出如何稱呼他為好。吉狄馬加笑言:“我們的名字一般是父子連名。我的全名是吉狄·略且·馬加拉格,簡稱吉狄馬加,把我父親的名字省了。我姓吉狄,名馬加。名字就是一個符號,你喊我馬加就行,這樣方便一些。”
彝族支系繁多,吉狄馬加說他們自稱“諾蘇”族,解放前彝族被稱為“夷族”,“毛主席在北京會見彝族代表時提到民族名稱不統一,其中‘夷族’泛指很廣,提出把‘夷’字改為‘彝’字。毛主席認為鼎彝是宮殿里放東西的,房子下面有‘米’又有‘系’,有吃有穿,代表日子富裕,大家聽了很滿意,一致表示贊成。從此,‘彝族’就被正式定為彝族各支系的統一族稱。”
吉狄馬加的故鄉在四川大涼山,那里森林密布,江河縱橫。有人說,“那是一個春天永遠棲息的地方”。吉狄馬加說:“我生活在四川的大小涼山,那是一個彝族居住區。如果沒有大涼山和我的民族,就不會有我這個詩人。”對吉狄馬加來說,他的大部分創作靈感來自大涼山。
小時候,他經常游走于大自然和城鎮之間,有時盤桓于山巔、村寨,或到瓦板房下、到火塘旁,和彝人飲酒歌唱。在積淀感覺的過程中,他會突然感到心靈的震動,找到那個詩魂和彝魂的結合點。在只有16歲的時候,他就會用詩句表達對故鄉的贊美、對大自然的熱愛。他在彝語和漢語中,同時找到了語言中最為精妙的美。
“當時‘文化大革命’剛要結束,要找到一些很好的詩來讀幾乎是不可能的。那個時候我得到的第一個外國詩人的作品就是普希金的詩。很偶然得到這樣一本詩集……當時讀著普希金的詩,我大概只有16歲,讀后非常震驚。他所表達的對自由、對愛情、對偉大的自然的贊頌,完全引起了我心靈的共鳴。”吉狄馬加強調,是讀普希金的詩集改變了自己,自那一天起立志當一個詩人。
1978年,吉狄馬加考入西南民族學院中文系。“大學改變了我人生的命運。從那個時候,我開始走上詩歌創作道路。”吉狄馬加說,當時大學圖書館的書很受同學的歡迎,像印度詩人泰戈爾的《飛鳥集》、《園丁集》、《吉檀迦利》等都不容易借到,這些書一旦被借出圖書館,要再回到圖書館是一個很難的過程。常常是一個同學借到,都會在他身邊要好的同學間相傳。在吉狄馬加的記憶里,在他上大學期間,圖書館的書在他身邊周轉的時間最多也就兩到三天。“那個時候又沒有復印機,又非常喜歡這些書,就只有買一個筆記本,自己用鋼筆來抄書。常常是挑燈夜戰,幾個小時幾個小時不停地抄書,手酸疼了,最多休息半個小時接著又抄。現在多年過去了,當年所抄的那些詩集已成了人生的一種財富。這樣一個抄寫閱讀的過程,在閱讀方面也留下了一種特殊的經歷,對自己日后的創作和寫作起到了作用,感覺非常美好。”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的一個精神復興的年代,也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年代。那時,通過詩歌來表達自己的精神追求和情懷,對于每一個年輕人來說都是一種夢想。“那個年代正是‘文革’的那10年,精神生活比較匱乏,要找到很多很好的文學讀物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到了西南民族學院的時候,我真正讀到很多重要的作家和詩人的作品,它們開啟了我重要的人生道路,我開始思考人的生存狀況,思考我們的國家、民族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所進行的歷史選擇和歷史創造。”
當年,從思想解放與意識形態啟蒙走出的中國先鋒朦朧詩人,其詩作晦澀難懂早已是文學評論界不爭的事實。細讀吉狄馬加早年的詩,有一小部分受到了朦朧詩的影響,吸收了朦朧詩的寫作技巧,但并非他的主體風格。吉狄馬加在這場詩歌創作探索中迅速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認同與表達方式——彝人的身份、直白敘事的詩性表達,抵達自己心中的圣地桃花源。如今,在他的詩里看到的幾乎都是最樸素、最簡練、最自然的詞匯:太陽、高山、原野、大地、翅膀、靈魂、歌謠……看似脫口而出,其實是經過長久的積累、沉淀和錘煉,組合出特別的魅力。
彝人是一個飽經磨難而又善良、強悍、頑強、有著火一樣情感的民族。火把節既是那個民族盛大狂歡的節日,更是他們世俗生活的象征性儀式與精神肖像。吉狄馬加的處女作就是發表在《四川日報》上的散文《火把的性格》。不久,《星星》詩刊推出了他的組詩。吉狄馬加,一個彝人的兒子,一個用心靈和生命歌唱的詩人,用他真實粗獷的歌聲編織著一個屬于自己、也屬于同樣痛苦而倔強的民族的頌歌與夢想。
從小在本民族文化的乳汁的哺育下成長起來,大涼山那種獨有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鑄就了吉狄馬加的文化性格。1982年大學畢業后,他重返故土,下決心“讓我的每一句話、每一首歌/都是這土地靈魂里最真實的回音”。他懷著滿腔熱情走進了四川省涼山州文聯,后來被選為擔任州文聯主席兼《涼山文學》主編。1985年,吉狄馬加為這片生育他養育他的土地唱出了《初戀的歌》,這歌聲如“一朵剛剛開放的花朵”,用“最深沉的思念”“獻給祖國母親的/最崇高的愛情”。他的這第一部詩集曾獲中國第三屆新詩獎,一時被詩壇界稱為黑馬級的新秀。1989年,他又用彝人崇拜的三原色為他深愛的人編織了一幅色彩斑斕的《一個彝人的夢想》。
“我寫詩,是為了表達自己真實的感情和心靈的感受。我發現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在感召著我。那個地方的河流、群山、鷹的影子,始終漂浮在我的詩中,那里是我的精神故鄉。那里的一切,都讓我雙眼含滿淚水。”步入詩壇以來,吉狄馬加一直把最深摯美好的情思獻給自己腳下的土地、自己的民族和偉大的祖國,禮贊土地、民族、祖國成了他詩創作的總主題。但是,他不滿足描繪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風景畫、風俗畫以表達鄉土愛、祖國愛,而是超越風物風情的吟贊,直寫生死、命運、心態。即使寫民族風俗、風物、風貌、風情,他也要超越表層描述而進入對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的深層思考,努力揭示彝人心靈、性格的本質特征。哪怕一條小路、一支口弦、一塊頭巾、一次邂逅、一句土語、一曲歌謠、一頂草帽……乃至于一根繡花針,一抹黃昏的余光,也會在他心中激涌起愛的波瀾,晶析出愛的詩行,使得他的“每一句詩/每一個標點/都是從這土地藍色的血管里流出”。在創作中,他時刻不忘: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應該到哪里去?
吉狄馬加是由一個漢族保姆帶大的。他從漢族保姆的“身上和靈魂里,第一次感受到了/那超越了一切種族的、屬于人類最崇高的感情”,使他從小就相信:“人活在世上都是兄弟。”后來,他又廣泛接受了彝族、漢族和其他多民族文學文化的滋養和哺育,所以他一開始寫作就有一種寬廣博大的人類情懷。
創作路上,吉狄馬加一直感恩艾青對自己的影響。“他對于人民與歷史的深切關懷,直到現在都影響著我的詩歌創作。”對吉狄馬加而言,詩歌的出發點永遠應該是人的心靈。“我不可能去寫什么‘命題詩’,詩人要忠于自己的內心和靈魂,否則他的詩歌無法感動他人。”在此之外,必要的道德法則與深邃思想也是他的寫作基準,三者共同構成了他作品的力量。
詩而優則仕。吉狄馬加的社會身份一次次開始發生變化,這個變化有時讓人容易忽略其詩的存在,忽略他作為一個優秀詩人的事實。1991年,30歲的他任四川省作家協會副主席。1995年,吉狄馬加告別故鄉來到北京,擔任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兼辦公廳主任兼《民族文學》主編,這期間還當選為全國青聯副主席。但是,真正的鐵桿讀者沒有將詩作者社會身份符號化而粗暴地對待其詩,而是一如既往地將吉狄馬加列入“遇詩必讀”的名單中。
身為少數民族,吉狄馬加在生活中創作了許多帶有民族印記的作品,他也戲稱自己為“彝族精神文化代言人”。在作品《自畫像》中,末句是“世界,請聽我回答/我——是——彝——人”,振聾發聵。這詩句成了吉狄馬加作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代言人的宣言,他以詩歌的方式向世界傾訴歷史、傾訴民族文化。在寫作中,彝族文化與曾經生活的廣袤土地始終是他憑靠的文化背景。吉狄馬加說:“任何一個人,尤其是詩人,他和民族間精神的聯系、文化的聯系,和他生長的土地的聯系,就像嬰兒和母體的關系。這一點,對詩人是非常重要的。 作為我來說,我首先是一個來自彝民族的詩人,我又是一個中國詩人。自我身份認同的問題,在我的早期詩歌中能明顯看到,但我需要聲明的是,我寫作還有一個重要目標,就是通過寫我的民族來窺視人類普遍的價值,力求這些作品都具有人類意識。”
吉狄馬加無愧于是當代彝族詩歌的開拓者。在很長時間里,彝族詩歌徘徊在諺語和民間歌謠的階段。解放以來,雖然也不乏用現代散文語言寫詩的彝族人,但他們的筆調往往滯留在對新生活表面的輕快歡樂的歌唱,而吉狄馬加作為一個具有現代思想的詩人,為我們重新構建了一個旖旎的彝族詩歌王國。他的詩飽含著歷史的滄桑,體現出對彝族文化遭遇現代性的憂慮,對彝族文化未來的思索,將思想的觸角深入到了歷史文化的深處,從心靈深處叩響那個古老民族的歷史記憶。他以個性化的言說方式,把彝人的歷史文化、生存狀態和內心世界呈現給世人,使世人看到了一種古老文明的獨特,觸摸到一個偉大民族的高貴靈魂,為中國多民族詩壇提供了詩學新思維。有人說,吉狄馬加的出現,讓一個古老而神秘的民族形象在中國詩壇上站了起來。
以詩的方式與世界對話
二十多歲起,吉狄馬加就一直在文化界做行政領導工作。“2006年7月,作為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我被派到青海擔任管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和體育的副省長,應該說這個跨度是非常大的。后來,又任青海省委常委、宣傳部長。”
文人治省,令很多人拭目以待。吉狄馬加說:“我是以文人的身份從政,這樣的狀態在我看來很好。因為作為一個文人,會有文人精神,更具有人文關懷。雖然不是每一個詩人都具備從政的能力,但我發現,有作家這樣一個背景,工作時的內容就會更加實在,作家關注百姓,關注底層的生活;那我作為官員,普通人的命運、現實和民生,我關注!”
吉狄馬加赴任青海之前,不曾踏訪過這塊土。“我曾經從書本上知道青海的文化豐富厚重、源遠流長。當我來到高原之后,才切身體會到,這里的文化如此富有個性和魅力,如此多彩而生機勃勃,就像一場從古至今從未落幕的戲劇。我發現,青海是一個秘境。她的文化自信孕育在時空的博大之中。正如莊子所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似乎這正是對青海高原的一種哲學隱喻。”吉狄馬加說,青海最顯著的特點,在于它原始壯麗的自然之中蘊含的人類文明與文化,這種文化就像它生存的環境一樣,具有某種神秘性,或者說具有某種雖然古老卻又不失新鮮和活力的特殊性。“我認為,青海的文化創意和品牌打造就立足于這些自然和人文的特殊優勢。青海的經濟社會發展落后,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相對于內地,特別是東部地區、甚至是中部地區而言,它是后發站,或者說相對滯后一些,但在文化上它具有非常豐富的多樣文化。我一直有一個觀點,經濟的滯后不完全等于文化、旅游和體育事業的落后,相反,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往往是文化、旅游等資源富集的地區,同時也孕育了豐厚的民族文化。而且越是交通不便、貧困的地區,越保存著古老豐富的原生態文化,如果把文化產業發展和脫貧致富連接起來,既能夠傳承文化,也可以使文化的傳承得到回報。我想,對于我們這些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到那樣一個具有非常豐富的文化富礦的省份,發揮作用、展示才能,是組織上給的一次機遇。”
作為黃河、長江、瀾滄江的發源地,青海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總是吸引著人們的到來。在青海的那些年里,吉狄馬加為青海的推廣做了不少事,“利用我特殊的人文背景和知識,我對這里進行了文化創意”。為進一步促進世界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吉狄馬加到青海省任職后,創立了一個具有國際影響的詩歌節——青海湖國際詩歌節,用詩歌“打開青海通向世界的門扉”。他策劃和組織的“青海湖國際詩歌節”、“金藏羚羊國際詩歌獎”等詩歌活動,已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反響,成為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國際詩歌交流平臺之一,被波蘭作家協會主席、著名詩人馬雷克·瓦夫凱維奇譽為“一個東方的創舉”。
1997年,吉狄馬加參加了“哥倫比亞麥德林國際詩歌節”,那是南美最大的國際詩歌節,同時也是目前國際上影響最大的詩歌節之一。當時詩歌節的規模、主辦方對詩歌高度的責任感以及100多個參加詩歌節的詩人都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正是因為參加詩歌節,他立志回到中國后要創辦一個面向世界的詩歌節。青海湖國際詩歌節曾宣示:“我們站在離太陽最近的地方,向全世界的詩人們呼喚!”吉狄馬加說,因為詩歌,詩人們才從四面八方來到了這里;同樣是因為詩歌,我們才能把人類用不同語言和文字創造的詩歌奇跡,匯集在一起。
他在青海的文化創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五大主題類節日,除了唯一西方之外的國際詩歌節——青海湖國際詩歌節,還有三江源國際攝影節、世界山地紀錄片節、青海國際水與生命音樂之旅、青海國際唐卡藝術節。“我一直努力用青海特殊的資源、特殊的地位、特殊的文化,體現文化創意,吸引世界的目光,走出一條欠發達地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新路子。”正因為吉狄馬加的潛心策劃與全力推動,青海在文化創意和對外文化交流方面走在前列。
吉狄馬加在大涼山的峽谷里出生、成長,后來才有機會到大城市求學,廣泛接觸城市的現代生活和古今中外其他民族的精神文化,如饑似渴地閱讀中國和外國的從古到今各種流派風格的作家詩人的名著,還曾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成員到國外參觀訪問。不論走到哪里,為了充實、豐富、提高自己,為了借鑒別人,以便更好歌唱自己的故鄉和民族,為了找到并完美呈現出自己作為彝族詩人的藝術個性,他都廣泛接觸和拼命吸收。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屬于那個創造了十月太陽歷的古老民族,他時時想著“生我養我的故土”大涼山峽谷。他的詩充溢著一種獨有的氣息和特殊的韻味,使人感到是從滲透著民族氣質的靈魂里、從燃燒著民族精神的血管里自然流出來的。
中國作協主席鐵凝曾說,作為一位具有少數民族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詩人,吉狄馬加既以他對于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與民族風俗的描寫見長,同時他又不斷拓展自己創作的疆界,使他的筆觸穿越了狹小的地理空間,而獲得更為廣大的祖國與世界的視域。吉狄馬加對于推動中國詩歌的發展、促進中外詩人的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2006年5月,吉狄馬加被俄羅斯作家協會授予肖洛霍夫文學紀念獎章;2006年10月,保加利亞作家協會頒給他詩歌領域杰出貢獻證書;2012年5月,獲第20屆柔剛詩歌(成就)榮譽獎;2014年10月,被以“人民文化的捍衛者”的名義授予南非“姆基瓦人道主義獎”;2015年7月,獲第十六屆國際華人詩人筆會“中國詩魂獎”……此外,其作品單行本還被翻譯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意大利文、德文等文字在近30多個國家出版發行。圈內人都知道,只有出色的語言,才能經得起翻譯,因為翻譯非但不能“拔高”原作,還會使原作多少“打折”。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越走越寬越遠的吉狄馬加,收獲著其語言成就的一次又一次的肯定和證明。目前,他是當代中國詩人中,被國外翻譯得最多的一位詩人。
吉狄馬加曾應邀出席在漢城舉行的中國、韓國、土耳其三國作家的對話會,并在會上作了題為“在全球語境下超越國界的各民族文學的共同性”的發言。在發言中,他提出,今天的人類無論從政治上、經濟上,還是文化上,都面臨著許多共同問題,作家和詩人只有關注人類命運,才能寫出真正意義的具有人類意識的作品。“面對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作為人類精神文化代言人的作家和詩人,必須表明自己的嚴正立場,身體力行地捍衛人類各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其實,吉狄馬加一直力求以詩的形式顯現這些理念。在這次國際文學峰會上,他在演講中最后借用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的一句話作結:“要么我誰也不是,要么我就是一個民族。”
吉狄馬加是一位身在傳統和現代之間的詩人,一頭在民族,另一頭在世界。 曾有詩人這樣評價吉狄馬加,彝族的文化傳統,漢文字創作的文學經典,以及優秀的外國文學,都是他吸收的乳汁,毫無疑問,他是人類文明養育的兒子。在一個以漢語為主要流通語言的國度里,他選擇漢語作為自己的寫作語言,并通過漢語讀到了大量外國文學的譯作,由此獲得了最初的世界意識,再反過來作用于自己的寫作。正因為吉狄馬加具備了世界意識、民族意識,所以他才能夠在一個更大的背景和舞臺上得以彰顯。他不僅以自己的詩歌實踐從涼山走向了全國,走向了新時期中國詩壇的前沿,而且在詩歌中實現了與世界的對話;不但通過詩歌表達對于世界的關注,對于全人類的關懷,還以詩人的身份真正走向了世界,讓世界都聽到了這個彝人的聲音,讓世界在美學層面感知到了一個偉大的民族。
走在政壇與詩壇之間的“業余詩人”
在這么多年的創作生涯中,吉狄馬加對現實投以極大關注,并融入帶有濃郁民族性的思考。他的詩大都從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命運等人文角度入筆,側重于對于一個民族的精神內核與文化心理的打探,在傳承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上達到了相當的高度。談起自己的寫作立場時,吉狄馬加說:“彝人相信萬物平等,并存在微妙的聯系,人類在發展中不能破壞這種平衡。我一直認為,作家和詩人要在世界發展中起作用,要堅持、要揚棄的都會在我的作品里得到體現。”對于民族語言的日漸消逝,他表示憂慮:“語言消失的后果,并不簡單是沒人能說這種話。文化是藏在語言里的,這個民族用語言承載的東西,會隨著語言的丟失而永遠失去。”
吉狄馬加說:“我的詩歌對人的關注從未發生改變,它們從來都是從自己的內心出發,從不違背自己的良心。我不僅關注彝族人,也關注這世界上所有地域的每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作為一個詩人,如果沒有足夠廣闊的視野和胸懷來關注這個世界,他也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詩人。”
如今,吉狄馬加離開了他熱愛的土地,走出大涼山的他看到外面的世界時卻像一個想家的孩子,在學習和接受現代文明的同時,時刻銘記著自己的民族文化,他沒有忘記帶回現代化的精神滋養,帶回外界絢麗的文化色彩,將外來文化融入彝族文化的血液里。
仕途上,吉狄馬加一路豐收,一級高過一級的領導職務使他的詩歌創作變成了“永遠的業余”而無怨無悔。
吉狄馬加從小生活在一個干部家庭,父親擔任過故鄉布拖縣法院院長,后來又長期在自治州的公安交警部門擔任領導工作;母親擔任過衛生學校的校長和醫院的院長。“父母都是非常傳統的人。多少年來,我的母親總會不厭其煩地告訴我一定要好好工作,要到艱苦的地方去鍛煉自己,不要貪圖享受,人民的利益至高無上。同樣,我父親也是一個很正直的人,彝族人正直、勇敢、無私的品格在他身上都得到了充分體現。我父親還是一位非常人性化的人,我們之間的交流,常常就像是朋友。”
如何平衡詩人與官員這兩種身份?——這是吉狄馬加被問到最多的問題。詩人和官員,前者需要感性與熱烈,后者則要求理性和果敢,每個人都想知道他怎么將兩者相融。“曾任法國共產黨總書記的阿拉貢是著名現代派詩人,塞內加爾前總統桑戈爾也是第一流的詩人,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則是很優秀的劇作家……我從來沒有感覺到他們在從政的過程中和他們在寫詩的過程中有什么不協調。”對吉狄馬加來說,作為官員是他的工作分工,是一個公共職業,而詩人則是他一生都想保持的頭銜。“‘官’,說到底充當的是個服務員的角色,千萬別把自己當‘官’。詩人不是一個職業,只是一個角色,而政治工作可以作為一種職業。詩歌是我發自內心的東西,也是我對這個世界的傾訴方式,我希望一直被當成詩人。詩歌對我來說是永恒的歸宿。”
在他看來,詩人與政治家之間有很多共同之處,好的政治家和好的詩人都需要富有激情與想象。“想象能為政治家開辟政治之路,激發對社會更大、更有影響的思想,并最終落實到政治現實,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他同時認為,詩人往往最關注人類命運,政治家也需要關注人民福祉。“一個政治家,如果具有詩人的情懷,那么他應該會更關注民生,更關注這個社會的弱勢群體。”他認為,好的政治家和好的詩人,都應該對這個時代充滿著責任,關注人類的命運,關注社會進步和世界和平。而這兩者所有的目的在最終層面上也指向了同一個方向:為了使世界更加美好。對他而言,詩人與官員的雙重身份還有另一層意義:“作為一個詩人,對骯臟、違背道德的事物,或者是卑劣的政治手段會有天生的抗拒和唾棄,從而成為一種警惕和警覺。這對我來說是件好事。”
曾有人質疑吉狄馬加是體制內詩人,吉狄馬加坦言:“詩人是典型的個體精神勞動者,他的詩寫得好不好,跟所謂的體制內或者說體制外沒有一點關系。你的詩寫得不好,你說你是體制外的詩人,別人也不會承認你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他認為,詩人的精神勞動一定是個體的,每一個詩人都是獨立存在的。“我寫詩那么多年,我就從來沒有加入過哪個派別,或者說,想利用某種小圈子的力量來達到什么目的。詩人一定要有道德操守,一定要堅守自己的寫作原則。”
當下,詩歌在一定程度上被邊緣化。“詩歌在世界上從來不是主流;但是,像詩歌這樣一種既古老又年輕的藝術,是最接近人類心靈的一種表達方式。這樣一種表達方式,在任何時候都是需要的。我覺得,在今天,在物質生活越來越充實的時候,人類最渴望的還是要有自己的精神生活。相比于其他的文學形式,詩歌對人類凈化心靈的作用可能更簡單、更直接。”吉狄馬加深信,詩歌一定會找到屬于它的受眾。“很多注重精神生活體驗的人,不會放棄詩歌,會依然去熱愛詩歌。只要人類存在、只要人類美好的精神生活存在,對詩歌的閱讀、對詩歌需求也會存在。當然,我們還是要注重詩歌文化的宣傳。”
相對而言,少數民族詩人為公眾所廣為人知的極少。對此,吉狄馬加有自己的解釋:“很多少數民族詩人作品的發行范圍和流行方式,和現代許多詩人不一樣。少數民族詩人大多生活在邊遠地帶,很少參加這個流派、那個流派的活動。現在是個傳媒的時代,講究包裝、宣傳,但由于少數民族詩人生活在邊遠地區,只埋頭寫作,缺乏包裝、宣傳。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少數民族詩人的作品質量不如其他詩人,恰恰相反,他們的作品不浮躁,很純粹,更接近于詩的本質。 ”吉狄馬加有一個觀點,如果一個詩人和明星一樣,天天都待在一個很浮躁的地方,天天出現在聚光燈下,天天參加這樣那樣的活動,那么這個詩人離毀滅就不遠了。“真正的詩人,他在寫作時,靈魂和心靈都是寂寞的。我也是。”
“我一直非常忙,但是對經典的閱讀,對當代一些世界性作家的作品的閱讀卻從未停止過,我始終保持著閱讀的興趣。”閱讀與寫作之外的愛好于他不多,愛散步、聽音樂、練練字,偶爾與朋友一起品酒。雖然公務繁忙,但吉狄馬加并未輟筆,始終鐘情于繆斯。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前提下,他組織了一系列的全國性和國際性的詩歌創作、研討、采風、評獎活動。同時,他堅持業余寫作,不斷有新作、佳作發表。“詩人最重要的是不能停下自己的筆,寫詩對我而言不僅是生活方式,更是生命方式,是我一生追求的東西。創作詩歌是我對這個世界最深情的傾訴,作為一個彝族詩人,寫詩是我一生必須堅持的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