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華《品讀江西:湘東的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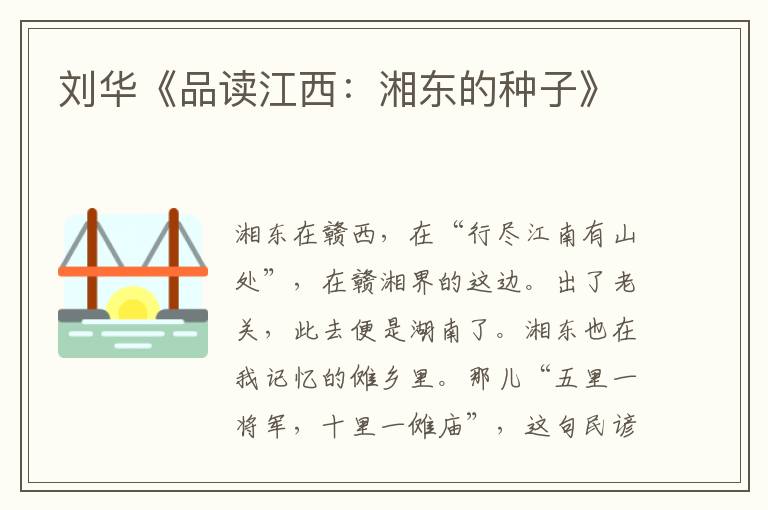
湘東在贛西,在“行盡江南有山處”,在贛湘界的這邊。出了老關,此去便是湖南了。
湘東也在我記憶的儺鄉里。那兒“五里一將軍,十里一儺廟”,這句民諺意在標榜萍水河畔儺廟遍布的奇麗景象。早些年我行走湘東,幾乎就是行走于一座座儺廟之間,行走于一尊尊儺像之間,行走于一支支儺隊之間,行走于一位位儺面具雕刻大師之間,他們中有毛園陳氏家族儺面雕刻的非遺傳承人陳團發陳全富父子,有彭國龍等多位杰出的民間藝人。我先后造訪過汶泉、明塘、下埠等村莊,汶泉習儺少年技藝之嫻熟,曾令我為傳承事感慨不已,明塘的掃堂儺儀古樸完整,竟讓隨行專家大開眼界,下埠儺在萍鄉的影響最大,其影響甚至進入了當地的語言生活,有歇后語道:“下埠的儺——面子大些。”湘東儺面具雕刻藝術堂而皇之地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而湘東區則名正言順地成為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到了湘東,我忍不住想吆喝一嗓子:民間文化依然活態存在的山野,才能夠算得上豐饒肥沃的土地!對吧?
湘東還在我的舌尖上。它是肥而不膩、香且又糯的臘肉。它是紋飾別致、味道甘美的花果。它是小覷四川、不讓湖南的辣椒。參觀排上鎮的南繁制種館,有一個火辣辣的數目字嗆著我了,那是1976年排上制種隊前往海南時留下的歷史記錄,隊員們隨身攜帶的物資以辣椒最為緊要,居然是每人十斤。那可是干的辣!紅彤彤的辣!叫人一把鼻涕一把淚的辣!
忍俊不禁之余,不由得怦然心動。依稀記起當年的海南制種,那是已經沉淀于我內心深處的一次國家大行動。置身南繁制種館,我才讀懂來龍去脈,我依稀記得的,乃上世紀70年代初、中期,雜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后,為了推廣種植,全國各水稻生產省(區)陸續在海南建立基地,開展雜交水稻繁育、制種,故而簡稱“南繁”。
十斤干辣椒的記載,喚醒了我的記憶。當年我下放所在的墾殖場,像周邊所有公社一樣,也必須派員奔赴海南。那時去往天涯海角一點也不浪漫,倒是充滿了瘴癘蟲蛇之懼、炎炎烈日之憂、臺風狂浪之惑,更何況往來不便、為期太長。場里決定抽調根紅苗壯且“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單身漢,響應者惟有一位剛剛入場的退伍軍人。可是,完成任務回來后,那剛強漢子絕口不提海南故事,也不知其究竟吃了多少苦遭過多少罪(萍鄉作家漆宇勤《候鳥》一文所寫的湘東繼父,也是這樣,“我反復詢問他制種是怎么回事,他先告訴了我父本母本的概念,然后就沒什么可說”;關于海南的熱,“繼父并未詳說”;關于農作的艱苦,“他只是淡淡地說”),我倒是發現退伍軍人此后養成了不管什么季節都緊扎褲腳的習慣。不過,我還能從墾殖場書記對待他的態度,間接感受到海南的辛勞、海南的煎熬。憨厚而儒善的書記每每遇見他,總是滿臉不無歉疚的難為情,連聲音都變了,輕輕的,親親的,像父親用語言小心地愛撫膝下后生曬黑的皮膚,療治他疲累且孤獨的心。
排上展示的南繁制種,已歷40年之久,蓬蓬勃勃一直延宕到如今。漫長的歲月一定有漫長的故事,那些故事一定可以編輯為厚厚的大書。它既是可圈可點的科學研究,也是可歌可泣的田間實踐;既是耐人尋味的珍貴往事,也是令人振奮的火熱現實。然而,身臨其境,我試圖追問的是,為何當年連我也知曉的國家行動,到頭來怎么就獨獨落在了排上的肩頭,怎么就能說“只要有水稻種植的地方,就有排上人生產的種子”,怎么就可以在排上造就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第一支種子生產專業隊伍?
排上娓娓道來。說的是“當驚世界殊”的種子革命。早在1970年代初期,在“世界成功利用水稻雜交優勢第一人”“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主導下,全國開展了秈型雜交水稻“三系”配套協作大會戰;而在萍鄉,由顏龍安領銜、多位湘東籍成員參與的研究團隊率先獲得成功,并立即運用于生產實踐;從1975年開始,萍鄉在全國率先組織人員奔赴海南大規模繁育、制種,經過長期努力,湘東的排上建立了全國規模最大的雜交水稻制種產業,從業人員6000多人,制種面積占全國南繁育種總面積的95%,制種業務拓展到全國各地,產品遠銷東南亞等十多個國家。
我更愿意通過一些細節感受當年,以便更加真切地逼近自己的追問。比如,制種隊員不無風趣地總結出了“海南十八怪”,什么“三只蚊子一盤菜,五只老鼠一麻袋;田螺吃禾比牛快,螞蟥又長又大當褲帶;男人騎牛車,女人學大寨;汽車跑得比火車快,老婆婆上樹比猴快;團魚海龜門板大,吃魚好比吃蔬菜”,如此等等,它既是風土人情的反映,也是生存環境的寫照;比如,海南各種自然災害肆虐,有的年份臺風過去暴雨即來,甚至海嘯接踵而至,以至于重災田塊顆粒無收,且有制種隊員在臺風中獻出了生命;比如,關于干辣椒的好處,制種隊老人回憶道:當年物資匱乏,想吃肉只有等過年,等萍鄉慰問大家送來的臘肉,然而,天氣太熱,臘肉也留不過一周,平時常吃的菜,就是干椒炒黃豆、干椒炒蘿卜皮、干椒燒魚干。如此看來,每人才十斤干辣椒,多乎哉?不多也。
原始落后的自然條件,苦不堪言的飲食起居生活,又臟又累且大強度、長時段的生產勞動,讓不少制種隊員難以承受。據說,制種期結束返鄉時,有人在海邊撿起石頭扔進瓊州海峽聊表決絕之意,誓不再還。難怪,當年萍鄉全市共有38個公社、4所科研所分別派出隊伍,后來僅剩排上隊一支獨苗;難怪,聲勢浩大的制種行動在我身邊卻是以制種人緊扎褲腳作結。
排上始終堅守海南,堅守制種基地,堅守種子們的初心。他們利用萍鄉的技術優勢,全面接管了眾多隊伍撤離后留下的基地。此后幾十年,候鳥般飛去飛來的排上制種人,不斷改革生產經營方式,直至抱團發展、組建公司,走向專業化、機械化、集約化、公司化經營,同時,積極開發雜交水稻新品種,創新生產工藝,擴大制種規模,使得排上成為能讓袁隆平院士欣然為之題字的“中國水稻制種之鄉”。與時俱進的一代代排上制種人,成為鄉村產業振興的“良種”。
追溯南繁制種的歷史,我記住了“野敗”不育株、48粒起源種子和有“英雄母親”之譽的“珍汕97A”,記住了顏龍安院士以及他的團隊,記住了這樣的褒獎:“如果說雜交水稻的締造者是袁隆平、顏龍安等水稻育種專家的話,那么將雜交水稻的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生產的,就是以張理高為首的排上制種隊。”排上,堪稱這場種子革命的開路先鋒!當然,我也記住了更多的后起之秀。其實,通過展出的那些紅頭文件,我想,不能忘懷的還有當年的組織指揮者。他們共同的作為,體現了往昔歲月的時代精神,那是“敢為人先、百折不撓、崇尚科學、求實創新”的湘東南繁精神之源頭。
往昔歲月的時代精神,并非僅僅只是遺產,它也可以成為財富,譬如在排上,它就是鄉村產業振興的獨特資源。由此,我想起水庫。讓今人受益的水庫大多建于上世紀中期,從前筑水庫,一聲號令便是四面八方,便是千軍萬馬,甚至自帶口糧,甚至義務勞動。水庫最能體現從前的時代精神;由此,我還想起遍及全省的墾殖場和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也是巧了,離開南繁制種館,便進了知青印象館,其中展出的也有墾殖場的歷史。
于是,我忽然發現,作為制種之鄉的湘東,真的善于繁育種子。它把民間文化的種子,播撒在0799藝術區里,播撒在麻山幸福景區,使之既得到保護、傳承的土壤,又享受著生長、發展的陽光雨露;它把紅色文化的種子,播撒在凱豐故居周圍,建起了凱豐生平業績展覽館、廉政文化教育館和智慧黨建體驗中心;甚至,傳統的工業陶瓷也是種子,湘東引進高端人才,建立科創中心,只為將其培育成產業振興的良種……
正是立冬。暖陽如春。我在湘東的山野間好奇地探訪著關于種子的傳奇。一些種子已收獲入庫。一些種子正繁育生長。一些種子卻懸掛枝頭。適宜繁育良種的地方,注定也是適宜良種落戶豐收的地方。我在田園里品過南豐蜜橘,又去山林間采摘廣豐馬家柚,沒想到,遠嫁他鄉的橘子柚子,滋味毫不遜色于原鄉。
哦,忘記問了,候鳥們應該又南下海南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