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勁松《防震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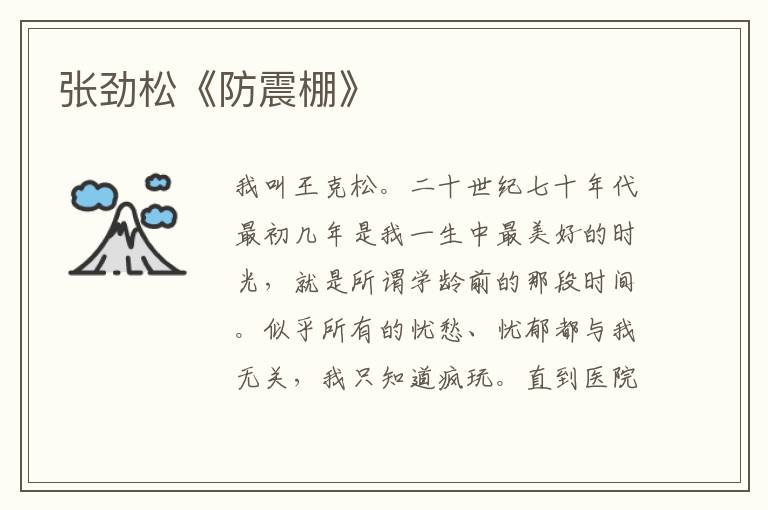
我叫王克松。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最初幾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就是所謂學齡前的那段時間。似乎所有的憂愁、憂郁都與我無關,我只知道瘋玩。
直到醫院家屬院里一座座的防震棚像雨后的蘑菇一樣冒出來,直到我和湯阿姨家成為鄰居,我無意間卷入了一起案子,我才覺得自己突然間長大成人。
那個夏天格外反常。一入夏竟然下起了秋天里才有的那種冰冷纏綿的雨,絲絲不斷,細膩悠長。在雨水的滋潤下,平地上長出了綠茸茸的苔蘚,家屬院里寬大的梧桐葉子未老先衰地流露出凋零的跡象,四處覓食的雞雛像剛學會游泳的鴨子,行走在綠色的水面上。陰雨過后,沒有一絲風的悶熱,像是把天地放在一口大鍋里持續地蒸煮。在蒸煮的日子里,上面下來了精神,要求“全民防震”。醫院伙房門前的大喇叭上連續播放了三天后,人們開始行動起來。伙房前面的小操場上,搭起了石棉瓦、油氈紙、舊帆布、塑料紙做頂棚的各式各樣的防震棚,各家各戶把縫紉機、柜子等貴重的家什都搬進棚子,白天在家里起火做飯,晚上到防震棚睡覺,大院里一時像臨時的軍營一般充滿了莫名的緊張和神秘。住防震棚的日子,同時也打破了一家一戶的隔閡,好像同在一片藍天下,同睡一張大通鋪的感覺,彼此沒有秘密可言。醫院的領導不知從哪里拉來了一臺廢棄的公交車,四個輪子沒有了,癱瘓的車身像是一排巨大的房子,作為醫院物資的貯藏室和治療室,白色的公交車身上畫上了大大的紅十字,車門上掛起了簾子。
我們的鄰居湯阿姨是醫院會計科的出納,是來自青島的洋學生,她的丈夫王哲是縣電影隊的放映員。王哲每到周末在縣工會的露天影院放電影,總是提前到大門口用三節電池的大手電,在人群中辨認我們這些醫院職工的孩子,給我們開后門放行,仿佛我們的臉就是五分錢一張的電影票,他的手電筒就是驗票機。在他的關照下,我們幾乎看遍了縣城里放映的所有電影。每當王哲走出家屬院去上班,我們都尊敬地敬一個禮,齊聲說道,大家不要擠,讓王哲叔叔先走。
王哲不光會放電影,還有一手木匠手藝。在這個夏天的連陰雨里,他剛剛搬到醫院家屬院來住,就給我家打了一個小柜子,用我家的木頭,他的手工。小柜子上面并排著三個抽屜,下面是兩扇門,一打開門涌出一股木頭新鮮的芳香。我父親把柜子搬回家,刷了清漆,鋪上了條絨的桌布,既當柜子又當桌子,成了那個時期我們家重要的一件家具。我記得有一尊石膏做的毛主席像站立在紅色的條絨桌布上,毛主席向我們全家親切地揮著大手。王哲家也有同樣的一個柜子。湯阿姨說,下雨天也放不了電影,他閑不住,做個柜子送給你們,也算是我們新鄰居的見面禮。我們兩家的平房是醫院里的一個舊澡堂改造的,頂棚互通著,隔墻只隔了一多半,兩家說話的聲音和炒菜的氣味都通過半隔山墻互通有無。這個房子,最大的好處是屋里有水龍頭,不像別人一樣去公用水房打水。最大的壞處是,水龍頭經常壞,半個地板都是潮濕的,滴答漏水的聲音像極了這個夏天。湯阿姨愛干凈,在這樣的日子里,她就趴在地板上,用抹布一點一點擦地,一擦就是半天。
這天,她趴在地上擦地,由里往外,快擦到門口的時候,看見了三雙沾滿泥水的膠鞋,她往上看,看到藍色的褲腿,再往上抬頭,就看到了總務處吳副主任和兩個年輕公安的臉。掛滿雨水的臉上,有一些水珠落到她剛剛擦干凈的地板上,讓她心生惋惜。
吳主任在總務處分管安全和伙房,也是我們這群家屬院孩子的好朋友。可是他今天帶著警察到湯阿姨家,是怎么一個情況呢?我內心充滿了好奇,仰躺在床上聽墻頭傳來的聲音。
湯會計,這是公安局的民警同志,來向你了解個情況。
是這樣的,湯會計。南關當鋪巷的一座老房子近日受雨水浸泡塌掉了。墻洞里發現了一批古玩字畫,還有一份藏品清單。對照單子,字畫全都能對上號,像是藏品的一個目錄索引。唯獨少了一幅《八駿圖》,是故宮里流失出來的東西。據調查,你家曾在今年初在該院落租房居住,你們有沒有見過或聽說過這么一幅古畫,請配合我們調查。
我們是在那里住過幾個月,前段時間醫院里騰出了房子,我們就搬過來住了。在外面住,房租也是一筆開支。況且我上下班也不方便。噢,扯遠了。你們請坐,請坐。剛住進去的時候,我整理衛生,從煙道里掏出一個紙包,打開里面包著一顆手榴彈,不知哪年哪月的。這幸虧發現了,要不以后我們生活做飯,還不得爆炸了。還有就是,有一回我們正睡覺,聽到啪嗒有東西從頂棚上摔下來,點上燈一看,是一只手掌大的大蝎子,尾巴都赤紅赤紅的。對不起,又扯遠了。請喝水,喝水。在這個老宅子住著,我們天天擔驚受怕,就怕再有什么意外,這不單位上有了房子我們趕緊搬走了。至于什么古畫,從來沒有見過也沒聽說過。要我說,也說不定是哪朝哪代丟失的呢。
吳主任一行人走后,我聽見湯阿姨又在那用力擦地,擦去那些膠鞋底濕漉漉的雜亂無章的印記。
那個年代,大人們總是組織沒完沒了的學習。晚上我一個人在家,在一張木頭棋盤的方格子里,寫滿車馬炮、將士相,這是父母留下的作業。我的啟蒙教育是從中國象棋的棋子開始的。等晚上父母散會回來,我還要背誦一首毛主席的詩詞,完成這些作業,才能睡覺。這天晚上,我呆呆地望著柜子上的毛主席像,心里在背誦他的“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王哲的聲音從墻上傳過來,好像被外面的雨聲襯托得沙啞而沉悶。
一張發黃的畫,怎么能扯上故宮,還是皇上的藏品?
是啊,公安說是元朝趙子昂的《八駿圖》,你知道趙子昂是什么人物嗎?
不知道,我知道我放的電影里有個趙子岳,老演員了。
你見過或聽說過那幅畫嗎?
扯淡,咱老百姓能見到那樣的國寶,快睡覺吧。唉,這沒有電影的日子還真難熬,什么時候蓋一座室內的大電影院,下雨刮風都能放電影了。
搬到防震棚里,我家和湯阿姨還是鄰居。她家的棚子是油氈紙的,我家是石棉瓦的,一白一黑,用竹竿撐著,像兩個孿生的兄弟。大人們談論著邢臺地震了,海城地震了,我們不知道邢臺和海城在哪里,地震在我們孩子們的心目中像尼克松的老家美國一樣虛幻而遙遠。一邊防備著地震,一邊還要過正常的日子,我家包了韭菜餡的餃子,掀開篷布給她家送一碗去,她家蒸了蘿卜餡的包子,掀開篷布給我家送兩個。這下可好了,連隔墻也沒有了,我們這些孩子,學著電影《地道戰》里的樣子,從床底鉆過去,匍匐前行,會突然從另一家的床底鉆出來,把大人們嚇一跳。
與我家不同的是,湯阿姨家把三個抽屜的小柜子也搬進了防震棚里,寶貝一樣愛護著。有時晚上還在上面倒扣一只碗,碗上倒立一只酒瓶子,當做地震報警器。我媽對湯阿姨說,這柜子也搬來了啊,怪沉的。湯阿姨說,搬來方便,既當桌子又當柜子,放個東西啥的。兩個女人成了好朋友,晚上去醫院東南角的公共廁所都要結伴同行。雨不知什么時候終于下完了,天氣一天比一天熱起來,整個世界都包裹在水蒸氣的一片朦朧之中。每天早晨和中午,高聲喇叭里的最高指示,穿透迷霧準時傳送過來,仿佛是人們久久盼望的陽光一般。
不下雨了,王哲又開始放電影。不光在城里放,還經常去下面的公社和生產隊里放。每當看到王哲騎著公家的大金鹿車子從外面回來,我們就知道他又出去放電影了。我們追著問,王哲,又來什么新片子了?王哲一臉疲憊地說,還是老一套,南征北戰。我們哈哈地笑著,張軍長,拉兄弟一把,請你拉兄弟一把吧。王哲外出放電影的時候,吳主任就經常到防震棚來視察,囑咐些用電防火防盜的事項,滿臉和藹可親。
事實上吳主任和我們這幫孩子是一伙的,我們經常配合默契地在一起做游戲。我們在從伙房到防震棚的路上,挖一個坑,埋上老鼠夾子,引一根長長的細線,躲在梧桐樹的后面。見吳主任走到“地雷”面前,就拉弦,“砰”的一聲騰起一片塵土。我們從四面沖上去,高喊,不許動,不許動。吳主任就順從地舉起雙手,彎下他肥胖的脊梁,低頭認罪。
吳主任是少數不住防震棚的人,他說,我老吳命大,死不了。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他依然住在伙房東頭的單身宿舍里,我們在防震棚里都能聽到他如雷的鼾聲。吳主任家屬在農村老家,他說是武松打虎的那個陽谷縣。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將來退休了回老家在景陽崗上蓋三間房子,開一家酒店。住防震棚的那些夜晚,我們這群孩子經常把吳主任圍在梧桐樹下纏著他講故事,我們有的給他扇扇子,有的給他端茶水,在他的故事里消磨掉一個個夏日的夜晚。
他會講梁山好漢的故事、三國演義的故事、聊齋的鬼故事,還會講皇宮的秘史。在我們眼里,他就是一本天書,他肥胖的肚子里藏著太多的秘密。故事告一段落,他就在晚上七點半準時打開他的收音機,和我們一起聽《小喇叭》《星星火炬》,聽岳飛傳播楊家將,有時我們覺得他本身就是一臺大型的收音機,只要給他灌足了茶水,吸足了煙卷,那些故事就從他的喉嚨里汩汩地流淌出來。他也講自己的故事。他是一個轉業軍人,轉業以前在部隊當過炊事班長,做過飯喂過豬,當兵以前在老家縣城的一家書畫店里當過學徒,會裝裱,還會吹笛子。這些我們都信。前幾天防震棚一對新人結婚,婚禮設在那個廢棄的公交車廂里,車廂上的紅十字被紅喜字蓋住了。我們這些孩子歡天喜地地搶喜糖,聽到了婚禮上傳來了委婉悠揚的笛子聲,我們想象不出這些美妙的聲音是從一個粗壯的胖子的嘴里,從一個滿口黃牙晚上鼾聲如雷的嘴里發出來的,吳主任的演奏把我們驚呆了。一管細長的竹笛,在他肥胖的手里像被施了魔法一樣,變得軟弱無力,任他拿捏,他說這支曲子叫《山村迎新人》。我們還親眼見他把一張普通的毛主席畫像,裝裱得富麗堂皇,掛在醫院大會議室的墻上,像是重新被描畫過一般,端莊大氣,氣宇軒昂,這是我們見過的最好看的一幅主席像。
那個夏天吳主任為伙房里買來了一只羊,說是給干部職工改善伙食。羊并不著急吃,他先讓我們這群孩子們玩幾天。放羊,成了我們光榮而艱巨的任務,我們每天牽著它去醫院北面的水塘里喝水,去醫院南邊的田野里吃草,每人輪流著牽一會兒,一副小心謹慎的樣子。有一次我試圖騎上羊背,被吳主任大聲地制止了。沒事的時候,吳主任穿著他洗得發白的軍裝,和我們這群野小子一起,簇擁著那只羊,游走在醫院四周的郊野里,采野花、拔野草,過著田園詩一般的生活。他穿軍裝的身影在我們的隊伍里顯得異常高大。那些日子,我們和羊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和吳主任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晚上,我們就把羊拴在防震棚里,和它同吃同住。那個時候,吳主任到防震棚里來得越發勤了,他經常從伙房帶了幾塊炸魚或是一個豬蹄子,用舊報紙包了,來找王哲喝酒說話。有時王哲外出放電影,他就和湯阿姨說話,有一回我看到他們在一起看書,吳主任的一只胖手在書上指指點點,另一只手就很自然地搭在了湯阿姨的左肩上。
后來殺羊的時候,我和小伙伴們都哭了。吳主任說,哭啥,買來就是為了吃肉的嘛。他把鋒利的尖刀一下子捅進羊脖子里,被吊在半空的羊奮力地蹬動四肢,發出絕望的慘叫。那聲慘叫在這個全民防震的夏天,顯得格外凄厲。鮮紅的羊血頃刻注滿了雪白的搪瓷盆子,泛著新鮮的熱氣和泡沫。到食堂打飯的時候,吳主任給我們每人多舀了一勺子羊血,我的胃里立刻翻起了熱騰騰的泡沫子。
防震棚里蚊子多,有時我就鬧著回平房里睡。母親把那個小柜子上面的三個抽屜拿下來,留了三個空洞的嘴巴通風透氣,再打開下面的兩扇門,把里面放上小褥子和枕頭,我在家里又有了一個屬于自己的木頭防震棚。我很喜歡在里面睡覺,透過三個嘴巴,我可以看到高處紙糊的天花板,看到玻璃窗外面掛在高高的梧桐樹上的星星和月亮。也許是水龍頭又漏水了,我的睡夢里總是有一只馬蹄表在滴滴答答不停地走動。
睡在木頭防震棚里的一個晚上,我第一次出現了幻覺。一覺醒來,聽到隔壁湯阿姨家屋里有悉悉窣窣的響動,類似于貓狗爬行一般的響動,先是在低矮處,在柜子底下、床底下,在地板的夾縫里行走,后是慢慢爬高。我看見一束手電的光柱直射到天花板上,然后一個人影順著光柱的白亮慢慢爬上去,用手電往四下里照,手電的光亮把我家的頂棚都照得雪白一片,那些舊報紙上的字跡都像是受了光亮的驚嚇,簌簌脫落下來,粉塵一般落在我家柜子的臺面上,甚至落在我的眼睛里,讓我睜不開眼。從我這個角度看去,那是一個只有下半身的人,攀爬在竹梯子上,把上半身探入到頂棚里,用手電尋找著什么。許久過后,屋里一片黑暗,一片寂靜,只有外面寬大的梧桐樹葉子嘩嘩作響,連鄰居家院子的狗都不做一聲。我懷疑自己是做了一個夢,后來我對誰也沒有說過。
再后來的一天,湯阿姨突然就失蹤了。王哲向分管保衛的吳主任報告:湯會計是被人綁架了。王哲手里拿著一張字跡歪斜的條子,上面寫著:拿古畫來換人。吳主任和王哲坐著醫院里唯一的一輛老式救護車趕到公安局去報案。我們這群孩子以為醫院里出了天大的事,就站在醫院門口,望著大街,等待他們回來。湯阿姨家的防震棚前站滿了人,人們說,昨晚還看見湯會計下班做飯呢,怎么王哲下鄉放電影回來就不見人了。這奇怪的天氣怕是注定要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吧。
在警察辦案的日子里,王哲和吳主任經常在防震棚里喝酒,高一聲低一聲地長吁短嘆。吳主任問,老王,你們家真有那么一張傳說中的古畫嗎?怎么連綁匪都找上門來了,這可是人命關天的事啊。你可得跟我說實話。王哲喝一口酒,用手拍打著柜子,說,你看我們家像是趁一張古畫的人家嗎?我們不配啊。我倒是想有,可是拿我的命也換不來一幅古畫啊。這都是前幾天警察來了解南關當鋪巷的案子惹出來的麻煩。你說這個藏主,你的東西里明明沒有《八駿圖》,干嗎要寫到清單上啊,這不是給后人找麻煩呀,也許在清朝也許在民國就失去了呢。天地之大,你讓我上哪兒找那張畫,你讓我上哪兒去找我的小湯。兩人都不再言語,繼續埋頭喝酒。
事情遠沒有王哲想象得那么復雜。第三天案子破了,湯阿姨被接回來了。她的頭發略顯零亂,身上鞋子上還沾滿了泥水。進門先是哭,哭完了就去公共澡堂子洗澡,洗完澡回來就像沒事人一樣,開始整理家務了。她對科長說,這兩天,可不能算我曠工啊,要給我記考勤發工資。
湯阿姨是被兩個本院的高中紅衛兵學生綁到了醫院的防空洞里。那兩個大孩子,一個叫海濱,一個叫春光,平時都喊湯會計阿姨,一個家屬院里的熟人。那個防空洞,是醫院“備戰備荒”時留下的遺物。我們這群孩子以前經常在里面玩,過家家捉迷藏,那里曾經是我們這群猴子的花果山水簾洞。大人找不到孩子時,在洞門口喊一聲,回家吃飯了。不多會兒,就有灰頭土臉的毛猴子從里面走出來,像電影里國民黨的俘虜兵走出戰壕,被大人們一個個擰著耳朵帶回家去。后來,我們在防空洞里發現了老鼠和蛇,就逐漸沒人敢來了,再后來我們更關心的是雨季和地震,漸漸人們都把它遺忘了。沒想到海濱和春光還記得這個隱蔽的洞口,把這里當成了他們的臨時山寨。
警察問他們,你們怎么知道湯會計家有古畫?海濱說,是聽你們說的啊,你們說南關街丟了古畫,湯阿姨家曾在那里住過,有嫌疑。警察說,難道這事情的源頭在我們了?你們要古畫去做什么?春光說,古畫是國寶,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我們要得了國寶獻給毛主席,我們要去北京。警察說,看把你們能的,北京故宮博物院來過兩次人,都覺得沒法查找。你們就能找到?
我們幾個孩子出于好奇,又去了一趟防空洞。門口已雜草叢生,進了門往里走,腳步不斷向下,像進入一個礦坑。這里我們是輕車熟路的,拐過一個轉角,洞里愈發黑暗潮濕,卻是格外涼快。在一塊不大的平臺上,青磚鋪的地面都有水從磚縫里滲透出來,地上鋪著一個麥草的門簾子,旁邊是兩個罐頭瓶子,一個盛著水,一個盛著剩飯。看來,這就是海濱和春光精心設置的臨時牢房了。那次去,我們看到了黑暗中亂竄的老鼠,沒有看到蛇。有人說,把這個防空洞改造成一個大防震棚,能住不少人呢。我說,你個嘲巴,在這兒住碰上地震,一個都跑不出去。
海濱和春光被判了勞教。后來在勞教所里他們聽到一個巨大的噩耗: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了。他們兩人抱頭痛哭,他們覺得自己這一生再也沒有機會進京獻寶了。海濱和春光的入獄,使這個縣城里關于古畫的傳說越來越撲朔迷離。甚至有人說,那幅畫原來確實是有的,不過在國民黨撤退的時候,被偽縣長帶到臺灣去了。眾談紛紜,也沒有證據。何況大事件在一九七六年的夏秋接踵而至,很快就轉移了人們對古畫的興趣。
綁架事件之后,我又一次隔墻聽到了湯阿姨家的談話。
老王,我看這個地方咱們不能待了。
咋不能待了?
你想想,一個大院的鄰居因為我被判了勞教,這抬頭不見低頭見的,怎么相處?還有這幅幽靈一樣的古畫,怎么就纏上我了。以后還說不準有什么事情發生。
那你想咋辦?
調走吧,回我的老家青島。
接下來的日子,湯阿姨開始為她的調動工作而奔忙,不管是下雨天還是悶熱天,總是人事局衛生局地到處跑。大院里的人都知道她是鐵了心要離開這個縣城了。湯阿姨跑調動的日子里,吳主任往湯阿姨家跑得也更勤了。
有一次玩捉迷藏的游戲,我沿著防震棚篷布的裂隙,爬到了湯阿姨家,鉆進了她的小柜子里。上面的三個抽屜堵著,前面的兩扇門關著,真是一個藏人的好地方啊。我在狹小的空間里,觀察她家的柜子跟我家的有什么兩樣,她那么不辭辛苦地搬到防震棚里來。我敲打著木板,發現她家的柜子發出“咚咚”的回音,像是有一個夾層,我家的柜子是“啪啪”的聲音,像是一塊實木。我把這個秘密藏在心里,一直藏到現在。我的心里能藏得下秘密,柜子里能藏得下人,也能藏得下別的東西。我想。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我去城里小學報名,準備過了夏天就上學,我為什么對這個日子記得這么清楚,因為我記得我是唐山地震前一天去報名的,史料記載唐山地震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那個上午,我和幾個伙伴沿著醫院后面從東山流淌下來的溪水,向西走,進東關,奔城里。一路經過了好幾個因夏天的雨水而豐盈起來的大水灣,我們停下來,脫了涼鞋,到水灣里游玩。到學校的時候快中午了,這是一個解放前大地主的宅子,院子里種著高大的芙蓉樹,教室里有四五根兩個人合抱的大柱子,頂天立地支撐著屋梁。在這樣的老宅里,會不會也藏著古畫和珍寶呢?我傻傻地想。后來的事實證明我錯了,在這里上學五年,我從墻縫墻基里掏出來過不少的銅錢和土鱉,卻從未發現奇珍異寶。
這天下午,我一個人坐在伙房前的院子里,發現了許多奇異的景象。我先是看到屋檐下的燕巢,一公一母兩只老燕,用嘴叼著小燕飛到半空里甩嘴拋去,能飛的小燕就歪斜著試飛,不會飛的就跌落到泥土上,痛苦地叫喚,老燕忙碌著,直到燕巢里一只也不剩。它們是在搬家嗎?為什么如此著急匆忙呢?稍晚些時候,我看到空曠的院子里熱鬧起來。成群結隊的麻雀、蝙蝠和蝴蝶從梧桐樹碩大的樹冠里飛舞出來,貼著地面盤旋,一副無家可歸的樣子。墻根下柴草堆的暗洞里,一隊老鼠有序地出行,一個咬著一個的尾巴,排著整齊的隊伍,黃鼠狼公的叼著小的,母的就馱著幼的,成群結隊,落荒而逃,一只臃腫的花蛇也在扭動著身體,奮力前行。它們的目標方向一致,向南,向南邊高闊的田野逃去。我被這景象驚呆了,想要呼喊伙伴呼喊老吳主任,整個大院里卻空無一人,只有動物們在忙碌著。
天色暗下來的時候,我甚至看見了墻角里一根生了銹的廢舊鋼筋,發出暗紅的光澤,像被烈火燒灼著一般。我開始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眼前的一切。我回到屋里,看到父親的魚缸里,一尾金魚頭朝下尾朝上直立在水面上,鼓著兩只憤怒的眼睛,它的尾巴蓬松著像螺旋槳一樣,整個身體在水上打著旋,然后奮力一躍,跌落到地板上。我把魚撿起來,放回去,它再一次掙扎著跳出來。魚缸里的水居然像開水一樣冒出了氣泡,魚兒發出了嬰兒一般尖銳的叫聲。
我想把這一切告訴大人,可是我一個人也見不到,他們又在搞政治學習。天黑了,我餓著肚子躺在防震棚的床上,滿腦子在胡思亂想。這時候,一個肥胖的人影進了隔壁湯阿姨家,直奔柜子而來,他的動作熟練而準確,用鉗子和螺絲刀打開后面的木板,取出一個錦旗一樣的卷軸,鋪開在柜子臺面上,用一支手電照了照,看了看。手中突然間多了一把小巧的手術刀,小刀在紙面上游動,像宰豬剖羊一樣靈巧,像殺魚去鱗一樣生動,迅速地完成了一場手術,迅速地將一切復原。我看到仿佛有八匹揚鬃炸尾的駿馬,掙脫了韁繩,從這個魔術盒一樣的小柜子里奔跑出來,首尾相連,腳踏祥云,一直奔跑到極高極遠處的天河岸邊,在那里自由地徜徉,昂首嘶鳴。這個下午和晚上我真是活見鬼了,我是不是又一次出現了幻覺。那人影剛要走出去的時候,倒立在桌上的空酒瓶子砰然倒地,發出一聲脆響。像是一狗引得百犬吠,幾乎同時,所有防震棚里的酒瓶子都落地了,有人敲鑼,有人喊,地震了,地震了。棚子里的家屬紛紛跑出來,醫院會議室里穿白大褂的人影也蜂擁而出,那個廢舊公交車里也鉆出了人,驚慌失措地向院子里聚集。院子梧桐樹下,站立著吳主任高大的身影,他招呼大家,不要慌,不要亂,要沉著,要冷靜。
后來,人們知道是遙遠的唐山發生了大地震。據說北京天安門城樓上那些渾圓結實的大柱子,都被震得“嘎吱”作響。
湯阿姨終于辦成了她的調動手續,要搬回青島老家了。搬家時,借了一輛解放牌汽車,所有的家當一車廂還裝不滿,王哲招呼著人們抬柜子:小心點,別碰了漆,別碰了漆。我媽和湯阿姨手拉著手說話,兩個好鄰居依依不舍。我們也舍不得王哲走,他走了,我們就沒有免費的電影看了。吳主任也來幫忙,也來送行,他和王哲這一對酒友,也是難分難舍的樣子,拍著肩膀說,常寫信,多聯系啊。想不到的是,海濱和春光的父母也來送行,畢竟是鄰里一場,握著手卻不知要說什么,只是互道珍重。揮手作別,解放車拉著湯阿姨一家駛出了醫院大門,那個柜子在車廂里仿佛要拒絕捆綁一樣,還在努力掙扎著。
湯阿姨走后,吳主任有些顯得悶悶不樂。他經常和我們提起,等退了休,他要回景陽崗老家蓋三間大屋,開一家酒店,過綠林好漢的日子。他還是照樣在夜晚,在院子里梧桐樹下,給我們講三打白骨精,講三打祝家莊,他還是孩子們心目中的神。那些日子,用火車運來了很多來自唐山的傷病員,醫院一下子忙碌起來。吳主任雖然是后勤人員,也有忙不完的工作,一度在大院里我們都很少能見到他了。
直到防震的口號喊得不是那么緊了,防震棚也漸漸空了出來,有些敗落的樣子了。這天吳主任陪院領導招待客人,喝多了酒,回到單身宿舍倒頭便睡。半夜里蚊香燒著了蚊帳他不知道,蚊帳燒著了紙糊的頂棚他還不知道,直到濃煙把他嗆得昏死過去,他更是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到搶救出來,人還昏迷著,屋頂已經燒落了架,他為數不多的全部家當灰飛煙滅了。人們用涼水把吳主任澆醒,他看了看眼前的慘相,肥胖的肚腹里發出老狼一般蒼涼的慘叫,號叫著就要起身往冒煙的灰燼里撲去,仿佛要去搶救一件比性命還金貴的物件,被眾人死死地摁住了。后來,全院的同志們為吳主任捐了款捐了物,他又重新建立了新家,很有一副災后重建的樣子。他還在大門上自編了一副對聯:烈火煉真金,患難見友情。只是,他的舊軍裝燒沒了,我們再也沒有見到他英姿颯爽的樣子。
夏天一過,我就正式上學了。我的學齡前時期宣告結束,我的無憂無慮的日子也宣告結束。上了學,日子便過得飛快,一年又一年馬不停蹄地往前奔,仿佛有無形的鞭子在身后抽打著。
多年以后某電視臺的一檔鑒寶欄目到山東青島錄制節目。一個青島小哥拿出祖傳的一幅畫,請專家鑒定。專家組沉吟良久,說道:這是元代趙子昂的《八駿圖》,可惜只剩下裝裱時托畫紙的那一軸,但從托紙上依然能夠看出八匹駿馬的大體輪廓,依然有天馬行空的意境躍然紙上,另外乾隆御覽的印章也可以看得清楚。只是這是一幅被人剝了皮的古畫,也就是說整個裝裱畫最表面的一層真跡已被人揭去了。
節目播出后,這個縣城里又引發了一場關于《八駿圖》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