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叔河《賣書人和讀書人》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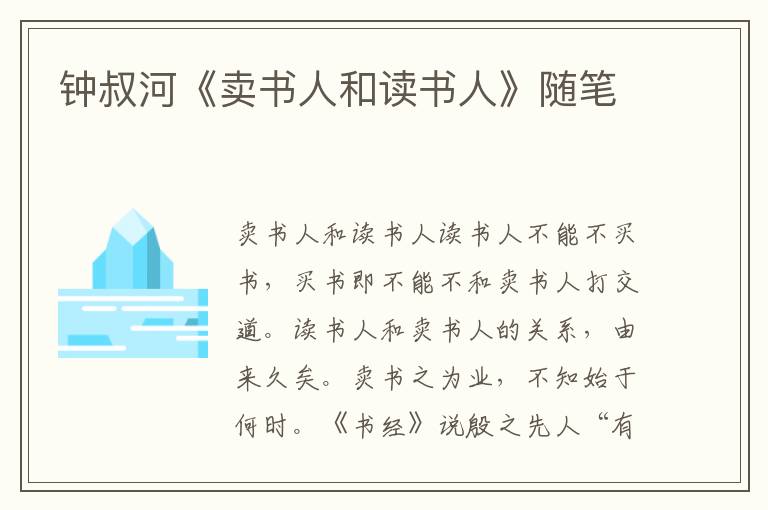
賣書人和讀書人
讀書人不能不買書,買書即不能不和賣書人打交道。讀書人和賣書人的關系,由來久矣。
賣書之為業,不知始于何時。《書經》說殷之先人“有典有冊”,那是放在機要室里的東西,普通人無從得讀,更無從得而賣之。直至天下合久必分,王綱解紐,春秋戰國時有了不吃王糧的讀書人,才有了屬于個人的書。不過當時寫在竹木片上用孔夫子翻斷過的那種皮條穿成的書,大概還沒有成為商品進入市場。惠施“其書五車”,蘇秦“陳篋數十”,書的字數當以萬計,恐怕也是本人最多加上幾個門徒“書之竹帛”而成的吧。
及揣摩既成,讀書人做了官,位尊而多金了,如果還要讀書,才有可能命人或雇人來傳寫,雇來的便是所謂“傭書”。“傭書”能出賣的只有自己的勞力,比起后世《清明上河圖》中書坊里的賣書人,收入恐怕相差甚遠,亦猶我這個領月薪的編輯匠之于黃泥街書老板焉。
最早的書市見于《三輔黃圖》,王莽謙恭下士時,長安太學規模頗大,附近有個“槐市”,“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傳書籍,笙磬樂器,相與買賣”,情形簡直同美國大學校園里的streetfair差不多。可見學生下海,古已有之,這也是王莽為了坐上金鑾殿而著意營造的“文化繁榮”之一小小側影。
還是紙的逐步改進和利用,才促成了書的普及和專業賣書人的出現。《后漢書》記載,王充“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家貧無錢買書,偏能過目不忘,來到洛陽書市,專門只看不買,王充這位讀書人也夠精的了。洛陽賣書人的服務態度也真好,允許王充盡量揩油,如果沒有他們行方便,《論衡》也許就寫不成這樣好。可惜范蔚宗沒有記下一兩位賣書人的姓名,不然奉之為書店業祖師,豈不比鐵匠行崇奉太上老君合適得多嗎?
唐時開始雕版印書,至宋而刻印大行,書業更盛。宋本《朱慶馀詩集》末頁末行文云:“臨安府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印。”這位陳姓賣書人,已是編輯、印刷、發行三合一,開近代“商務”“中華”之先河了。下至明清,仍然如此。《儒林外史》第十三回,寫蘧公孫到文海樓書坊,拜訪書坊請來編書的馬二先生。馬二先生食宿均由坊中招待,兩個月編選成一部書,得了一百兩銀子,付了采紅的身價,平息了一場官司,還剩有銀子去游西湖,稿酬似比今為豐。又看第十八回,文瀚樓主人同匡超人談話,不僅于編印發行十分內行,對讀者和作(編)者也是熟悉而有辦法的。
我想,賣書人以書為生計,自不能不以讀書人為衣食父母(今稱上帝,則比父母更尊矣);而讀書人若真以書為性命,亦當視賣書人如救苦救難觀世音。聯結二者的紐帶就是書,只要彼此都喜歡書,看重書,熟悉書,自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共存共榮,融洽無間。只怕身在書界,而心不在焉,對于書和讀書人一概漠然,即使沒穿“煩著哪,別理我”的文化衫,臉上卻明擺著那樣一副神氣,則雖焚香頂禮,亦不得靈驗矣。
(一九九五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