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偉芳《更聞秋聲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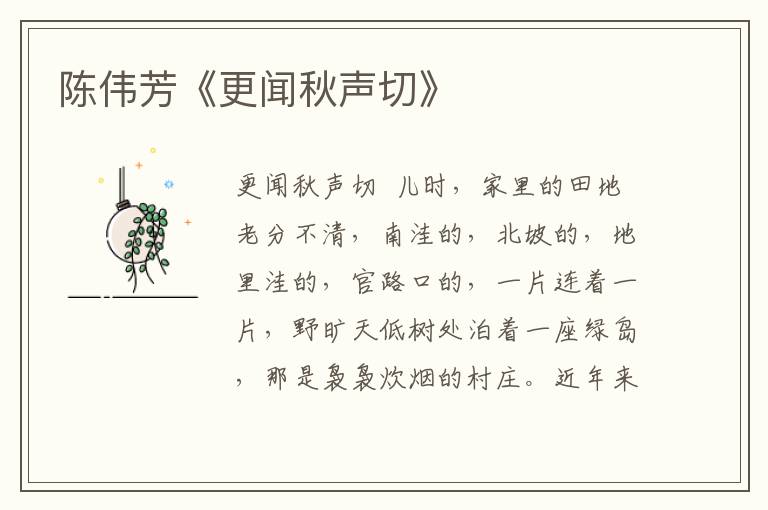
兒時,家里的田地老分不清,南洼的,北坡的,地里洼的,官路口的,一片連著一片,野曠天低樹處泊著一座綠島,那是裊裊炊煙的村莊。近年來,土地的面積銳減,全家的土地僅剩一畝多了,名曰:自留地。君臨的華庭一路之隔,正等著自留地騰地方。土地彌足珍貴起來,卻又在誰的手中流失?只要有地,世道無論怎么變,人就有吃的,這是祖祖輩輩信奉的道理。農民用自己視如命根的土地作了廉價的交易嗎?還是時勢的使然?時代不同了,土地不再是農民經濟支柱的唯一,五谷雜糧,已然退出引領家家戶戶全年生計的光輝歲月。
夜深了,秋蟲好像叫的無邊無際,但心里明白,蟲鳴漫浸的田野,格局越來越局促了。想想土地,想想種地的父親,油然而生人與地俱老的感喟了。
前些日子,莊稼還站在地里一副等待成熟的樣子。隔著連綿的秋雨,幾場焦灼的期盼過后,得老天爺體恤,乍現了幾個明晃晃的日頭,玉米粒已攻到頭,暗綠的皮還需在陽光里褪成黃白。等到頂著褐色的干胡須,裂開嘴,暴露著金黃板牙,玉米就熟的有模有樣了。
遠遠地,父親尖利、渾濁、甚至歇斯底里的咳嗽從地的那頭傳到地的這頭,有一種隔山打物般的疼,歲月相催的無助,一半給了父親,一半是我的。和土地摽了一輩子的勁,農忙時,這點少的可憐的地,一向以主心骨自居的父親生了些怯意。零碎的地塊,機械也愛莫能助。他真的老了,遲緩地侍弄著畝把地,直至收割完最后一株莊稼。
土地貫穿了生命始終,細批著流年,往事自一個秋天而來,又歸另一個秋天而去。
年輕的父親那樣強壯,總有使不完的勁,支楞著胡茬,發根,精神抖擻的像一個王,逡巡于地頭,香煙夾在熏黃的指間;煙頭一甩,大手一揮,雷一聲“掰”,我們得了軍令,沖進掛滿露水的青紗帳;蟲子在腳下四散奔逃,玉米葉子劃拉在臉上,胳膊上,一經汗水腌漬,火辣辣地疼往心里滲透。
田地里堆起累累的玉米,滿滿地排進父親的排車,伴著長一聲,短一聲的號子,一溜蛇皮袋子高高垛上。父親頭上,肩上,胳膊上的汗珠一粒粒膨脹鼓動,閃閃發光,像一顆顆透明的玉米粒,在不斷的揮灑中突然破裂,競相順著油亮的皮膚滾滾而下,汗濕的衣衫如同水洗。骨節凸出的大手掌住把,架好轅,大踏步形成自然的節律,狂走如一匹奔馬。我和母親一輛車,始終攆在后面,雙腳蹬地如鼓點,心里似開著一臺砰砰不息的發動機,跑的心快跳出來了;氣喘吁吁地坐上母親的空車,一路上,迎面跑著別家拉偏綆的孩子。
一趟趟,來來去去,家門口漸漸隆起小山一樣的大玉米堆,小孩會發愁地尋思,月亮地里還留著剝玉米活呢。早當家的農家子弟,從輪番磨礪的農活里破繭而出。
田野上遺留了一些干枯的玉米秸,持抱著空空的田野。土地深翻的面缸似的,莊稼的秸稈隨即粉碎在田,溝邊地角,野草匍伏,像田地潦草的花邊。鄉下的燕子沒打招呼就南飛了,趕路的腳步太遲,收秋的過程匆促的像一陣風,省略了許多人力的糾纏。機械刪除緩慢的細節,留下一個曲終人散的大戲臺。
不勝唏噓!無處安放的目光不禁翻起記憶的冊頁,回放著秋野上有過的童年。
拾掇地時,秋野給了孩子們一個明朗而歡喜的樂園。銜一莖青草,仰面朝天躺在莊稼的秸稈上,白云悠悠,搶拍下來雁群愈來愈遠的“人”字,“一”字;翻著,踩著一排排秸稈,轟出紛飛的昆蟲,貓撲上去,串一草繩的大螞蚱,逮幾只蟈蟈做過冬的寵物;最喜發現一座很深的鼠洞,端了它的老窩,竟然有不少的斬獲,一只走投無路的小白鼠,慌亂的眼神,莫名地憂傷了孩子的心,任其吱吱地抱頭鼠竄。
秸稈歡快地燃起噼噼啪啪的脆響,草木的清香里飄著烤玉米,紅薯,爆料豆的香味。眾人拾柴火焰高,竄來竄去的火舌映紅孩子們饞涎欲滴的臉。一聲熟了,便迫不及待的伸出老鴰似的黑爪子,吹噓著掌心,帶著煙灰捂進黑嘟嘟的小嘴。可是,誰太心急了,啃著的地瓜定會皮焦骨頭生,那就在草木灰里多焐一會兒吧;互相抹著,取笑著花狗臉,嬉鬧聲穿花繞樹,飄散的煙嵐挽起地野,西天里的晚霞蒙了紗,映在古久而遼遠的畫卷里了。
誰家的小兒女耳際簪著幾朵小野菊,一顫一悠地走在大人悠長的呼喚里。小路彎彎,秋蟲依舊叫得酣暢,星兒聽的閃閃亮。像羊兒切慕溪水一樣,想往那堆篝火里再添些枝葉,想伏在秋天的某個角落里笑一笑,哭一哭,那樣的日子都藏在哪兒了?假如躲在了時光的背后,在心里總是不難找到的,如果藏到某種物質的殼里去,任誰也找不到的。
這些接通地氣的引子,打開了大自然豐富的靈性敘事,使田野里的勞作化作農家孩子回味的甜。帶孩子回家掰玉米,暗自以為孩子能拽住莊稼地的尾巴,像我一樣地長出莊稼人的根須,得以歇腳在人生的某個秋天,有著土地養育的生命質地。搞得有點形式主義,其實,很多東西像土地的流失一樣,也是孩子們生命中必然的缺失。而今,孩子再也感受不到收秋撫摸我的樣子。慢慢遠離鄉村的孩子,不再面對與自己沒關系的秋收發出內心的贊美。從小跟莊稼打交道的人,十分親切地經過路邊晾曬的糧食,努力嗅向那塊氣息的島嶼,糧食照眼明的光影,只有梵高的刷子能涂抹出來,相看兩不厭。
一個走在秋日下的人,揮霍了太多傷逝時光。那個以一雙冷眼,寄身現實,運行于慣常軌道的自己,隔著幾十個秋,竟有一種不識之虛空。走到秋冬的臨界,萬木蕭瑟,百草枯黃,脫殼在時間之外,寒露一語道破:從頭再來,上蒼從不吝惜他的浪費。
造化有序的針腳里,一些種子養活人類,一些養活鳥獸,一些繼續埋在土地里活出神的愛。遺落的莊稼倍感孤獨,靜靜地臥在草稞里懷念被揀選的一幕:一個深深彎下的身影,一雙低到泥土上的手,一個溫暖的,拾麥撿豆的口袋,幽微的細節曾讓它們揣起對谷倉的朝圣。離收獲僅一步之遙,鑄成永恒的寂寞,一群群鳥雀翔落田野,仔細地找到它們,啄食的搖頭鼓翼。
一粒被秋天放大的種子,與犁鏵下的土地深入的交流:悅納了悲苦的過程,才能欣然交出成熟的生命。土地為它蓋上溫暖的被子,種子一意低下去,低到蒿草里,躺進泥土的被子下面,一切渺小被沉睡包圍,永恒的沉睡,所有的物質構成夢幻的本質。
村莊后面,一條彎彎的小路通向一片群鴉云集的林子,那是先祖們安息的墳地,塵世的喧囂都已謝幕,只有暮鴉分享著這一世界的寧靜。
秋氣迫人,黃陰陰的天,仿佛到了某段旅程的小站。落葉從不向秋風打聽那個翩然欲舞的理由,隨風滑翔,聚散,追逐,做著新的游戲,沉默無語的大地在接所有的孤子回家。
土地的兒女大多總有一次背離她的過程,沒有誰能把自己從土地上連根拔起,一枝一葉濺落地上,根須上會有抖不落的泥巴,異地他鄉的遠游之后,反而把自己更深的植入泥土,化作地里的肥泥巴,滋養著一茬又一茬的黍麥稷粱,還有一地生之歡愉與貪戀,開的像春花兒一樣。
從戰場上歸來的祖父,沒有任何野心,本分地做著該做的事,安居樂業的日子多么美好,遠離血與火的生活又多么平淡有味,像一頭老牛反芻著日月;那本摩挲的起了毛的戰地日記,翻來覆去地打開合上,一方清白的手帕珍惜的包好往生的英靈;酒酣耳熱之際,往往要唱幾曲高亢激揚的軍歌,蒼老沙啞的嗓音里軍魂繚繞,老槐樹上的老鴰聽呆了。祖父探親時英姿勃發,一揚手擊落一只哇哇叫的老鴰,那鏡頭無疑深深地影響了他的兒子們。三叔做了民兵連長,父親一心模仿他老子摸槍的神氣,圓報效祖國的英雄夢。《青春之歌》《烈火金剛》《林海雪原》塑造著奇特的信仰與浪漫,而他人生的最高峰,僅僅站在縣里的小禮堂,上衣兜別著支鋼筆,留著三七開分頭,一臉政治熱情的團支書,那是父親最年輕的一張老照片,風華正茂依稀在時光揉皺的臉上。
無論夢想走的多遠,飛的多高,冥冥中擋不住土地的召喚,這片土地安身立命——曾經是那樣不屑于接納和理解的平凡收場。
也許,祖父在生命的揚棄中找到了與大地同步的光與靜默,背著糞箕子去拾糞,城里的老茶館里去消閑。赤膊在田間的父親,古板的很,出門時一定套上白汗衫,為所有生命不能承受之輕打底。無論走到哪里,分的清黑白,挺得起胸,本著自然的本性一身坦蕩,朗然笑出對命運的平和自在。
一位拄杖的老翁,一個偷棗的孩童,一群歡實的雞鴨,令政治失意的辛棄疾愿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唱出山前溪畔的一畝三分地之歌。“雁引愁心去,留酔與田翁” ,一種古老的遺風,把田間的辛勞者點化成一個田園風光的欣賞者。
駐留下匆促的腳步,卸下盔甲,面具,暫且不做萬物之靈的人類。住進一棵狗尾巴草里,隨風搖曳,沒有一點女孩變成老婦的面目可憎。披起陽光的袈裟,融入地野,在生命的中心地帶,仰視著那個遠遠高于自身的生命坐標,曲人悟道般明了大地無限豐富,又簡潔至極的寓理:看透了這個世界,卻依然愛它!傾聽土地與莊稼的晤談:化身腐朽的神奇,在于另一場孕育的開始。
秋日正刪盡春夏的繁枝縟葉,阡陌明胸,落筆于田野,眼前,田野攜帶無數的子民正破土而出,一塵不染的麥苗盡顯清發之姿,神奇地抒寫出展望的,氣血盈盈地詩行;探索,叛逆,不服輸,嫩生生地向空中勁發。
那些曾經與溫暖的谷倉無緣的億萬兄弟,是否走出了寂寞,藏身于這燦爛升華的蘇醒隊列?
種子的野心越來越大,看到的,便分享了;它的心變得挑剔,只有放上與愛有關的字眼,靈魂才長出了飛翔的羽毛。土地上盡藏著太多看得見,看不見的幸福。一個持抱半壁人生的人,就以她所熱愛的文字,行過青荇之上的聲息,來締結秋之盟約:撲一撲風塵,疊起秋日的征衣,堆一個雪人般的自己,如同塑一座紀念碑。
通透,蕭然的秋天盡收眼底,筆管撲向不著邊際的浮想,遠遠地,幾個墨點般的鳥影落于青蒼際線,一幅臨近收筆的秋之畫卷,將興亡,桑麻稼穡和流離勞苦隱在無盡的留白······
無物之陣,一望天地遠,一望萬古清,遠望可以當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