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與家風(fēng)》王金平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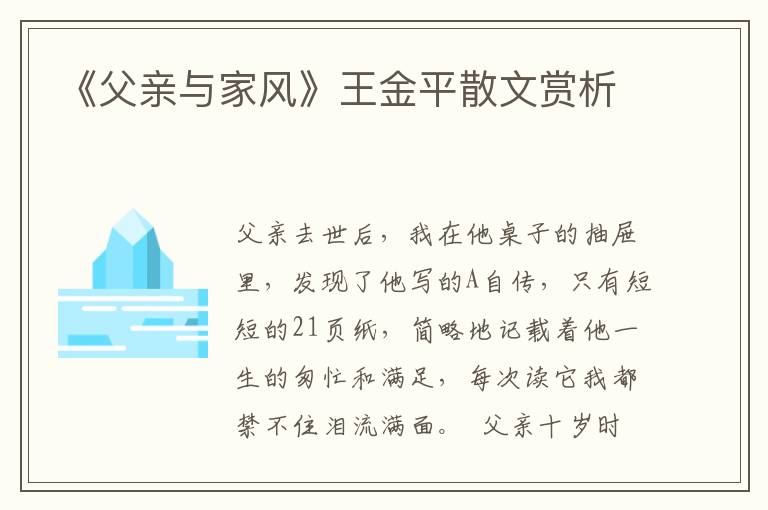
父親去世后,我在他桌子的抽屜里,發(fā)現(xiàn)了他寫的A自傳,只有短短的21頁紙,簡略地記載著他一生的匆忙和滿足,每次讀它我都禁不住淚流滿面。
父親十歲時,連年鬧災(zāi)荒,由于家里人多(他弟兄五人,一個姐姐),糧食很快吃光了。開始,帶糠的棗核還能買得到。吃了棗核渣,屙不下來,就用錐子捥。吃花生秧。村里村外的榆樹皮也被剝得精光。沒東西吃,餓得皮包骨頭,頭都抬不起來。爺爺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們擔(dān)心呆在家里會餓死,無奈,就遞給父親一條布袋讓他去要飯。
走到村東的小河邊,父親實(shí)在邁不動腳步了,便蹲在墻角下曬太陽。父親伸不出那只向他人乞討的手,更舍不得那張自尊的臉。他擺弄著布袋,發(fā)現(xiàn)布袋上有個窟窿,就有了不去的借口和理由。他折回村里。
一進(jìn)村,碰見一位大輩分的婦女,正舉著一塊糠面餅一邊吃一邊從巷子里朝外走。她見父親餓得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便掰下一三角給他吃。父親咀嚼得如美味佳肴。當(dāng)時,父親就想,長大了,一定忘不了鄉(xiāng)親們。
父親給村里辦的第一件善事,是最先給每家每戶安上了電燈。
記得那年我八歲,下學(xué)回來,見幾個腳穿膠鞋、頭戴安全帽的陌生人,在村南的地里,推著一盤一人高、纏著麻繩粗的電線線盤,我和幾個小伙伴好奇地遠(yuǎn)遠(yuǎn)站在一邊看。聽人說,村里要安電燈了。
那天,在我家院門口,碰見一個頭戴安全帽的年輕人,他笑著問我:“你爹叫啥?”
我回答,叫王懷亮。
他說:“知道不,就是你爹找我們局長的,這兒是山里最先拉上電燈的村。”
半月后,送電了。家里突然明亮起來,比煤油燈不知要明亮多少倍呢!我的心也隨之明亮了!
父親又幫村里安上了自來水。
村里原有兩口水井,村東一口供村東的人吃水,河邊一口供村西的人吃水。以前,村民們都是提著井繩擔(dān)著擔(dān)杖朝家里擔(dān)水。下雨下雪多有不便,特別是河邊那口井,臺階高。我十二歲開始一天擔(dān)兩擔(dān)水,它讓我吃盡了苦頭。而現(xiàn)在,只要在自家院里擰開水龍頭,清泉就會嘩嘩流出。
再后來,父親跑來點(diǎn)資金,又帶頭捐款,在村東的河上,也就是當(dāng)年他去要飯歇腳的地方,架起了一座石橋,消除了老鄉(xiāng)們的涉水之患。
從前,有許多人親口對我講過,說父親是個誠實(shí)的人,是個老實(shí)人。
當(dāng)下,“老實(shí)人”在一些人眼里是個貶義詞,意思是沒能耐、比較窩囊。但我認(rèn)為他們說父親的“老實(shí)”是褒義的,是說父親講誠信、不欺騙。
父親在任邢臺縣西水東調(diào)指揮部副指揮長時,夜以繼日地為野溝門水庫的修建和東調(diào)水渠的開挖忙碌著。
有一天,他帶技術(shù)人員到西河口水渠涵洞施工現(xiàn)場查看,為鼓勵他們大干快上,面對幾十名民工,父親承諾,明天中午他要親自給大家送飯。
不料,第二天上午一陣電閃雷鳴,天下起了大雨。快到中午時,父親冒雨擔(dān)著蓋有塑料布的兩桶面片湯,手提一布袋饅頭出現(xiàn)在施工涵洞。他衣裳上的雨水不住地滴滴答答往下掉。
民工們一見,都驚喜地圍了上去。
帶班長上前緊握父親的手,激動地說:“指揮長,這么大的雨,叫炊事員送就行了,您還親自來!”
父親說:“既然我說要來,就得守信用。”
帶班長說:“非常感謝指揮長!我一定要帶領(lǐng)大家埋頭苦干,不辜負(fù)您一片期望!”
1981年夏天,我剛到城里參加工作。娘和兩個妹妹,從山里的賈莊村,搬到了邢臺市楓林街縣社家屬院。那時,大哥和二哥都已結(jié)婚另過。父親要求我和三哥搬回家住。
長這么大,我和父親在一起的時間并不多,猛一下生活在一塊兒不習(xí)慣。況且,父親對我們很嚴(yán)厲。在家住了一段時間,覺得別扭,于是我要求搬回公司住,理由是公司安靜、有時間看書學(xué)習(xí),這一要求卻遭到父親反對。當(dāng)時,我并不理解父親。后來,他在跟同事們談話時,我在一旁聽到了,才懂得他這樣做的目的:一是便于培養(yǎng)父子感情,二是守在身邊便于管教。
我一直認(rèn)為父親是一個粗魯?shù)娜耍驗(yàn)樗?jīng)常罵孩子們,尤其對我更甚。我參加了工作,有一次和他犟嘴時,他還杵了我兩拳,結(jié)婚后,他還當(dāng)著我妻子的面罵過我。但那一次,父親領(lǐng)回來一位客人,在我家住過一晚上。從此,我改變了對他的看法。
那是一個冬天的傍晚,下班回家的父親,身后跟著一個花白頭發(fā)、農(nóng)民打扮的老者。
一進(jìn)屋門,父親便請老者坐在沙發(fā)上,然后對我說:“這是我的高小老師,讓你娘炒倆菜!”
平時,我家飯桌上都是一盤菜,那晚出現(xiàn)兩大盤不同的炒菜,證明家里來了貴客。
我們圍坐在小低桌周圍,父親請老者坐在平時他坐的沙發(fā)里,父親,則和我一樣,坐在一邊的小板凳上。
吃飯時,父親不時客氣地讓老者夾菜吃,還親手給他遞燒餅。
老者只教過父親一年的課,卻成了父親永遠(yuǎn)的老師。
第二天早晨,老者起床后,父親從自來水管里接了涼水,又從暖瓶里倒出熱水,用手試過水溫后,才請老師來洗臉。老師洗臉時,父親手拿毛巾恭敬地站在一邊。老師洗完,父親遞上毛巾,然后把臉盆的臟水倒掉……
在家,父親對我們這些子女很嚴(yán)厲;可在外,他從不拿官架子。他對人很有禮貌,特別是對鄉(xiāng)下的農(nóng)民,像是和風(fēng)細(xì)雨,唯恐他們感到陌生或者不自在。
父親當(dāng)副縣長時,主管我們縣財貿(mào)工作,可以說從他手過錢無數(shù),而實(shí)際上,父親是一個很仔細(xì)很節(jié)儉的人。
三哥結(jié)婚前,每月的工資都要交回家里,手里只留一百元的零花錢。三哥結(jié)婚后,父親仍要他向母親交工資,父親的“苛刻”實(shí)在叫人無法忍受,三哥只好搬走另過。
每月,我的工資交沒交,父親都要過問。我是上發(fā)薪還是下發(fā)薪、工資多少,他都一清二楚。
1992年我結(jié)婚時,父親要給我在木器廠定做大哥、二哥、三哥結(jié)婚時一樣的一套家具:一個半開門的立柜,一個雙人板床,一個寫字臺,兩把木椅,另外縫制幾套被褥,除此之外,沒有別的。
“現(xiàn)在什么年代啦!”妻子極力反對。
經(jīng)過幾次“拉鋸”、磋商,無奈下,父親才同意給我換成一套組合立柜、一個包廂床、一個寫字臺、椅子換成了一組拐角沙發(fā)。彩電和洗衣機(jī)都是妻子陪送的。
父親對我們很“小氣”,其實(shí)他對自己也是如此。
父親是從苦難中走過來的,所以他年輕時就很懂得如何縮衣節(jié)食。
從前,我聽他的同事說過,跟他出差在外很憋屈,他啥東西也舍不得買不說,吃飯還要撿最便宜的。
父親退休后的第二年,搬到了縣地稅局家屬院去住,當(dāng)時,他對母親說:“你看咱多享福,住的和金鑾殿一樣,比以前皇帝住的皇宮都強(qiáng)。”
其實(shí),他住的是一套極平常的單元房,但在父親眼里,這已很奢侈了。
父親從沒主動讓人給他過過生日。
他當(dāng)領(lǐng)導(dǎo)時,單位里幾個晚輩,每年都嚷著要給他舉辦生日宴會,他總是推脫說:“等退休了再說吧!”
而退休了,人們再催促他時,他又推脫說:“過生日太麻煩,以后老了再說吧!”
直到他六十九歲那年,子女們都要求給他過生日時,他才說:“明年吧!等我七十歲了吧!”
可就在七十歲生日的前夕,他突患腦出血成了植物人,再沒醒來。
從父親成為植物人那年起,每到父親生日那天,我們兄妹六人都不約而同聚到一起,給躺在病床上的父親,給沒有意識的父親,舉辦生日宴會,算是彌補(bǔ)我們這些做子女的遺憾。
我最早記事,是父親蓋老家的紅石頭房子。那時,我還是一個光屁股孩子,常在石頭堆里穿行。石匠叮叮當(dāng)當(dāng)鑿飛的石渣,濺到身上,疼得我呲牙咧嘴,然而還沒顧上喊出聲,就被石匠呵斥跑了。
爺爺本來在老家的垴上給父親分了兩間舊房,我出生那年夏天,幾場暴雨竟使石板房滴滴答答漏個不停,再說孩子們越來越多,炕上擠不下,蓋房便成了家里的當(dāng)務(wù)之急。父親心里卻暗暗叫苦,因?yàn)樗掷锛葲]錢又沒糧。
在橫穿村中小河的西側(cè),大隊給我家劃了一塊宅基。父親決定借錢借糧先蓋三間新房。
他抽空匆匆回家,當(dāng)天找石匠、找家具、發(fā)面蒸饅頭,一刻不停,直忙到夜里12點(diǎn)。第二天凌晨4點(diǎn)起床接著蒸饅頭。父親和石匠們一塊兒抬石頭運(yùn)石頭。平時,他一頓飯要吃3個饅頭,那幾天中午,也不知道是累得還是舍不得吃,他只吃半個饅頭就吃不下去了,下午還要繼續(xù)干活,手指都磨出了血印。離開家后,十天半月才能緩過勁來。
因?yàn)樯w房子,家里過幾年緊日子,經(jīng)濟(jì)上緩緩勁,然后再接著蓋。老家現(xiàn)在那一全院,父親分三次才蓋好。
我十歲那年平生第一次“出遠(yuǎn)門”,是去父親“單位”。 那時,父親住在野溝門水庫建設(shè)工地的工棚里。我放了寒假,陪他去值班。
人們大都回家過年了,工地上顯得很冷清。我在那里住了十多天。
野溝門水庫距我老家只有三十里地。回家時,父親沒時間送,我是搭順路的貨車回來的。
平時,修水庫的民工一萬多人,幾十個施工點(diǎn)同時施工,供應(yīng)、技術(shù)、民工安排、處理傷亡事故……諸多的事情忙得父親不可開交。父親有時到漿水、有時到山西陽泉出差,經(jīng)常從我們村邊路過,可他就是顧不上回家看看。古代有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父親修水庫五過家門而不入是常事。
后來,父親在縣商業(yè)局當(dāng)了副局長,在縣供銷社當(dāng)了主任,在縣政府當(dāng)了副縣長……父親曾代表邢臺縣政府,兩次出席全國“學(xué)大寨學(xué)大慶”等重大會議,并在會上作典型發(fā)言。
至今,家里的墻上,還掛著父親當(dāng)年受到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國家領(lǐng)導(dǎo)人接見時的合影。
很多人這樣評價父親:他是靠實(shí)干“上去”的。換言之,勤勞使他一步步走上了領(lǐng)導(dǎo)工作崗位。
父親的品質(zhì)、作風(fēng)、性格、愛好等等,自然不自然地在我們這些孩子們以及孩子們的孩子們身上顯現(xiàn),自然不自然地形成一種“門風(fēng)”,形成和確立了我們的家風(fēng)。
如今,我們兄妹們都過著幸福的生活,而我們的身上,始終都保持著那根深蒂固的、質(zhì)樸的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