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厚的一切都值得回憶(二篇)》石英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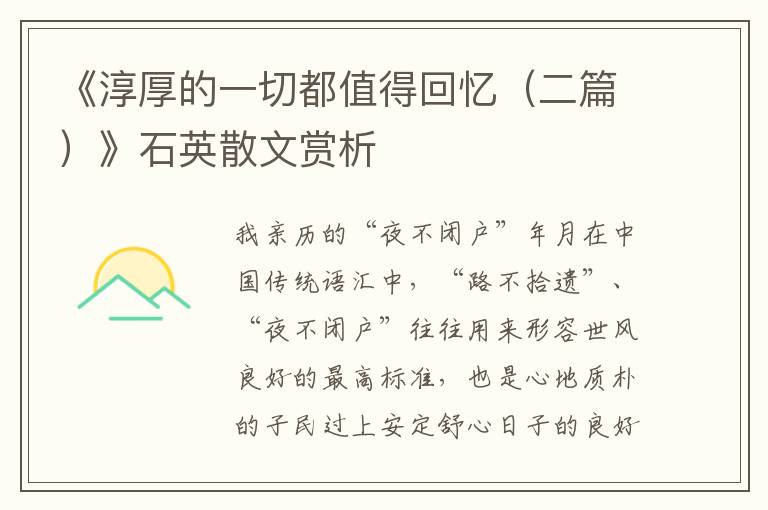
我親歷的“夜不閉戶”年月
在中國傳統語匯中,“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往往用來形容世風良好的最高標準,也是心地質樸的子民過上安定舒心日子的良好期望。也許,在很多時期,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前,這一目標基本上是不可能實現的奢望,但也并非絕對如此。很長時間以來,我就想寫一寫這個特殊的例外情況,寫一寫親歷的故鄉膠東解放區曾出現過的類如“夜不閉戶”這樣良好世風的時段,是不無意義的。
這樣的狀況曾有過兩個時段:一個是1945年日本投降至1947年秋蔣軍大舉進攻我們家鄉解放區,持續了約兩年半的時間;另一個是蔣軍逃竄之后的1947年冬至1948年。我參軍離鄉后數年未回,此后的情況知之不詳。我只記敘我親眼見到與親身體驗到的真實情況。盡管也許還只是幅員不太大的一個范圍。
第一個時段的東風實際上自1944年深秋即開始吹拂。那時,國際上反法西斯戰爭節節勝利,在國內抗日戰場我八路軍、新四軍已展開局部反攻。當時我縣的縣城尚未解放,但武工隊和地方民主政府工作人員已在縣城周圍的農村進行活動,縣城中日偽軍事實上已成甕中之鱉,其中偽軍除最頑固的八中隊偶爾還敢出城搞點動作,大都已成為縮頭烏龜。以我所在的村莊而言,距縣城雖僅僅六華里,我黨政軍的影響已深深滲透進來。村小學已為抗日進步分子和地下黨員所掌控。張校長是村中首富的公子,卻早已是一位熱情澎湃的進步青年,教“修身”課的女老師我后來知道也是地下黨員,“大飽學”戰老師為人正直,從未向漢奸惡霸低頭。村里的佃戶老梁是外縣來此定居的老黨員。以他們為“內應”,我南山根據地的“包袱客”夜間基本已可自由進出。“包袱客”者,是因為區縣工作人員習慣以深色包布裹著書報之類,故人們便以“包袱客”作為八路工作人員的代稱。
這時,東風所吹拂和滲透的內容包括村小學成了進行抗日愛國教育的基地;音樂課時教唱進步歌曲;“修身”課“摻”進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的內容;“包袱客”們以各種巧妙的形式宣傳減租減息的政策,合理解決租佃關系和突出矛盾。與社會秩序關系最為直接的是:將原來由各家輪值、老弱病殘充數的夜晚“打更制”加以改造,逐步滲入由素質較好的青壯年組成自衛團,每晚執勤巡邏。此項措施使肆虐數年的頑偽游雜流氓盜賊對中小戶農家的夜間搶劫風得到有效抑制,許多中小戶得到了安定踏實的生存環境。他們互相傳頌:“城里的鬼子、二鬼子還沒跑,咱們就嘗到了解放的滋味!”
日偽投降,縣城解放后,廣大群眾揚眉吐氣,正風勁吹,邪氣下降。民兵、自衛團組織得到強化,勞動光榮、勤儉持家的價值觀得到張揚。村、鄉鎮、區、縣各級都涌現與評選出勞動模范。記得在我村舉行的勞模表彰大會上,有位姓紀的勤儉忠厚的老農民戴上大紅花,被請到臺上,由村長和農會長獎給他一把鋼口上好的大镢頭。這位平時說話都有點結巴的“老莊戶”,也當眾講出了“要做好人,做正經人,做勤勞的莊稼把式,靠歪門邪道禍害人的人沒有好光景”。他這番老實巴交的心里話,提升了正氣,潛移默化地震懾了不務正業、游手好閑、小偷小摸的二流子混混之流。與之同時,還適當打擊了坑害良善的惡行。本村有個邢姓的混混,自年輕時就橫行鄉里,人不敢惹,1946年第一輪土改開始,他自以為他既非地主又非富農,似乎可以渾水摸魚。有天晚間,他趁本村馬姓富戶之妻獨自在家時,翻墻入內,巧言誘惑,欲行非禮,這位婦女拒之,喊聲驚動了街上巡邏的民兵,將施暴未遂者抓獲。村農會為此召開批斗大會,該邢在眾人指斥下只好喏喏表示:“以后不敢了,一定重新做人。”但他卻惡習難改,幾年后聽說又“犯事兒”,那是后話。
正反兩面的事例及有力措施,極大地教育了各階層群眾,一時間,和諧互助之風,感激黨和政府土改等利民政策之風,影響深遠。就連多數的懶漢、二流子也認真干活了。記得有一刁姓中年男子,半生不務正業,鄰里人等視若害蟲,但自從分得三畝水澆地后,一反常態,對莊稼活不僅愿干了,而且會干,竟使人們對他刮目相看。
由此,社會秩序良好,以往發生的盜搶、截道剪徑、勒索拐賣等案件可謂絕跡。許多人家不再將門戶看得那么緊了。一個細節我終身難忘:有天晚上睡前我照例去上門閂,掛上“門吊”,母親自自然然提示我:“把門推上就行了,啥事也沒有。”其實,閂上門本是舉手之勞,也不多費事,而母親卻認為多此一舉,充分說明一種對環境完全信賴的心態。
但隨后不久又是蔣軍的瘋狂進攻,燒、殺、搶、奸,濫施暴行,故鄉解放區陷入災難之中。
幸而災難不久即已過去,敵軍為收縮戰線,相繼放棄了一些地方,至1948年初,僅余煙臺、濰坊、青島等城市尚為敵盤踞(稍后煙臺又告收復)。鑒于膠東解放區遭受嚴重破壞,生產亟待恢復,上級領導又發出“節約度荒,恢復生產,提倡互助組,大力支援解放戰爭”的號召。軍民同心協力,生產逐漸恢復,人民生活得以改善,社會秩序、人們的生存環境又漸漸恢復到前年的良好狀態。這時地主、富農也相對得到妥善安置,同樣是“耕者有其田”,自食其力,得以溫飽。但也有個別的不勞而獲者,如分浮財時因其窮而享受一等“果實”的二流子、混混,又揮霍成一貧如洗的“窮人”,故態復萌,手持空口袋到安分小戶去勒索財物而被抵制,自感好景不在而絕望。我記得有一張姓無賴在妻子與其分手后又不肯“學好”,無奈而服毒自斃。對此無人憐憫,只有感嘆而已。
總之,我們那片地方又恢復了并不富裕卻欣欣向上、社會安定而共享清平的“夜不閉戶”的日子,至于是否達到“路不拾遺”,我當時并未做調查,何況在那時候,縱有人不慎而所遺,恐也沒有值錢的物件。
回想當年,仍不難得出這樣的認識:只要方向對頭,措施有力,政策把握得當,必然大得人心,社會風氣向上,邪行空間緊縮,如此一來,所謂“夜不閉戶”,不會只是一個美好象征而已。
村邊葦席上的課堂
我在故鄉解放區上小學直到上初中時,應該說是有兩個課堂的。一個課堂在學校教室里,這里的主講當然是老師們;另一個課堂在村邊田頭,夏秋之間坐在葦席上納涼,納涼的時刻其實也是在“聽課”,有那么幾年的時間里,主講人是我的叔伯二舅曰潤和我家東鄰的三胖哥。二舅大半生走南闖北:下關東,去北平、天津,在大上海洋人餐館當過兩年學徒;還是一位京劇票友,地方戲劇種中,起碼評戲、梆子、河南墜子也能唱兩口,年將半百回鄉結婚生女,又成為種地的把式,再也離不開家鄉土地了。三胖哥年輕時在青島榨油廠干過“外城客”(即跑供銷),在德國經營的膠濟鐵路小五金門市部當過幾天“帳桌先生”(即會計),故鄉解放后反而回到家鄉,趕集下店做個小買賣,平時也是在家門口的兩畝水田里種菜和水果,尤其對蒔弄櫻桃和“高麗果”(草莓在我鄉的俗稱)很有一套技藝。但不論是二舅還是三胖哥,都是名副其實的“故事簍子”,曰潤熟諳本地歷史掌故,而三胖哥對于膠濟、津浦鐵路沿線地理風物耳熟能詳。
我作為一名虔誠的學生,是每堂課(亦即每個晚上)都到的。還有兩個學生,一是我的表弟,還有一個叔伯表弟(曰潤二舅的侄子)。這課堂說小也真小,只有一領葦席的見方;說大也真夠大,村邊東西五十米,北南一直深入幽綠的青紗帳。哦,其實師生也不止眼前這幾個人,看螢火蟲燈會,聽蟋蟀伴奏,還有夜風五味雜陳,我一面聽講,一面也在嗅覺中分辨著各種正在旺長著的作物的味道。
二舅、三胖哥演說的具體內容非常豐富、廣泛。有的是歷史故事,眾所周知的如關公、岳飛、戚繼光等還是百聽不厭,因為舊的內容中還有新認識,表面上都明白了,細想還有疑問。與在課堂聽講不同的是:聽者能夠隨機插話,總是有來有往,彼此都能受到啟發,增加了不少樂趣,遠比課堂上的氣氛平等、民主。還有一些反面的和有爭議的人物如韓復榘、吳佩孚、張宗昌和劉珍年,他們中大都是軍閥,而且幾乎都跟本鄉本土關系緊密。吳佩孚是蓬萊人,在我縣東面;張宗昌是掖縣人,在我縣西面,都是相距不遠的鄰縣。二舅說吳是前清秀才,文人當了武將,外號“吳大舌頭”;張宗昌是無賴出身,不過年輕時也賣過幾天豆腐,他自己曾說過,我一生都要成為“帶刀的”。年輕時刀切豆腐,發跡了以后揮刀砍人。二舅還念了兩首據說是張自己寫的丘八詩,“學生”們都忍不住笑,這次我母親也出來納涼,她聽了也覺得好笑。韓復榘是山東省主席,至于劉珍年知道的人好像不多,其實也號稱“膠東王”,他與比他還大的軍閥張宗昌、韓復榘都交戰過,很難說是為什么,無非是狗咬狗、爭權奪地而已。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韓復榘和劉珍年原籍都是河北,韓是霸縣人,劉是南宮人,可后來都跑到山東地盤上較量,而最后卻又都死在那位罵溜了“娘希匹”的蔣委員長手里。三胖哥曾在青島和膠濟線與德國人打過交道,他說德國制造“成色”比較可靠,就拿膠濟鐵路來說,修得就挺“瓷實”,道軌鋪得很平,水杯擱在小桌板上,水一點灑不出來,可見車體晃動得很輕。但是,他也親眼所見,德國鬼子也很殘忍,為了修鐵路占地,高密一帶的農民起來抗爭,德國兵開了槍,這場血案實在是慘,“忒慘!”,三胖哥一再重復著這兩個字兒。他最自豪的是對膠濟、津浦和隴海鐵路的熟悉程度:每一個車站,就連芝麻粒小站,所有的名兒他都記得,特別是蔣介石和閆錫山、馮玉祥中原大戰的時候,他還要冒著槍林彈雨到河南那一帶去收購黃豆和花生,什么民權、蘭封、考城、馬牧集,都打得很厲害,有一回沒辦法他只好鉆進一大車黃豆里才躲過了槍子兒……(過后許多年,我才悟出焦裕祿同志工作過的蘭考縣就是當年蘭封和考城兩個縣歸并的。而蘭封、考城這兩個地名就始于聽三胖哥講課所得)。我最難忘有一次是我主動向二舅提問而引發出來的。這就是關于我縣老縣城當年的氣派是啥樣子。
曰潤二舅對這個話題,一開口就眉飛色舞,他將老黃縣的沿革也先交代了一番,自豪地說:“咱們黃縣是秦始皇建三十六郡時就設立的,起先在如今縣城東面的黃城集,現在還是一個大鎮,三國書上那個東吳大將太史慈就是這個疃的人。直到北齊天保七年才遷到現在這里建新城,城墻外面還有一道圍子,城門里邊還有閣門,講究著哪!”他說縣城最1CDqCOEiXQ5Ybr7lMnE854tk2Sni9YuoS1DPFUmWBh4=興旺的時候是在抗戰前的三十年代,西閣外的老戲樓常有名角上演,趕上廟會時周圍人山人海,多么牛的富家子弟票友想在這里票戲,至少也要先付三十塊大洋才能露一手。西面三十里的龍口港的戲園子,北平和天津的名角常來演。別看龍口這港不大,可離天津不遠,有定期的火輪船,來去方便,所以四大名旦、四大須生中有好幾位都來過。他說老縣城頂興盛的時候有兩千多家商號,大都“整”得很勢派。甭說綢緞莊,就拿藥店來說,西圍門里的“登仁壽藥局”,門前是小河、拱橋,河岸兩邊是用成千上萬顆經過精選的鵝卵石鋪的,有坡度有形,遠遠看去,嘿,漂亮,藝術!那時就有人說:來登仁壽抓藥,還沒進門病就好了一半。二舅說他對比了上海、北平、天津的中藥房,也沒見到有登仁壽這般氣派。他的話還真不是夸張,因為我也親眼見過。日本投降后我進城,登仁壽還在,就是1947年秋天蔣軍進攻膠東,侵占我縣城,為了修工事,鏟平碉堡的射擊線,便把“登仁壽”全平毀了。
以上,是我壓縮了又精簡的敘述,便不難看出當年村邊葦席上的“課堂”,兩位“講課”人所講的內容,舉凡史地、人文、經濟、民俗種種,有許多是我在學校課堂上聽不到的。而且只要講者在、聽者在,就沒有學年,也沒有“畢業”之說。
但對我而言,是止于參軍之日,不得不中止了這“天地人”課堂的知識所獲,而不能不作為村邊葦席課堂的一名“肄業生”。
從此,我不見了那領葦席,也久別了兩位義務講課人。當我追憶時,已無法完全分清我所擁有的知識哪些是源于村邊葦席上所得。但我只知道,多少年來,任我西至霍爾果斯邊境口岸,東至普陀山頂,南迄三亞海濱,北到黑龍江撫遠漁村,再也沒有機會重會當年葦席課堂聽講的情景。后來我才發現,其實我一直沒有放棄席子,哪怕不再聽課,只是看一眼我和本村長輩坐過的席子也好。因為,故鄉的一尺地,心中的一丈天哪!
終于有一天,我在新疆賽里木大草原珍愛地仰臥望天,突然一片白云飄來,與我的視線直上直下地凝住了。幻覺中,我覺得它就是我當年與長輩們坐過的那領席子,也許它一直在隨著我的神思追蹤著我,(只是不知道席上有沒有二舅和三胖哥),而我這么多年無暇注意罷了。
是它,我假定就是它,不,我確信就是它。它馱著時光,馱著人生,帶著體溫,穿過云煙。哦,這席子——云朵,灑下幾滴雨星恰好落在我的唇邊,我細品著,清甜,也有點兒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