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恩典》許松濤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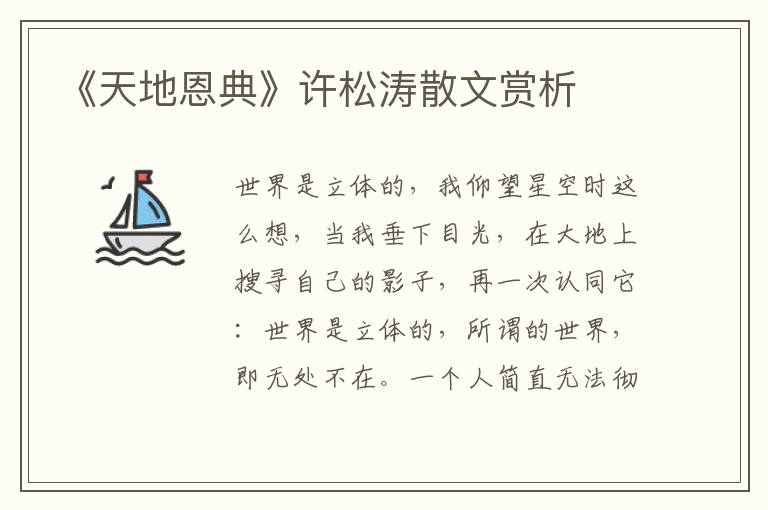
世界是立體的,我仰望星空時(shí)這么想,當(dāng)我垂下目光,在大地上搜尋自己的影子,再一次認(rèn)同它:世界是立體的,所謂的世界,即無(wú)處不在。一個(gè)人簡(jiǎn)直無(wú)法徹底認(rèn)清這座迷宮。難道不是嗎?我低頭尋思,腳邊一口陰暗的井,很老很老的井了,它屬于某個(gè)朝代,它所在的位置,應(yīng)該是從前某個(gè)大戶人家的庭院,抑或是在某戶恬靜的四合院里,因?yàn)槲規(guī)缀趺咳ヒ粋€(gè)這樣的地方尋覓古跡,井就在這些處所安靜地迎來(lái)送往,用青苔,用安靜的水銀的波紋,我是根據(jù)一口井在這樣的地方對(duì)端它的從前的,有沒(méi)有道理呢,當(dāng)然不由我斷定。
再繼續(xù)尋覓,就不是一口井那么簡(jiǎn)單了,我發(fā)現(xiàn)了腳下的河流,無(wú)論是寬是窄,無(wú)論是季節(jié)河或不是,無(wú)論它是否浩茫抑或潺潺,我都心生敬意,它跑了那么遠(yuǎn),流經(jīng)的地方那么多,即使偶爾斷流,它總能與季節(jié)與天時(shí)相呼應(yīng),一條河的濫觴從此開(kāi)始。我熱愛(ài)每一條河流,像熱愛(ài)每一口老井一樣,我常常懷念老井時(shí)記起了每一條河,即使它們與我家鄉(xiāng)的河流無(wú)關(guān),我還是由此及彼地想到它們,它們依稀就流淌在我的生命里,像一個(gè)秘密的網(wǎng)絡(luò)。我懷疑天人合一的相生相克關(guān)系被確立、被接受,從來(lái)都不是無(wú)端的,即使我寧可相信無(wú)中生有,但無(wú)端肯定不會(huì)存在。事物間秘密的聯(lián)系和溝通,并非我輩有限的智力所能窮盡。我認(rèn)為人體的每一條看得見(jiàn)的血管,錯(cuò)綜復(fù)雜卻井然有序地布置在應(yīng)該安置的位子,恰到好處如本然天成。難道不是造物主的恩賜?難道不是天意的設(shè)計(jì)和神來(lái)之筆的安排?這些天衣無(wú)縫的對(duì)接,使我陷入對(duì)世界奇妙和神奇的叩問(wèn),結(jié)論雖不是我輩所能下的,卻吸引了無(wú)數(shù)窮極物理的人們?nèi)ヌ剿鳎ラ_(kāi)墾未知的空間。
我還是回過(guò)頭來(lái)觀察一口井和一條河的關(guān)系吧。恕我冒昧地打個(gè)比方,井在縱深的過(guò)程中,它是以最為簡(jiǎn)潔的路徑、最短的距離,向一個(gè)更深的未知邁近,不止是一口水井,它長(zhǎng)年累月安靜地坐在院子的中心,給一個(gè)四世同堂的家族帶來(lái)興旺和安逸,帶來(lái)祥和與底氣,讓青磚、黑瓦、檐角、青苔、衣架、立柱形成一個(gè)雅致而安謐的對(duì)應(yīng)空間,將一個(gè)家族的氣息和血脈在家與國(guó)的境界里持續(xù)綿延、繁盛下去,井也代表了一個(gè)家族的深度和緣起。仿佛暗示某種來(lái)歷,強(qiáng)悍之中綿柔氣象的彰顯。井不說(shuō)話,而所有的語(yǔ)言容納其間,在廳堂、條幾、八仙桌、太師椅和旗袍、馬褂、山水字畫(huà)和古箏的調(diào)和聲中,茶、瓷器、陶壺、火爐、米酒中間,井是個(gè)安靜的處子,又是個(gè)定力突出的奇人。井是一個(gè)家,一個(gè)村莊,或者一條街道的軸心?那么誰(shuí)會(huì)認(rèn)為軸心的位置給了井、給了水?不止是水井,井的族群也無(wú)限深廣。油井,大地的深處,井并非與水構(gòu)成唯一的親緣,黑乎乎的井架為黑油油的深井向藍(lán)天展示雄偉的高度時(shí),誰(shuí)會(huì)想到那些未來(lái)的煙囪以工業(yè)文明的名義來(lái)污染人們的肺葉呢,侵蝕人們的健康呢?我們從來(lái)不懂得大地深處的脈動(dòng),坎兒井,沙井,暗藏的力流在洶涌,仿佛那是一條河在某處的決堤,突然的強(qiáng)壓使億萬(wàn)年的流淌找到了噴發(fā)的出口,解脫羈絆,揚(yáng)眉吐氣,豁然開(kāi)朗,甚至,這樣的井噴不止發(fā)生在荒漠,還能展示在深海的溝槽,海上的鉆井平臺(tái)簡(jiǎn)直是一塊漂浮在汪洋里的陸地。而一條河,九曲十八彎,在大地上漫流、低洄,似乎是淺吟低唱,但是有誰(shuí)看到了它的強(qiáng)悍、暴烈與澎湃?這些河流首先挽留了遷徙的人群,他們不再逃難,命運(yùn)從此安頓下來(lái)。從高空鳥(niǎo)瞰,那些河流像一張盤旋的唱片,圍繞一根帶磁性的唱針,發(fā)出四季的轟鳴,即使有沉寂的部分,它的樂(lè)音總在大地上繚繞,輕吟,盤旋,與天上的云朵和倒旋的星河遙相呼應(yīng),這是誰(shuí)也不曾料想到的恣肆橫溢又收斂自律的狀態(tài),與井對(duì)峙,交叉在無(wú)垠的時(shí)空之中,多像一個(gè)立體坐標(biāo)系的本身,它們是早就被上蒼設(shè)計(jì)好的物件,以河道和井壁的渠道,管制并有序地制動(dòng)著星球的整體。疏朗。簡(jiǎn)約。固執(zhí)。不可更改。
有一天,我在小城的古巷子里漫步,游走。城市是細(xì)密而繁雜的,掩映著來(lái)自遠(yuǎn)古時(shí)光里的氣息,一磚一瓦,一巷一弄,青石板,凹陷在時(shí)間深處的轍痕,被磨礪得圓溜溜的黃花石,粗糲的石磙與石碾,它們的材質(zhì)與井欄上的井欄材質(zhì)無(wú)異,這些足以傾頹的物件,記錄了時(shí)間的通道和里程,一如腳下的巷子存在,映照古今的變遷,它們是一群散落在時(shí)光縫隙里的紀(jì)念碑,是風(fēng)通過(guò)的河流,是落葉墜入的井廊,我撫摸那些被粉飾后的墻,依然感知到內(nèi)里肌膚的斑駁。我是自己的嗎?一瞬間,我不忍質(zhì)問(wèn)自己,我立即否定了這個(gè)最粗淺的質(zhì)問(wèn),生命的個(gè)體雖然發(fā)自自我,卻孕育于自然的精氣。巷子外是一條河,河水瘦瘦的,每年的汛期才能漲滿,人們愛(ài)河,然后架起了橋,一座不大的古城,竟然有一條環(huán)腰的玉帶,這河與一條著名的巷子依稀是天生的一對(duì),那些巷子穿越舊時(shí)光的舊網(wǎng),打撈歲月的鱗片,我在暗淡的燈光里閃爍著自己的影子,在漆黑的石板路上敲擊出陣陣蛩音,物是人非,那些前朝往事都恍惚如夢(mèng)了,而那些浸透前朝光陰的雨水,那些閃爍在頭頂?shù)年?yáng)光,分毫的差異也沒(méi)有。那些斑駁的石墻縫里冒出的不是青藤,不是灌木的枝葉,而是來(lái)自時(shí)空的回音。浩蕩,渺遠(yuǎn),幽寂……好像這曾經(jīng)的鬧市,同樣是更遠(yuǎn)古的山谷,空谷回音,那些沒(méi)有流失的水土,又把我們帶回到如今。從河沿上的八座不同材質(zhì)的橋就可以歷數(shù)時(shí)光的飛逝之快,河沒(méi)有動(dòng),卻因?yàn)闃虻牟煌粍澐譃椴煌臅r(shí)間段落,每個(gè)段落都有各自的強(qiáng)音,如果我回到橋上,站在不同的點(diǎn),都能找到一段值得回憶的歷史與之洽談,即使年代有激烈和動(dòng)蕩的時(shí)刻,正如橋下的浪花挑選浪尖,我矚目遠(yuǎn)眺貫穿在河沿上的風(fēng),以深邃的目光穿越面前無(wú)窮遠(yuǎn)處的飄渺,川流不息、熙熙攘攘地經(jīng)過(guò)橋上的人流,喧囂與沉寂在一瞬間定格成一幅歷史的畫(huà)卷,不知今夕何夕,今年何年。
石橋,拱橋,廊橋,木橋,落水橋,人們從此岸到彼岸,橋是凝視河流的最佳過(guò)客,人們的身體離開(kāi)水流威脅的第一選擇是橋而不是船,這好像比船更可靠的橋任由水流激蕩、穿越,這是水的追趕,更是時(shí)間的回溯,仿佛在向未知超越。我超越了嗎?我無(wú)法回答。橋是靜的,水是動(dòng)的,這動(dòng)靜之間的聚會(huì),仿佛是一種巧合,我在某個(gè)時(shí)刻來(lái)到橋頭,再次驗(yàn)證了時(shí)間與一個(gè)人的契合關(guān)系。我喜歡梅雨季節(jié)的天氣,這時(shí)的橋仿佛比時(shí)間更生動(dòng),上游的水勢(shì)磅礴下泄,在這兒回旋,在那兒飛流直下,都是值得觀賞的美景,我情不自禁地傾聽(tīng)水聲,觀激流,渾濁的水,野獸般成群奔突,狂野恣肆地撒野,是多么壯觀和驚心動(dòng)魄啊。而一座小城為什么要在一條蜿蜒的河上建這么多橋,我暗暗猜到了決策者的用心。那是對(duì)水的渴望,對(duì)時(shí)間流逝的追逐,對(duì)時(shí)空的作答和回應(yīng)。我喜愛(ài)它的古樸,沉靜,壯美,溫文爾雅。除了每年的夏季,黃梅雨來(lái)臨的前夜,這些橋就是風(fēng)景,就是擺設(shè),然而它最終形成為一道欣賞不盡的景觀,來(lái)自建設(shè)者的匠心,人們把橋身建成彩虹的模樣,叫它彩虹橋,人們將橋身建成回廊的模樣,翹角飛檐,紅墻粉柱,金甌琉璃,南北風(fēng)往來(lái)勁吹,攔截壩下的水,或汩汩,或潺潺,或款款,或嗒嗒,晚風(fēng)習(xí)習(xí)的夏日黃昏,二胡的絲弦在這里嘔呀周折,溫馨的短笛在這兒委婉悠揚(yáng),黃梅調(diào)陪著黃梅雨,梔子花迎著老花腔,實(shí)在是文化古鎮(zhèn)的絕配,在河岸的某條里弄里流連,簡(jiǎn)直是上天的雅意和成全。
我把井、橋、河流、巷子這些屬于一座古老小城的物件排列在一起,忽然有了奇異的念頭,大地萬(wàn)物從來(lái)就是相通的。尤其是喀斯特地貌的特征進(jìn)一步被解開(kāi)自然之謎后,我的這個(gè)信念更為堅(jiān)定了。地下河,幽眇神秘,地下隧道,比比皆是,而在人潮擁擠的大都市,我簡(jiǎn)直為之震驚,人群如同土拔鼠一樣,把地下掏空了,地下商場(chǎng)燈火輝煌,一時(shí)間簡(jiǎn)直不相信是在地下,形形色色的廣告和燈光,在整個(gè)地下制造著白晝,制造仙境般的光怪陸離。地下的鐵軌載著重負(fù)的喘息將人們不斷送回地面,大地被無(wú)盡地開(kāi)發(fā),一直到某處的大地是空的!空城,不是人走光了,而是被挖空了。除了人們無(wú)盡地開(kāi)挖寶藏之外,人們的生存空間已深入到地下!我從縱橫交錯(cuò)的地鐵軌道里退回來(lái),回到我足不出戶的小地方,再次走進(jìn)那條寂寞的古巷子時(shí),高高的墻垛把我與周圍的市聲遠(yuǎn)遠(yuǎn)隔開(kāi),我立即如同跌入陷阱,我有與世隔絕之感,盡管我還能透過(guò)頭頂上的梧桐樹(shù)枝看到上面藍(lán)藍(lán)的被弄得支離破碎的天空,我仍然心里滑過(guò)一陣寒徹,墻體厚厚的,涂抹了深重的黑,這更像被埋入地層的覆蓋,我在這兒躅躅獨(dú)行,仿佛走入一條地下通道,我恍然大悟,這條古老的巷子是多么幸運(yùn),它幸虧誕生在從前。倘若是現(xiàn)在,還能有這么安穩(wěn)嗎?有多少大型建筑設(shè)施能繞它而去?它的存在,得益于位置的偏僻,它將是多么幸運(yùn)。這是地上的封閉與地下的開(kāi)放在某個(gè)時(shí)節(jié)的交鋒?
另外,我還領(lǐng)悟到,井、橋、河流、巷子,等等,它們是如此地有著同一的指向。它們雖然各為一方、不相往來(lái),雖然有不同的用途、不同的特征,然而,它們共同在策劃或指導(dǎo)著塵世,組成了一個(gè)彼此需要的格局,它們?cè)跁r(shí)空面前有時(shí)竟然可以獲得等號(hào),可以發(fā)生意義上的交換,它們是時(shí)間意義上的魔術(shù)師,千變?nèi)f化地圓通這個(gè)世界的來(lái)歷,好像是個(gè)解釋者,乃至我一次次聯(lián)想到血肉之軀的身體。一個(gè)人以自己的肉身去尋訪自然萬(wàn)象時(shí),人的世界之謎剛剛解開(kāi)一小部分,人體上的井在哪里呢,高速公路與河道在哪里呢?是腸胃?是神經(jīng)元?是經(jīng)絡(luò)和血脈?在臟器的回環(huán)往復(fù)的迷宮里,一個(gè)謎一樣的世界存在著,然而,我們因?yàn)樗究找?jiàn)慣而消失了對(duì)它的好奇和仰望,只有為數(shù)不多的人在探究它的奧秘。這是無(wú)論如何都不能回避的事實(shí),常常由于我們目光的偏頗而喪失了追問(wèn)的條件。在我路過(guò)街道上叫不出名字的巷子時(shí),我想起了這是古老身體上的一根細(xì)小的神經(jīng),一個(gè)穴位,或者,一處等待我們揭開(kāi)的謎團(tuán)。我們其實(shí)是被謎團(tuán)包圍著,我們認(rèn)識(shí)的日月和四季,我們所有的紀(jì)年,還有,仰觀的天象,把它們畫(huà)在紙上的圖形,以及從地下發(fā)掘出的甬、劍、馬車、陶罐等實(shí)物和模型,都是人類對(duì)自然叩問(wèn)的佐證。那確實(shí)是我所要探尋的通道,然而,大自然的神秘依然深不可測(cè)。
星空還是那個(gè)星空,地球還是那顆地球,而大地已經(jīng)不是原來(lái)的那個(gè)大地了,今天的大地除了自然力原始作用下的地貌山川河流湖泊之外,還留下越來(lái)越多的人類的痕跡,代表人類的意志和智慧在思考的航程中的行走,有時(shí),為了欲望的滿足,我們不惜為之瘋狂和唯我獨(dú)尊地處理了自然與自己的關(guān)系。我看見(jiàn)的那些老井漸次消失,它們?cè)谌祟惖膾仐壷酗@得落寞惆悵,同時(shí)又孤傲無(wú)比。在老家的一個(gè)塘壩下,原先有個(gè)井臺(tái),我曾經(jīng)在那里取過(guò)清水供燒飯和飲用,我用兩只小巧的木桶擔(dān)起它,晃悠悠地往家里走去,隨著腳步的趔趄而顛搖出的水散落一路,恰恰給我描畫(huà)出一條路線。后來(lái)我發(fā)現(xiàn)井干了,隨后發(fā)現(xiàn)井被丟棄的雜物填塞了,漸漸被改造的塘壩埋沒(méi)了,沒(méi)有一個(gè)人提出異議,可是它依舊像一只枯干的眼,在我的心里偶爾眨巴著它灰暗的眼神,我不止一次想起它曾經(jīng)的鮮活存在,人們淘一口井的場(chǎng)面依舊在我眼前浮現(xiàn)。我在一處開(kāi)發(fā)的老街院子里徜徉,一口天井里的井吸引我的腳步,我走過(guò)去,映照的是一方小小的天空和天空下一張飄忽不定的臉,那臉來(lái)自古人還是我呢?不甚分明,光線暗淡,井口的水面像一張模糊的底片,來(lái)自歲月的漫漶時(shí)光,我一時(shí)語(yǔ)噎,僵滯在那里。我轉(zhuǎn)過(guò)身時(shí),院子里的草在瘋長(zhǎng),花在盛開(kāi),蟲(chóng)鳴唧唧,陽(yáng)光燦爛,是個(gè)晴好的春日,我的心被這盎然春色挽住了。時(shí)間讓我記住了,我真的記住了:一切接納都是恩典!
我在大地上行走。這是一個(gè)人與螞蟻的生命共同的趨同。沒(méi)有什么驚奇,我沿著河流走,翻越高山走,趟過(guò)沙漠走,我從來(lái)都走在我想象的意境和絕境,或者我并不完全走在真實(shí)的大地上,我順隨夢(mèng)境和年華地流淌自己的意趣和感覺(jué)吧,我即使偶爾離開(kāi)生養(yǎng)我的小城池,我還是沒(méi)有覺(jué)得走遠(yuǎn),我在一座小站走下火車,我回到我的小房子,在熟悉的場(chǎng)子上收割玉米、大豆和麥子,我依舊還是被門前的一彎溪流所打動(dòng),我喜歡這樣細(xì)小的流水,輕盈,遲緩,波瀾不驚,齊岸而行的并不是河流,還有大地上的萬(wàn)物,那些花朵,青草,莊稼,屋舍,柳絲,炊煙,城鎮(zhèn),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蟲(chóng)子和樹(shù)木,哎,我以短暫的光陰來(lái)分享這永恒往復(fù)的景致,四季流淌,時(shí)光荏苒,星河垂落,紅日東升,那些歌吟不盡的雨水,那些繽紛純潔的雪花,那些燕子和蝴蝶的蹤影,都是大地上的物產(chǎn),都是上蒼慷慨的恩賜。我的精靈之物,總沒(méi)有理由不接納呢!
我挖向?qū)儆谧约旱木绘@一鍬,是我對(duì)生活的寬度和長(zhǎng)度的丈量,那是河流和井的共同杰作!我不停地挖!挖!挖!
任由靈魂飛舞吧,我是螢火蟲(chóng),我是草葉上的露珠,我是灰燼燃燒后留下的余光,我邊走邊唱,我仰望星月,我邊走邊舞,好像長(zhǎng)不大的孩子放歸自然,自然與童真是一體的。我不斷地死亡,又不停地重生,我蛻下了殼,我也作繭自縛過(guò),不過(guò),我還是要破繭的,每每的我,忽然來(lái)到一個(gè)陌生而更為新鮮的世界,興奮著,流連著,顛仆著,一點(diǎn)也沒(méi)有計(jì)較和悲切,我有無(wú)數(shù)的問(wèn)題需要追問(wèn),需要來(lái)自風(fēng)和大地的回答,但我更愿意把一切放下。我隨著河流奔跑,我在棧道口佇立,我邊走邊猜這時(shí)間的謎語(yǔ),我走在流水的影子里,日光照徹,笑聲響亮,我不記恩仇地坦然面對(duì)所經(jīng)歷的一切,一個(gè)人,一粒沙子,一陣風(fēng),大自然里可以過(guò)濾出太多的清純和天真。是的,還是把自己還給單純的大地、勇敢的河流、蒼翠的群山吧,我舉起右手,給這個(gè)世界一個(gè)深刻的造型,我將起航或道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