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的塘》駱正葵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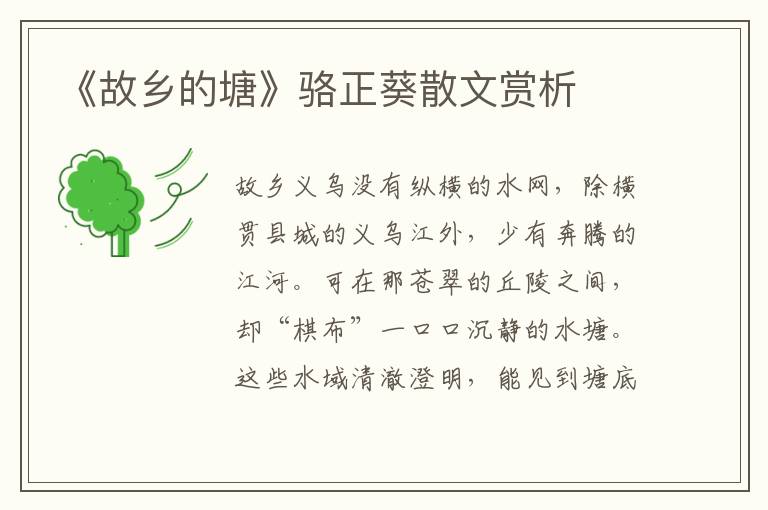
故鄉義烏沒有縱橫的水網,除橫貫縣城的義烏江外,少有奔騰的江河。可在那蒼翠的丘陵之間,卻“棋布”一口口沉靜的水塘。這些水域清澈澄明,能見到塘底漂動的水草,倏忽的游魚。灼灼陽光下,如一面面藍瑩瑩的鏡子,與天光云影,輝映成趣。我問爸:“是人工開掘,還是天成?”,“自然是上蒼的恩賜”,爸笑答。
水塘,風光秀麗,不用說“荷塘月色,菱池泛舟”,尋常景致也足使你銷魂。春天,塘岸綠柳醉輕煙,桃花綻笑臉。地上泥土滋潤,馬蘭頭,薺菜也紛紛嶄露頭角,引你去采摘。“清明螺抵只鵝”,螺螄也肥美,我們常拎只小竹籃,隨大人去摸螺螄。草葉上,樹根邊,一摸就一小把。爸好酒,螺螄是上乘酒菜。秋日田塍豆花飄香時節,鯽魚最咬“鉤”,塘邊或蹲或立的垂綸者,個個活像當年的姜太公,寧靜以致遠。天氣晴好時,我也會約幾個小伙伴,到塘邊玩摔“水漂”。揀一小片碎瓦片,彎腰用一只眼睛瞄一下,貼近水面“嗖”一聲拋出,瓦片就“飛”似的在水面噗噗向前跳動,留一條白花花水線,精靈般跳至對岸。這玩意頗含技巧性,久練才成,弄不好會“石沉”于水。
炎夏酷暑,我們就趁背草籃割牛草之機,到水塘洗澡,游泳,扎猛子。鼻子一捏,一個猛子下去,在水底俯身前沖,當人家著急等待時,人早在對面近岸處鉆出水淋淋的葫蘆頭,活像課本上的“小英雄雨來”。游泳真能練出人的頑強體魄和意志。
家鄉人歷來珍惜水環境,崇敬水塘。把“水塘”視為佳風水的“氣場”。卜居于水,臨塘而居。人與自然融會和諧,親密無間。有的連村莊也依“門口塘”而命名。什么宗塘(宗澤故里),李塘(賓王后裔世居)、蓮塘、清塘、石塘。據約略估計,凡是古村,近半村名皆帶個“塘”字,只是歲月變遷,年代久遠,有的“塘”已演變為諧音的“壇”或“堂”而已。
古縣城東有個小村落叫駱家塘,門口塘呈長方形,“長塘伴古村”。相傳唐初四杰之一的詩人,寫過《討武曌檄》的駱賓王就出生于斯。他祖父是個很有學問的宿儒,深諳教育之道。常陪少年賓王在水塘邊玩耍,觀察塘里鵝鴨悠游戲鬧。時日既久,潛移默化,幼小心靈深受熏陶。賓王七歲時,有次祖父送客路過塘邊,客人聽說少年賓王天資聰穎,令賓王對池中白鵝賦句。賓王凝視片刻,略一思索,脫口吟誦:“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其客贊嘆不已,譽為“神童”。如今村莊已廢,池塘猶存,后人于塘畔建祠塑像,辟為紀念駱賓王的公園。
流風余韻,時至現代,故鄉水塘更流光溢彩開新篇。分水塘、苦竹塘、神壇(塘),三村俗稱“義烏三塘”,出了教育家陳望道、史學家吳晗、詩人馮雪峰這三位現代史上赫赫著名的人物,譽滿神州。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古人喻水塘為“書”,堪為傳神。家鄉的“水塘”,富“源頭活水”,確是一部哲思奧蘊的書,千年萬代讀不厭。它奉獻于人的,豈只是“千鐘粟”、“黃金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