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鷹《我無比懷念那個夜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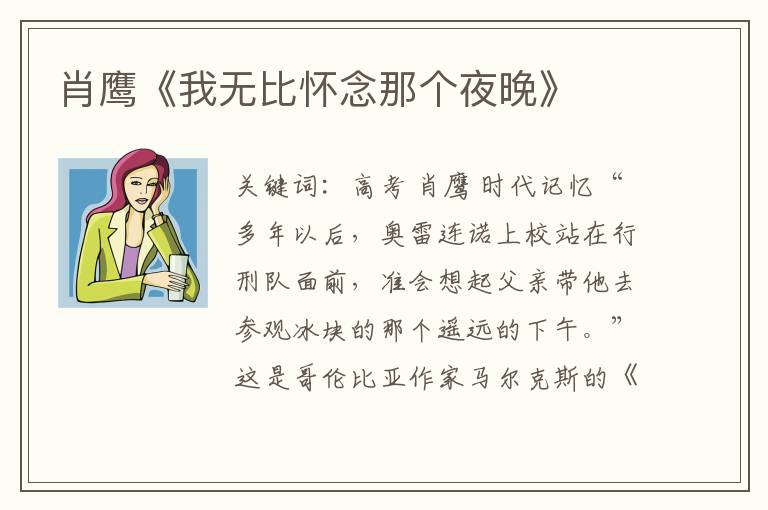
“多年以后,奧雷連諾上校站在行刑隊面前,準會想起父親帶他去參觀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這是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開篇第一句。人生無論窮達,總有某個獨特的時刻決定個人未來命運的漫長走向。對于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參加中國高考的眾多考生,三天高考結(jié)束之際,就是這樣一個決定未來命運的時刻。
1980年的中國高考,在7月7、8、9日三天舉行。考試結(jié)束的當天晚上,學校宴請高中畢業(yè)生,我舉杯把盞,一宵痛飲。40年后,當我追溯自我人生命運的轉(zhuǎn)折點的時候,首先回想起的是1980年7月9日那個夜晚,在那個夏夜,金沙江拍岸的江濤見證了一個17歲少年告別中學時代的狂放和豪邁。作為我的成年禮,我大醉三天之后,才醉意全消。套用脂硯齋評賈寶玉醉酒的話說:“鷹兄真大醉也。”
我1962年出生,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因此在我15歲之前,絕沒有“高考”意識,也沒有上大學的夢想。我的母親是原昆明師范學院中文系1962年的畢業(yè)生,上大學前,她與我父親是四川內(nèi)江市政府的干部,兩人結(jié)婚并生育了我哥哥。母親上大學時就發(fā)表詩歌、小說和劇作等作品,云南作協(xié)還為她的劇本《幸好爸爸不在家》開了專題討論會。但是,因為是四川三臺縣頭號大地主的女兒,母親畢業(yè)后不僅不能回四川與我父親、哥哥團聚,已有身孕的她,只身被分配到當時極端窮困落后的云南綏江縣中學教書。數(shù)月后,我在這里出生。再過一年左右,母親因為一個冤案被以“特務嫌疑”罪名逮捕,從此,我們家庭就淪入另類家庭。1963年被捕,直到1978年被平反,超過15年,母親的案子始終沒有審判、沒有結(jié)案,她先是被羈押,后是被勞教。為了兩個孩子的“前途”,等待多年無望之后,1970年,在內(nèi)江市政府任職的父親被迫與尚在云南接受勞教的母親離婚,兩人各自重組家庭。
我離開母親的時候,只有半歲。當時她還沒有被捕,但因為忙于教學工作,不能照顧我,就讓我的一個伯父把我接回四川老家由爺爺、奶奶撫養(yǎng)。我哥哥回到她身邊。她被捕后,我哥哥也被接回到老家撫養(yǎng),當時他5歲。
我爺爺、奶奶是四川威遠縣鄉(xiāng)下的農(nóng)民,他們居住的鄉(xiāng)村,是永新鄉(xiāng)桃李村。爺爺和奶奶共生育了7個兒女,在我童年的記憶中,我們家是遠近聞名的人丁興旺之家。我童年時代,正是20世紀后半葉社會混亂、生活困難的時代。但是,在這個大家庭中,我作為最小的孫輩之一,因為爺爺、奶奶的特別呵護,我的童年生活是甜蜜、自在的。十二三歲讀了 《紅樓夢》,我就想,雖然家境與賈寶玉無法相比,但以 “老祖宗獨寵”而論,敝人童年也與玉兄仿佛。
爺爺不僅識字,而且寫得一手好毛筆字,我幼年習字,記得就是臨摹爺爺寫的字帖。爺爺經(jīng)常教導我,寫字的關(guān)鍵,就是字要立得住,像做人一樣,站得穩(wěn)。所以,爺爺是我的文字啟蒙老師。爺爺是一家宗主,家里人都非常敬畏爺爺。逾越五十年以后,我仍然清晰記得爺爺坐在家中八仙桌后的威嚴神情——是神態(tài)自若透露出的堅毅。據(jù)伯父們講,我爺爺早年做過使用黃牛販運商品的生意,也曾是民間組織袍哥會的一個小頭目,在當?shù)厥禽^有名望的鄉(xiāng)紳。1949年之前幾年,國民黨縣政府要委任我爺爺做鄉(xiāng)長,他堅決辭絕了。一位伯父還告訴我一個電影畫面一樣的場景:當?shù)卣プ×艘粋€被誣為土匪的外鄉(xiāng)人,行刑者正要開槍的時候,忽然感覺背后站著一個人,回頭看是我爺爺,扔下槍就走了。這是爺爺在1986年去世后,我聽到的傳奇故事。這個故事有許多需要解釋的背景,但它的真實性是不容置疑的。
在我所受的兒童教育中,如果說爺爺給予我的更多是男性尊嚴和自重的品格啟蒙,培養(yǎng)我做一個“站得穩(wěn)的人”,那么,奶奶則以她無比寬厚的善良和慈愛培育我的良知之心。我幼年記憶中,爺爺、奶奶時常周濟附近幾位年老貧窮而且缺少兒女孝敬的孤寡老人。在我童年的眼中,這些老人不僅衰老而且可怕。有一位老太太,常從我家后門進家,以至于我特別害怕后門打開。但是,爺爺、奶奶待他們非常親熱,不僅把難得的好東西留給他們吃,而且還給他們帶走。奶奶似乎不識字,但她有遠近聞名的“論理”聲望,附近人家有難斷的家務是非,都喜歡找奶奶斷理。當時,奶奶已是六七十歲高齡了。我兒童時代至上小學前,除了爺爺教習字,沒有讀過書。我自半歲至10歲前,都是跟爺爺、奶奶睡一張床上,我和奶奶睡一頭,爺爺睡另一頭。當時老家還沒有電燈,也沒有廣播。奶奶身體不太好,躺下比較早。家中大小事,都會在奶奶床頭談論。奶奶躺在外側(cè),我睡在里側(cè)。奶奶半靠著床背與床前的兒孫們說話,她富有邏輯而且非常理性的話語,就是我童年的語文課。
老家的房屋坐落在一片丘陵的腰際上。房屋背后是爺爺?shù)奶伊帧4禾焯一ㄊ㈤_,順坡而上,層層渲染著悅眼的嫣紅。夏天桃子成熟,桃林就成為饞嘴的孩子們的樂園。房屋前是一個小壩子,但是孩子們的眼中,這小壩子就是一個早晚嬉戲的大天地了。從壩子沿石級而下,是一口石砌的水井。這口水井,冬暖夏涼。大旱之年,遠近的水井都干枯無水,它依然溢滿甘洌的泉水。水井背后有一棵巨大的核桃樹,它的左右兩側(cè)散布著幾片竹林,在竹林中延伸出來的小路,就是我們外出的道路了。在竹林的外面,是一塊面積很大的水田。它春夏種植水稻,秋冬蓄水。在這塊水田的外側(cè),有一排櫻桃樹,櫻桃成熟的季節(jié),望著一串串鮮紅欲滴的櫻桃,我年幼的心中是無限歡欣的。桃園,竹林,櫻桃樹,核桃樹,是我童年朝夕相處的近友。站在那塊大水田的外側(cè)田壟上,越過谷底眺望對面的山陵,尤其是在冬日晨霧濃郁的景況中,我的童心感受到的是一種冥想遠方的惆悵。
我1970年春天在桃李村的小學入學。1973年春節(jié)后,我在前兩年已去內(nèi)江市內(nèi)父親身邊上學的哥哥的勸誘下,同意轉(zhuǎn)學去內(nèi)江上學。自半歲以來,10年中,我從未離開爺爺、奶奶,但這次,我要離別他們了。我是帶著非常懊悔的心情離開老家的。在內(nèi)江,在父親重新組織的家庭中,除了父親和哥哥,還有繼母和她帶來的兩個女兒。我在這個新的家庭環(huán)境中,感受到莫名的孤獨和壓抑。父親在進入機關(guān)工作前曾從軍數(shù)年。自我懂事起,他給予我的記憶就是嚴峻和可怕,因為他的“軍閥作風”。在內(nèi)江生活的歲月中,我最希望父親出差。在他出差的日子,我感到一個被釋放的奴隸的自由。父親的同事經(jīng)常笑說:老貓走了,耗子就出來了。
父親對我少年時代的 “暴力管教”,現(xiàn)在想來,一則是因為我確實時常在學校弄出一些惹老師生氣的事件,屬于“非好學生”,父親期望我做一個“好學生”;二則因為我是另類家庭的孩子,我必須“夾著尾巴做人”。我無意做“壞學生”,但我總是管不住自己調(diào)皮的心。小學五年級,一天中午放學后,我和幾個同學不回家,把班上的桌椅堆成一個山丘,我坐在山頂上扮演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的反派主角座山雕,被來尋找我的父親撞見;剛上初中,正值全國“評《水滸》、批宋江”,我卻與班上幾個調(diào)皮的同學結(jié)拜兄弟,我做大哥,幾人還喝雞血酒立誓,被老師查獲。這些事情,都是必然被父親 “家暴”的案例。我父親總說,我是被我爺爺、奶奶寵壞了。他這個說法,讓我奶奶曾經(jīng)痛哭一場。但父親的暴力家教,從來沒有讓我內(nèi)心屈服。我父親打我,我就想,你管得了我的身,管不了我的心,我的心是自由的。
我少年時代生活的內(nèi)江城,是質(zhì)樸、清靜的,而且還有些雅致的韻味。沱江河舒緩地環(huán)繞著城區(qū),沿河兩岸老舊的小街散逸著濃郁的老四川風味。從家中走出機關(guān)大院,穿越幾條小街,就下到一大片亂石密布的河灘了。我喜歡深秋之際的河灘景色,尤其喜歡漫步走過河灘登上劃向?qū)Π段髁炙律侥_下的渡船。這渡船兩頭略為上翹,中部有一個圓拱形的竹棚蓋,船工在船尾劃著一支長槳。天色晴好的日子,河水清幽,秋風習習,西林寺的山頭,越來越近,越來越高,我的心就越來越歡暢。西林寺是一座有些年代的寺廟,在我少年時代是荒廢的。在山頂有座臨江的亭子,名為“太白樓”。我不知道唐人李白是否游歷到此,但是,佇立亭下,俯瞰秋陽下如寶藍玉帶一樣的沱江河,我的少年情懷的確是充滿詩思的,當然,也每每念及偉大詩人李白。
夏天沱江河的洪水會淹沒整個河灘,濁浪漫涌。我的小叔,父親的弟弟一家就住在距西林寺不遠的一所職業(yè)中專學校中。在夏日洪水期,一個雨意清涼的上午,我和同住機關(guān)大院的一個同學去小叔家,走到那個學校附近的河灣,見有幾個小孩在游泳,我們倆也脫了衣服跳下水。水意外地涼,這位同學很快上岸。我當時還不太會游泳,但大著膽子往外游了幾米,再往回游,忽然發(fā)現(xiàn)踩不著地,心一慌,就越不能向岸邊游,幾番沉浮中,見附近岸上有一個用纖網(wǎng)捕魚的大人。我把救命的希望寄托于他。但是,他只是喊我向岸邊游,并無動身下水救我的意思。我同行的那位同學,蹲在岸上嚇得發(fā)抖。這時,上游開來一艘汽艇,我想今日小命必葬身艇下了,就放棄了掙扎。不料,正是這艘汽艇在航行中掀起排浪,將我推向岸邊,從而得救。從小家里大人不許我學游泳,偷著游泳被大人知道后必定挨揍。我記憶中爺爺真正打我的一次,就是我偷著一人在一個小水塘中游泳。這次沱江河死里逃生,事后似乎也沒有逃過父親的痛揍。
在我少年的記憶中,父親似乎是完全為了那個時代而對我嚴酷管教。然而,他始終如一地堅持要我和哥哥努力讀書,似乎又超越了那個時代。我在父親身邊生活的日子,幾乎沒有零花錢,但是,只要我要買書,父親總是毫不猶豫地給我錢。每當繼母阻攔時,他就會大發(fā)雷霆,用他軍人的粗暴聲調(diào)對繼母咆哮:“老子就是要給他錢買書!”我在“文革”后期,購買了多本魯迅的《野草》《吶喊》等小冊子,后來解禁了,又購買了《紅樓夢》等古典文學著作。這些著作的閱讀,豐潤了我少年寂寞的心田,自然也為我后來以意外成功通過高考,作了“史前鋪墊”。如果沒有父親在那個“讀書無用論”的年代堅持讓我們兄弟倆埋頭讀書,我們不可能在恢復高考后雙雙考上大學,并且兩人都成為教授。父親是一個聰明而且工作能力非常強的人。他初中沒有上完,因為家中窮困,就跑出去當兵,三四年后,做了排里的文書,后轉(zhuǎn)業(yè)地方工作。由于長期受母親政治問題的影響(雖然離了婚),父親在機關(guān)工作數(shù)十年至退休,職位幾乎沒有提升。我至今也不明白,父親當時堅持要我們兄弟倆埋頭讀書的“前瞻”智慧是從哪里來的。因為在那個年代,母親的遭遇和父親自身的處境,都應該讓他明白, “埋頭讀書”不僅沒有前途,而且還可能遭遇厄運。我現(xiàn)在能想清楚的是,父親嚴酷要求我們兄弟倆“夾著尾巴做人”的另一面,就是要我們“埋頭讀書”。
我母親1978年獲平反,并恢復工作。當年秋季的時候,母親回綏江工作,只身從昆明經(jīng)停內(nèi)江,我們母子時隔15年后得以相見。母親在內(nèi)江住了兩天,她臨走前夕,我突然說要同她一起去綏江。父親同意了。我向?qū)W校請了幾天假,陪伴母親起程。我們母子倆下午先乘火車到宜賓,次日換乘輪船沿金沙江逆流而上,經(jīng)約一天航程到達綏江縣城。這是我平生中唯一一次單獨與母親同行。
與母親在綏江相伴度過幾天之后,我告別母親,回到內(nèi)江繼續(xù)上學。我就讀的是內(nèi)江七中80屆一班,是這個中學80屆唯一的“全市重點班”。班主任老師是一位語文教師,因為我有一次在他上語文課時開小差,他提問我答非所問,他當眾諷刺我“這就是肖鷹先生”云云,并指責我曾告訴同學“班主任老師嫉妒我的語文水平”。我確實沒有說過這樣的話。這事發(fā)生在1979年3月中旬末,我回家告訴父親后,他說,既然這樣,你就轉(zhuǎn)學去你母親那里吧。
1979年3月27日,我告別父親和哥哥,只身經(jīng)宜賓赴綏江投奔母親。當時我還不到17歲,帶著兩大件行李。到宜賓下火車后,租了一輛人力三輪車,請車夫?qū)⑽依揭粋€靠輪船碼頭近些、價格便宜的客店。因為下火車時天已經(jīng)開始黑了,這個車夫似乎并不熟悉碼頭附近的旅店,費盡周折,到晚上九十點左右,他才把我放在一個名為“反修旅店”的客店門口。這個客店非常簡陋,記憶中陰暗臟污,還是大通鋪。我和衣睡了一覺,天亮醒來,就又雇了一輛三輪車帶著行李去了碼頭。又是一天逆流而上的航程。那天時雨時晴,兩岸時而山崖云繞,時而層林雨染。在船上,我非常懷念去年秋天與母親同行的甜蜜、溫馨。在一座峻峭的山峰上,有一只山鷹在盤旋,令我想起,母親給我取名“鷹”字,一定是 “觸物隨情” (脂硯齋語)。
1979年3月末,我轉(zhuǎn)學到綏江讀書時,母親已年過45歲。我沒有母親年輕時的記憶,熟悉的人都說我母親年輕時非常美麗。在照片中,少女時代的母親曾扮演過林黛玉;母親在生產(chǎn)我一月后的照片中,是一位明麗優(yōu)雅的少婦,有人說這照片像年輕時的電影演員秦怡。15年人生厄運的摧殘,在母親的身上留下了不可消除的傷害。她帶著一身病痛。但是,母親令人意想不到地充滿活力。她重返工作崗位時,只有15年前留下的一年多的教齡。她不僅很快熟悉了教學工作,而且因為表現(xiàn)了較好的業(yè)務能力,被安排給高中快班生上語文課。我轉(zhuǎn)學來,先就被安排在這個班插讀,聽了母親大半個學期的課。1979年,進入高二學年,學校分文理科班。因為當時重理輕文的高考教學風氣,學校將我母親安排給高二理科快班上課,我因為自主選擇文科班,則不能再聽母親的課了。
我來到母親身邊讀書,父親對我的監(jiān)管權(quán)自然移交給母親。相對于父親的嚴管,母親對我的管教是非常寬松的,在她的同事眼中甚至有放縱的嫌疑。進入高二前,文理分班時,我高一時的班主任是一個物理老師,他非常希望我選擇理科班,一方面盡力說服我,一方面向我母親游說。文科班的確集中了該校學習較差的學生。而且, “學文科沒有前途”也是當時的社會流行觀念,“好一點”的學生都不會選擇文科班。母親任由我自主選擇了文科班。因為當時高中學制兩年,進入高二,就是進入了決定考生命運的最后沖刺年度,不僅老師要求更加嚴格,學生們也普遍緊張起來。但是,母親并沒有給我施加任何壓力,我甚至沒有她督促我學習的印象。每有老師向我母親告狀:“劉老師,你看看,這就是你家公子的作業(yè)!”母親聽完后常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我一定要嚴加管教!”但是,等那老師一走,母親就笑著說:“兒子,你盡讓你老媽為難!”
1979年3月末至1980年8月初,在我與母親兩人生活在一起的一年多時光中,我與母親的交談超過我與父親十余年相處的交談。母親是非常健談的人,而且談吐非常風趣。人們聊天,她只要在場,一定是極受歡迎的中心人物。她的涵養(yǎng)、見識和聰慧,是我平生所遇的中國知識女性中少見的。你很難想象一個遭遇15年牢獄之災的女性,仍然如此開朗、豁達和從容。在各科任課老師輪番角力鞭策下度過高考歲月,我一天中最愉快的時候是與母親在晚餐后在夕陽下去學校背后的金沙江畔散步、聊天。母親會不時背誦一些古詩詞。我第一次聽到蘇東坡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就是母親在我們母子倆散步后返校的路上背誦的。
我高考復習的這一年,母親盡她所能,給予了我最大的自由學習空間。我時常草率應付各科作業(yè),她是非常清楚的。但她并不過問我。臨近高考時,她在學校圖書館借到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本來只是自己消遣的。我見了就跟著看,十數(shù)天中看得昏天黑地。母親也不擔心我高考復習受影響,她只是對我過度崇拜基督山伯爵有些擔憂。大約高考前一個月,縣城影院放映新片《小花》。母親設(shè)法購買了首場電影票,在自習課時悄悄帶我去看電影。一個高中語文老師允許自己臨近高考的兒子昏天黑地地讀長篇小說,還在自習課時私自帶兒子去看電影,這恐怕是中國高考史上少有的“母愛壯舉”。我實在記不得在高考復習的課堂上聽了什么——當然努力將當時的教育部統(tǒng)編教材全部學習了一遍,但是,我課余時間(主要是晚上和周日),似乎多在讀自己想讀的書。高考前最后一個月,學校強化沖刺復習。我似乎很少理會一張又一張的復習試卷,傍晚多在金沙江畔的河灘上,以江濤為伴,逐篇背誦一本《唐宋八大家散文選》中的文章。這不是語文老師要求的,當然也不是我母親要求的。這是我少年的心靈的渴求。朝夕盤桓的金沙江畔,以及背景中那急流洶涌的江灣和對岸那似乎是千古無人的險峻荒涯,激勵和配合了我的心境。每當兀然獨立灘頭,暝色四合之際,朗誦著古人的文句,就宛然古人前來與我對話。這是我高考歲月中,最自由的心境,也是最真實的心境。
我與母親住在綏江縣一中校內(nèi)教師住宅——我不知道其中哪一間是我的出生地。我們母子開始是住在底層一個十數(shù)平方米的單間內(nèi),靠門口的小部分隔斷,作為廚房。不久我們搬到一個二樓的房間,房間面積增加了一些,分隔為內(nèi)外兩間,母親住較大的內(nèi)間,我住較小的外間;廚房則在陽臺上。在陽臺上可以越過河灘遠眺金沙江。學習一天后,佇立陽臺,靜靜眺望夜幕下的金沙江和對面江岸的大涼山山影,星空遼遠,江山沉郁,是我至今非常懷念的體驗。
我出生時的綏江縣城,因為在下游修建的一個電站大壩,如今已經(jīng)被淹沒在金沙江水之下。當然,我和母親居住的房子也早已湮滅無跡,那個陽臺上的夜景,現(xiàn)在只是我無限懷想的少年記憶。
大概是7月下旬,高考成績從省上下達。我的成績首先是從學校接收的地區(qū)教育局電話中知道的。我總分421分(滿分530分),是全省文科并列第一;我數(shù)學考分最高,96分(滿分100分),是全省文科第一。當年云南是公布分數(shù)之后報志愿。我第一志愿填報了北京大學,專業(yè)志愿是:中文系,圖書館系。我第二志愿填報的是北師大,專業(yè)志愿是:哲學系,中文系。北大哲學系錄取了我,我想,招生老師一定是意外地發(fā)現(xiàn)了我竟然在第二志愿中填報了哲學系。我在上初中后期,看了印度電影《流浪者》,非常崇拜做辯護律師的女主角麗達。我想報北大法律系,母親堅決不準,我只能放棄。
我在高考前,非常認真地向母親申明:如果考不上正規(guī)大學,我絕不復讀,因為我實在不能再忍受高考生的生活;我去草原當牧民,寫小說,如果成名,就回來報答母親,不能成名,母親就當白養(yǎng)我了。坦率說,我對于自己能否考上正規(guī)大學(更不用說考上名牌大學),心里是沒有底的。高考前云南省高考摸底考試,我的成績只是在那個50人左右的文科班上前5-6名。按這個摸底考試估計,我發(fā)揮最好,大概也只能上云南大學。高考錄取的結(jié)果,班上同學,只有三個考上正規(guī)大學,除我外,一個同學考上云南大學,另一個同學考上原江西財經(jīng)學院。以我的努力,以我的自知,我是順利地通過了高考,意外地考了個 “省狀元”——更意外地“被”北大哲學系錄取。
我無比懷念1980年7月9日那個夜晚,因為那個夜晚宣示了我的高考結(jié)束,也宣示了我的人生新歲月。在那個夜晚,我并沒有預見自己的未來會是什么,但我深知自我人生即將開始新的時代。
2020年8月22日-24日稿、28日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