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德來《記憶石坦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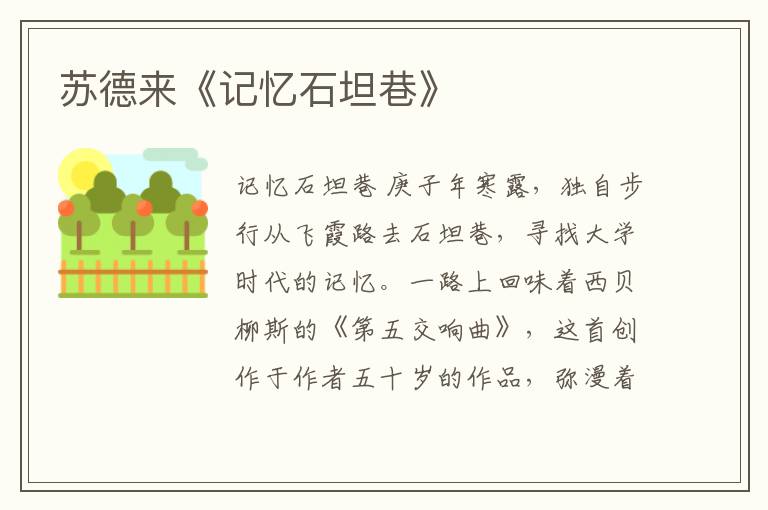
庚子年寒露,獨自步行從飛霞路去石坦巷,尋找大學時代的記憶。一路上回味著西貝柳斯的《第五交響曲》,這首創作于作者五十歲的作品,彌漫著對人生復雜,隱晦的氣息。法國號響起,少了一種少年亦或是青年的沖動,雖然,木管樂器奏起,百鳥歌唱,春天似乎即將來臨,音樂還是沉穩定性的中年人品質。《第五交響曲》,已經從《第四交響曲》悲哀,低沉的人生中出來,多了一份積極向上的心態,擺脫孤冷的味道。
孤冷,可能為人生態度,經歷后的失敗更能認清生活,人生如同在北歐的冰天雪地中艱難行走。苦痛可能是肉體,可能是思想,能夠向前走就好。
音樂,總是讓我找到慰籍的理由。自然,尋求一種溫暖記憶也是需要的。走過公園路,少年、青年的映象已經不再回歸,所謂的復古卻也牽強附會。唯有穿過五馬街的時候,不知哪一家店里播放舒曼寫給克拉拉的第一首情詩《童年情景》如此自由,天真,歡樂,充滿夢幻。鋼琴自由奔放容易感染人,特別是舒曼的這首由七個樂章組成的曲子,似乎魔力的引入回憶。
毋容置疑,我回到了年輕時光記憶。心底深處浮現出石坦巷,石板鋪陳的道路,在青磚綠瓦照應下,詩情畫意。那里有我的愛情,有聽著《水車謠》舞蹈的伙伴,有我喜歡的先生們,一切皆歷歷在目。
味蕾記憶最是鮮明的,小巷中有一家豬腸粉店和一家早點店我是最喜歡去的,粉和早點糯米飯都是一元錢一碗。現在想起來小巷的味道是最正宗。確實,我的記憶力,最多的是關于石坦巷帶來的歡樂和吃,以為少了一份讀書的愉悅。
真實的說,玩和吃相對于課堂來說我更喜歡前者,甚至我喜歡窗外的知了的歌聲,肯定的,元明清文學里的愛情故事是不如窗外知了鳴叫的。盡管年輕帥氣的老師,用他清純男高音賣力讀他在新華書店里買來的教案和文學分析之類的書本,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老師音響是有變化的,有情感,是認真的,盡管如此,卻也不如窗外知了單音節的歌聲。我以為窗外有天籟。
當然,我也喜歡宋代文學,美學,寫作課等等,教授們是有水平的。只不過花花世界總比枯燥無味的課堂有趣味,年輕只要當下歡愉。
信河街是忙碌的,車水馬龍,站在十字路口望去,幻如隔世,記憶中的石坦巷,已經成了寬闊的大道。步入石坦巷,石板路換成了水泥路。
閉上眼,回憶。尋找最熟悉的,也是在記憶中。街道左邊有幾處等待拆遷的舊房子,卻也不是熟悉的。
記憶,很奇怪,美好是甜的。
深秋的風吹著我的頭發,也撩起一股冬天的暖陽。我想起了一個風高夜黑的夜晚。
溫州人冬季來臨的時候喜歡曬醬油肉,鰻鲞等等。學院的老師也不例外,年關將至要備一些年貨的。學院樓上有陽臺,是曬醬油肉鰻鲞的好地方,北風一吹,太陽一照沒幾天即可以存放。
陽臺也是同學們常上去聊天,休閑的好去處,也是夜晚戀人們約會地方。那年初冬學院后勤處一位胖胖的老師在陽臺上曬了四條大鰻鲞,一米五左右,寬有二三十公分左右,厚有一兩公分。新鮮的鰻鲞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勾起了同學的口水。
夜晚降臨,年輕人精力旺盛,睡不著覺,到夜半議論起了陽臺上鰻鲞真大。突發奇想把鰻鲞拿來吃點吧。這個建議很快取得一致同意。并進行分工,文哥、冰哥上去偷鰻鲞,我的任務是翻墻出去買酒和取點醬油醋。
下半夜的寢室樓是很安靜的,聽到的只有鼾聲和風聲。幾個人輕手輕腳的踏上陽臺的樓梯,很順利的取到兩條大鰻鲞。到了寢室才想起這么大的鰻鲞怎么燒了吃,人多思路寬闊。用剪刀把鰻鲞剪成小塊,放在燒的快水壺里煮。
我以飛毛腿的速度從宿舍北門的鐵門翻出去購置酒和調料。回來遇到值班老師,問我,你怎么現在才回來?我說,肚子餓了,吃點心。可能是夜深,老師問了一兩句也就放行。但是,我的心臟跳動他肯定聽到的。
到寢室鰻鲞已經燒熟,我的天吶,至此后,所有的鰻鲞味道,不如那個夜晚味道鮮美。
第二天早餐,聽到餐廳外傳來,一個女高音用溫州話在咆哮,“鰻鲞給人偷了,那個狗生的偷了我的鰻鲞。”同寢室在偷樂,吃好早餐出餐廳,見到走廊架著一個小黑板,有粉筆字,“誰偷了鰻鲞狗生。”
后來,學院展開調查,大家信誓旦旦沒有做壞事。
凌晨來臨,回憶的是大學時代的石坦巷,卻不知不覺的寫到偷鰻鲞的事情,不知為何一邊寫一邊笑。
記憶石坦巷卻是用偷鰻鲞事情結束。青年時代走過的一條充滿煙火味小巷容顏大變,那明媚的陽光也只能通向心中最美麗的記憶。
我看到石坦巷深處榕樹下的一彎小河,在綠茵下閃爍著春天的綠色,它是通向九山湖的小河,也是唯一讓我在卸下黑發的年齡里熱淚眼眶的地方。
風兒響起,如同聽到李宗盛的《漂洋過海來看你》唱到的:我在最絕望的時候都忍著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