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婷《簡論范瑋《太平》的復雜性和夢幻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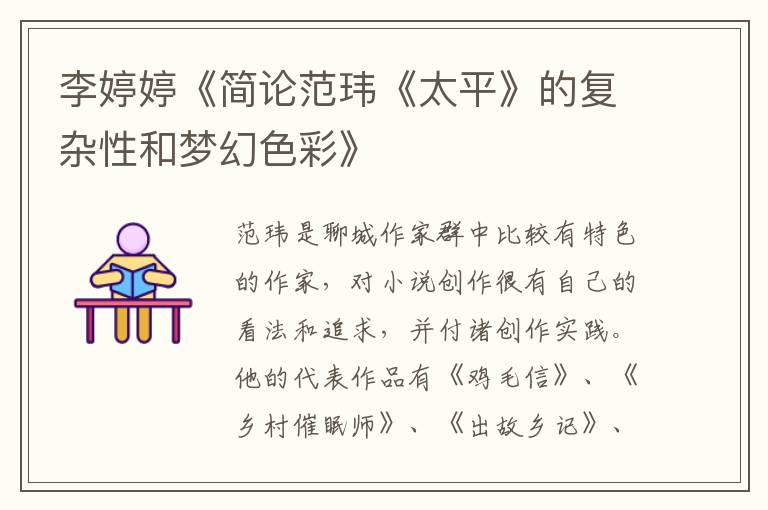
范瑋是聊城作家群中比較有特色的作家,對小說創作很有自己的看法和追求,并付諸創作實踐。他的代表作品有《雞毛信》、《鄉村催眠師》、《出故鄉記》、《刺青》等,并著有小說集《刺青》。其多篇作品被《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等轉載。其短篇小說《孟村的比賽》獲得山東省第二屆泰山文藝獎。其創作值得關注。
范瑋的小說以他成為簽約作家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他早期的創作清新淡雅,類似于白描,受沈從文、汪曾祺等人的寫作風格影響很大。后期的創作借鑒了現代派的敘事手法,極力擺脫傳統小說敘事的束縛,大膽探索,不斷突破,形成較為鮮明的個性風格。他注重小說敘事的虛幻性和復雜性,注重夢幻與現實的結合,創造別出心裁的敘事風格。《太平》是范瑋2013年創作的中篇小說,后被《小說選刊》等雜志轉載。這是范瑋近期的創作,可以說是范瑋追求復雜性的代表作。下面我從撲朔迷離的故事情節、獨特而夢幻的敘事方式兩個方面,談談我對這篇作品的感受和理解。
一、撲朔迷離的故事情節
《太平》主要借助“我”與自己的上司小白通過網絡聊天的方式,交代了自己失蹤4天的經歷。故事由父親周成舟讓“我”去太平鎮查詢于勒的死因開始,牽扯出于勒與張映紅、張映紅與父親、“五四青年”與張小琴、六姑與師范校長的愛情故事。在和小白交流和講述的過程中,也夾雜著述說父親和母親的愛情,而“我”和小白的愛情也浮現出來。據說,小說原名叫《圣安德里亞斷層》。圣安德里亞斷層是北美板塊和太平洋板塊之間的斷裂線。其中北美板塊向西南運動,而太平洋板塊向西北運動。這個斷層很特別,它大部分是隱蔽的,只在某些地方留下了明顯的斷裂痕跡。作者正是用這樣的斷層來表示小說中人物的愛情關系。小說中還幾次提到馮內古特,他是德裔美國人,1945年向英裔美國人克可斯小姐求婚時遭到強烈反對,馮內古特說過德裔美國人和英裔美國人之間一直存在著一條圣安德里亞斷層。范瑋這個小說中所敘述的愛情,正像馮內古特的愛情遭遇一樣,都隔著一條這樣的斷層。這個斷層是愛的阻隔,愛的斷裂,所以終究不會有完美的結局。就像小說中的父親和母親并不相愛,因為“我”的存在勉強廝守在一起,上了歲數之后還是選擇了分手;父親深愛張映紅,而張映紅對父親沒有感覺,卻因為翻譯于勒發給別的女人的求愛電文而莫名其妙地愛上了于勒;于勒博愛卻不專注,他喜歡風騷的女人,對張映紅并不癡情,張映紅由原來的孤傲變得放浪,他們的感情結局竟被簡單定性為嫖客因嫖資殺人且自殺;六姑愛上不該愛的自己的老師——一個師范校長,一生都不愿跟男人打交道,而她心中的校長卻不一定知曉;“五四青年”和戀人張小琴分離時,恪守諾言,不停地尋找,傻傻地堅持卻仍無結果;“我”和小白的愛情,誰也說不清楚最后會是什么結局。
《小說選刊》的編輯付秀瑩認為:范瑋的小說是追求并深度契合米蘭·昆德拉關于小說復雜精神闡釋的優秀之作。從范瑋的這個小說中我們可以深切體會出來。小說主人公在父親的安排下去太平查詢十五年前于勒的死因,但是在追問過程中,卻越來越趨向模糊和復雜。看似在尋找真相,結果卻向著反方向靠近,越來越模糊,讓人難以琢磨。比如張映紅這個人物,“我”是在眾多人的口中漸漸了解了張映紅這個人物的。從當年參與辦案的老韓口里我們知道,張映紅的案件被定性為因于勒拒付嫖資而殺人并且自殺,但是在老韓看來又不是這么簡單;在偶然經過卻目睹了殺人過程的賭徒看來,張映紅是個喪心病狂的女人,為了某個爭議乃至意見不合而殺人;在紅星旅社的胖老頭眼里,張映紅這樣一個好女人竟然會把狂放灑脫的于勒殺死了,很不可思議;在六姑的心里,張映紅是一個癡情而執迷不悟的女子,為了愛情敢于犧牲;而“五四青年”則認為張映紅是于勒和周成舟交情的附屬品,小白又談到張映紅應該是為了愛的尊嚴。每個人口中的張映紅都不盡相同,這也就造成了敘事的模糊性和多義性。她或許是為了“愛的尊嚴”,或許是因為其他的爭議而殺人,我們無法說清楚。還有“五四青年”這個人,雖然說起張小琴的事他顯得不正常,而且別人都說他是傻子,但是我們從他的行為中又看出清醒的一面,比如他對六姑人生經歷的敘述和對于勒性格的了解。
所以從作品描述中,我們可以感知作者對小說復雜性的實踐。范瑋小說的創作源于他對生活的獨特感悟,小說的復雜性也是對應著生活的復雜性。作者試圖通過這個小說告訴我們,生活本身是復雜的,每個人透過自己的眼睛只能看到生活的一面或幾面。真相只是相對而言的,現實存在著多種可能。
二、獨特而夢幻的敘事方式
范瑋說過他偏愛異質的小說。他認為這樣的小說能夠給讀者帶來全新的體驗、感悟和樂趣,把讀者由現實世界的“此岸”擺渡到可能世界的“彼岸”,給讀者提供豐富而神秘的心靈活動。他反對我們日常所見的小說,認為那些小說所顯示不過是人所共知的顯而易見的體驗,沒有揭示表象背后的本質意義,屬于淺層次的小說。那樣的小說,除了具體故事有些差異,其他沒有改變,讓人讀了不能產生共鳴,也不能引發思考。所以范瑋的創作不僅在內容上做了新的嘗試,在敘事方式上也借鑒了現代性的手法,做出大膽嘗試。
首先,作者貼近現實,通過網絡聊天和談話方式來展開故事情節,揭示人物關系和命運。聊天是現代傳媒給人們帶來的新的生活交往方式,因方便快捷而風靡世界。這樣的敘述會讓讀者產生親切感,似乎讀者就是站在他們身旁的聽眾,聽他們在講故事,使作品獲得了一種真實的現場感,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作品主要是以“我”和小白的聊天進行的,隨意流動的思緒、質樸流暢的語言,擺脫了傳統小說的束縛,使小說結構具有流動性和張力。作者在作品中寫道:“火車是有特殊意義的東西,它有著封閉的空間,但它又是流動和開放的。據說很多作家習慣在咖啡廳寫作,為什么沒有人建議他們來火車上寫作呢,這樣他們的作品起碼不會缺乏起伏感和方向感,但他們大概不知道,有多少讀者討厭那種平鋪直敘和漫無目的的作品。”我想作者借小說的主人公說出了自己對小說創作的獨到理解和詮釋。他喜歡開放性的寫作,世界是復雜的、多元的,小說創作也應該突破慣性思維,擺脫模式化的束縛。讀其作品,一開始會覺得很亂,很難理解,慢慢地會覺得越讀越有味,這就是小說寫作的成功之處。盡管有些地方有一些瑕疵,但是范瑋畢竟做了獨特的嘗試,為小說創作會提供很好的經驗。
其次,復調小說的嘗試。復調小說理論是巴赫金提出來的,用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詩學特征。復調理論的核心特征也就是不同聲音和意識間的對話。“對話”是復調小說的理論基礎,通過對話,復調小說才具有了情節的豐富性和人物的復雜性。當代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在他的小說創作中運用并發展了巴赫金的復調理論。范瑋借鑒了米蘭·昆德拉有關小說的創作理論,并在創作時也在做著這方面的嘗試。比如說《孟村的比賽》,就出現了“我”和竇大爺兩個敘述者,他們共同完成了小說的敘述。在《太平》中,也運用了各種敘述聲音,警察、胖老頭、六姑,還有“五四青年”,他們分別講述于勒和張映紅的人物性格和是非關系。多角度敘述,張映紅和于勒這兩個人物形象得到立體呈現。小說中眾多的他人敘述、他人意識的交相進行,構筑了“多聲部”的敘事結構,較好地襯托出人物個性和內心世界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再次是小說給人一種夢幻感覺。作者用自己大膽的想象給營造了一個個的夢境。他偏愛借助夢境展開自由想象來虛構小說,或者直接發揮自由想象來虛構小說,以達到以虛寫實,還原真實世界的目的。在他之前的創作中我們就會有這樣的感受。比如說《孟村的比賽》,作者虛構了一個像夢一樣的村子——孟村。小說的開頭就寫了我在夢中去公社趕集,夢見了熱騰騰的包子蒸屜和態度不好的女服務員,還夢見父親讓我吃包子等。然后寫了這個村子有比賽的傳統,比賽吃辣椒、比賽吸煙、比賽冬天抗凍、比賽放屁、比賽養雞等等,重點寫了因為比賽養豬發生的一系列故事。給人印象深刻的是編織人模樣竹筐的竇大爺,他是神一般的存在,可以用編織各種模樣的筐暗示和保守著所有的秘密。還有父親陷入和孟二起與麥小小的感情糾葛,為了贏得比賽,父親養了一只外國豬杜洛克,因為杜洛克讓父親喪失了自尊,導致父親氣憤地殺豬。杜洛克死后,父親一切不正常的反應,都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小說敘述起來,就像是一場夢境一樣,而這樣的夢卻是現實基礎上編織出來的,作品表現了作者對生活的理解。還有小說《刺青》,烏山就像是一個世外村莊一樣,每個人身上都有刺青。他們認為“刺青是烏山人的護身符,身上有刺青,出門在外不受欺負”。小說中蘇醫生為人們講述了一個夢幻般的人物烏山英雄雷大鼓,雖然大家都沒有見過,但是雷大鼓的形象卻深入人心,以至于蘇醫生的女兒被父親的講述迷惑嫁給了雷大鼓。讓她沒想到人們心中敬仰的雷大鼓竟是一個膽小如鼠的人,打破了蘇小耳心中的迷夢。而主人公蔡小筐一出場就亦真亦幻,他也是把雷大鼓當作大英雄,他刺殺黑道大漢的時候自稱雷大鼓,但是他至死也不知道雷大鼓到底是誰。不但這些人充滿奇幻色彩,就連咖啡館的女仆也有特殊的功能:鼻子異常靈敏,能嗅出各種氣味、物品和客人的職業。所以《刺青》這部作品就像作者創造出來的夢境。作者似乎想告訴我們生活中充滿虛幻和神秘,每個人都做過類似的夢,它是由現實的感受接續而來,表現了世界的神秘性和人生的荒誕性。
小說《太平》也是夢一般的存在。小說開始就說“我”多次想去太平,而且還做過夢,夢里全是在太平街上閑逛的情景。去太平的路上遇到的刑警副隊長李大成,似乎是命中出現的人物來成全“我”的太平之行。還有之后遇到的似傻非傻的“五四青年”,他是一個奇特的存在,他就像幽靈一樣總是在“我”需要的時候出現,告訴“我”關于太平的一些人的故事,卻對自己的愛情故事含糊不清,一直在和不知道存不存在女友捉迷藏。還有紅星旅社的胖老頭、參與案子的警察老韓、六姑等人物都像是一個個從夢里浮現出來的一樣,亦真亦假,神奇地出現,又神秘地消失。小說最后寫道:“我的小說是這樣結尾的,這是我從‘鵲橋’酒吧回去后做的一個夢。”我們讀完小說,總有一種理不清人物的感覺,似乎每個人物都很難說清楚。讀到最后才恍惚覺得,作者似乎在敘述一個夢,這個夢連接著眾多的人物故事出場。我們每個人做夢后醒來都會有這樣的疑惑:總也想不起夢中的那個人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只能記得片段的場景。作者就是在造夢,而且是令人回味的有意思的夢。范瑋說:“夢幻,是現實的一種可能。”他寫小說加入特別多的夢境元素,他認為這樣寫才比較順手。范瑋為現實和夢想之間搭建了一個橋梁,它們是相通的。人的一生就是像夢一樣的活著,從現實中幻想,從幻想中回到現實。范瑋為我們提供了一場夢幻之旅。
這篇小說讀了很多遍,覺得有些東西總也說不清,這也許就是作者創造復雜的小說世界所追求的效果。這是作品耐品味的原因,也是作品的魅力所在。范瑋的作品語言質樸自然,形象逼真,都是個人人生經歷和內心世界的最真摯的情感表達。他那豐富的想象力和獨特的藝術表現手法會讓他越走越遠。
范瑋借鑒和追求現代性小說敘述手法,無疑給他的作品增色不少,卻也存在不足。比如在小說的復雜性和夢幻色彩上,作者刻意追求,用力過猛,就會造成讀者理解障礙,難以產生共鳴。像《刺青》中的雷大鼓形象,蘇醫生敘述中的影像和真實的雷大鼓之間巨大差距,讓人捉摸不透作者的用意。《太平》中的人物也是,“我”和小白的關系最讓人搞不清楚。有些事自然搞不清楚,搞不清楚也是一種美,但刻意追求或者過分的撲朔迷離,就會形成閱讀障礙。事實上,作者沉迷于夢境,借助夢境敘述,亦真亦假,虛實難辨,已經形成閱讀障礙,導致讀者市場狹小。所以作者過多的借鑒西方現代手法,忽視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節的連貫性等傳統敘事方法,忽視讀者的閱讀接受能力和接受心理,不一定是小說發展的坦途。因為小說畢竟是寫給人看的,特別是在這個審美消費時代,更要尋找創新探索與審美“悅讀”的契合點。創新的要義在于加強藝術表現力和審美魅力,而不是徒增閱讀障礙,不是炫示技藝。
本欄責編 孟 騁
郵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