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民《吾友陳應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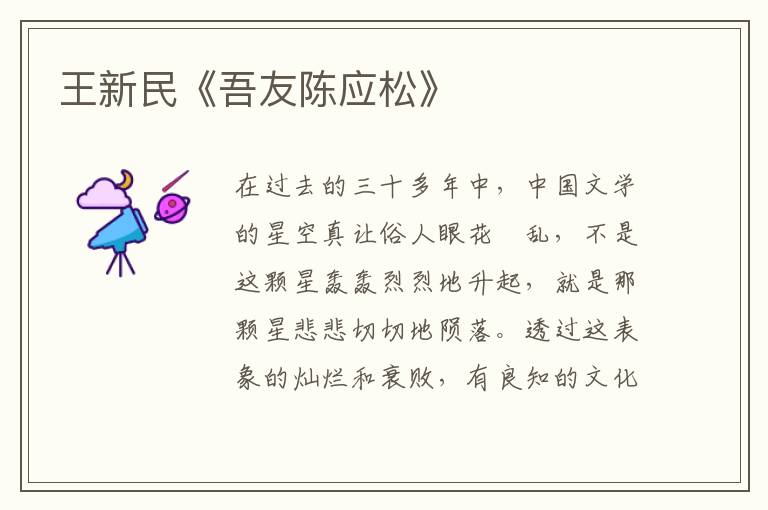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國文學的星空真讓俗人眼花瞭亂,不是這顆星轟轟烈烈地升起,就是那顆星悲悲切切地隕落。透過這表象的燦爛和衰敗,有良知的文化人一定會捫心自問,這到底是為什么?其實,這道理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國上世紀后二十年的文學,大多都是思想解放的武器,成了“革命衛生學”的工具,本世紀這幾年的文學,大多卻在玩庸俗,玩青春,玩泛愛,玩性,玩“小資”,玩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文學變成了玩具,變成了“不革命不衛生”的桑拿場所。
而這么多年來,陳應松在喧囂與騷動中一直保持著心靈的指向,在欲望橫流中一直堅守“人學”原則,在他發表、出版的數百萬字的作品中,無論是詩歌、小說、散文、隨筆或文學評論,他都堅守將文學通盤人性化、生命化、生態化,賦予了文學血肉之軀,然后又以生命的感覺關懷著“人學”。在他的筆下,文學生命與歷史文化互相感染著、兼容著,原創性的文化思考方法和話語表達方式,“人化的自然”和“詩化的世界”,總是自覺深入地走進我們民族的文化本原。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曾經震撼文壇并且還將繼續感動和影響文壇的“神農架系列”小說,從文學性的意義上,真正地開創了自然與生命的對話:詩性與哲理的融合。在這一系列小說中,他用獨特奇妙的審美視角,精彩絕艷的詩化敘述,普通平凡的人物故事,將生命與自然的關系揭示得如此鮮活生動、血肉相連,讓人讀后靈魂久久不得安寧。他的榮獲“魯迅文學獎”的《松鴉為什么鳴叫》,描繪了生命與自然,人與死亡之間的關系,整個故事籠罩著浪漫和奇妙的色彩,就像小說中掛榜巖上幾千年以來無人可解的天書,作品寫得虛幻而現實,張揚而節制,讀后自然會迫使我們重新審視自我,審視我們身邊和生活中的各類生態環境。
早在上世紀末,我曾多次與武大教授樊星、湖大教授李國俊談到陳應松的作品,二位評論家對他的作品也一直看好,并說他將來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家。別看現在文壇對他冷落,但總有一天文壇會回歸文學,這獎那獎一定會向他走來。話音還在耳際回響,“魯迅文學獎”向他走來了,“中國小說學會大獎”向他走來了,“人民文學獎”向他走來了。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小說連續5年進入“中國小說排行榜”。
我與陳應松相識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那個時代,是現代中國文學的黃金時期,是一個優美的、永遠值得我們懷念的文學時代。那時他寫詩,我也寫詩,我們的作品經常出現在全國各地的同一家刊物上。由于為文做人觀念較為接近,我們很快成了摯友。他每出版一本書,都是要送給我“賜教”的。記得幾年前有一次我去他家中聊天,突然在他的書柜中發現了他于199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別讓我感動》,我向他索要,他當時不相信這本書沒送我,于是在書的扉頁上這樣寫道:“竟說此書未送你,那不是要打老弟的板子?書雖不好,第一贈送請求賜教的當老兄第一人也,所以,補送謝罪!”由此可見,他是多么珍視我們之間的兄弟情誼。在作家圈里,他送我的書最多最全,在寫這篇文章時,我清點了一下,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隨筆集、詩集不下二十部。
陳應松才華橫溢,滿腹經綸。寫詩時,他是詩壇的一員猛將;改寫小說后,他又成了小說界的一位傳奇人物。他的散文、隨筆,他的文學評論,他的書法繪畫,都是獨樹一幟的,都是值得各個方面的專家認真研究的。他才思敏捷,提筆成章,在文壇上是個著名的快槍手。后來他越寫越精,不再以快著稱,這幾年,幾乎篇篇轟動文壇,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
在人們心目中,陳應松頗像一位隱居深山的“隱士”,他從不趕什么熱鬧,更不喜歡張揚。在這個浮躁的時代,能像他這樣耐得住寂寞,并且沉下去苦心經營自己作品的作家并不是很多。當然,生活中的陳應松并不是總是那么“嚴肅”的,頗具幽默感。記得在1998年“三樓”(黃鶴樓、岳陽樓、騰王閣)筆會期間,我們一行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作家三省游玩,陳應松一路以令人笑破肚皮的“趕五句”活躍著氣氛,那幽默的脫口秀精彩極了。陳應松是性情中人,他的作品中總是溢出一種生命中不可言說之痛的陳應松,他臉上常常掛著幾分高貴和憂郁。他是我們的文學的榜樣,生活的摯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