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月斌《盧一萍小說簡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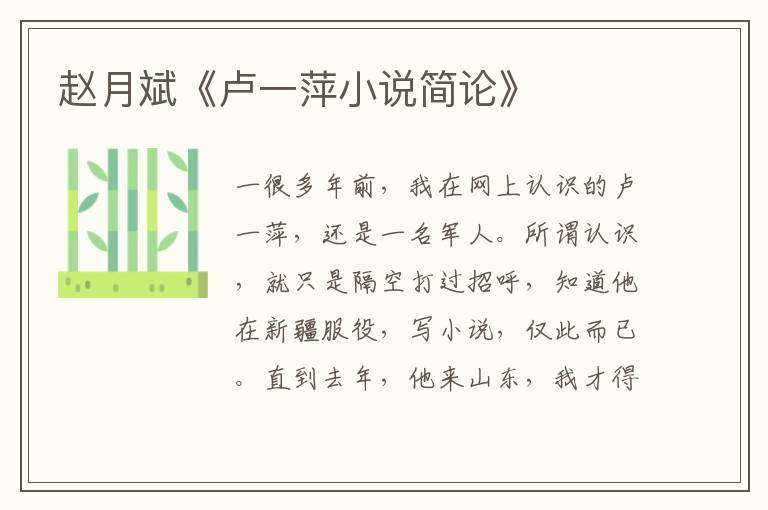
一
很多年前,我在網上認識的盧一萍,還是一名軍人。所謂認識,就只是隔空打過招呼,知道他在新疆服役,寫小說,僅此而已。直到去年,他來山東,我才得見其真身,并有幸駕車,載他從泰山北麓穿過。一路上走走停停,他一邊贊嘆泰山的美景,一邊講他年少時的文學因緣,以及后來的從軍、寫作經歷。我比盧一萍虛長半歲,然而他看上去更像踏實可靠的兄長。他長得老相,顯然跟二十多年的高原生活有關。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肚腹不光是比我大,里面裝的故事也一定比我多。這樣的人即便不寫什么,本身也夠精彩。更精彩的是,他寫了,他寫下了他的“小世界”,寫出了自己的高原。
盧一萍當兵二十七年。1990年春荒時節,十七歲的盧一萍穿上軍裝,從大巴山區走向了西北邊塞。1996年他從軍校畢業,又主動要求回到南疆,從北京“放逐”到帕米爾高原一個邊防團當排長。2000年,他調到新疆軍區文藝創作室當創作員。前后在新疆待了二十多年。直到2012年底,才調到成都軍區工作。所以盧一萍自認為擁有“兩個故鄉”,一是生身之地,一是成人之地。與此相應,他的創作資源、創作對象、創作成果也和這兩個故鄉密不可分。所以,若要簡單概括盧一萍的小說,大致可以說他總體寫了兩個地方:一個是安身立命的邊疆荒原,一個是遠而未疏的蜀地老家。前者主要包括南部新疆和藏北高原,“也就是盧一萍自己在《天堂灣》代后記中所說的,“從塔克拉瑪干沙漠到帕米爾高原、喀喇昆侖山脈和阿里高原之間沙漠、綠洲和冰峰雪嶺之間那塊荒蕪之地。”后者便是位于四川盆地東北部的大巴山區。雪山高原和老家樂壩構成了盧一萍敘事的兩極,它們互為映照,相為始終,雖然相隔萬里,卻連著一根無形的引線。
盧一萍的寫作一向具有鮮明的地域性,這種地域特征好像天然具備了一種遼闊格局,讓他的作品流蕩出蒼涼高曠的氣息。讀他的小說,總可看到遙相呼應的故鄉和遠方。他像一位曠野獨行的采風詩人,把所有的遠方全都寫成了故鄉,又把故鄉寫成了無盡的遠方。你能感受到他和沉默的大地一樣堅忍篤定,又可感受到他的內心如天空一般通透澄明。顯然,盧一萍身上攜帶著濃重的高原氣質,同時還帶有邊關浪子的嫌疑,他的文字里有陽剛、雄渾和質樸,也有苦寒、孤獨和悲傷。所以,一方面,他是忠于生活的寫實主義者;另一方面,又是擅長白日做夢的幻象制造者。他的作品里有巍巍群山,也有悠悠白云。有纖毫畢現的小工筆,也有荒誕不經的大寫意。就是在虛虛實實的光影里,盧一萍找到了一條玄妙的通道,由此,“正切合了生活環境的轉換。從高原到低地,也隱含了某種象征的意味。”
二
讀盧一萍的小說,會有一種道阻且長的距離感,讓你感覺他寫的遠方才是真正的遠方。在他的作品中,隨處可見喀什噶爾、塔什庫爾干、克克吐魯克、塔合曼草原、慕士塔格雪山、薩雷闊勒嶺、紅其拉甫河、葉爾羌城等帶有異域色彩的地名,還有娜依、德吉梅朵、古蘭丹姆、巴娜瑪柯、夏巴孜、沙吾提、阿拉木、巴亞克、阿加熱等帶有異族色彩的人名和他們的冬牧場、夏牧場。那遠方的人和事被盧一萍記錄、捕捉、沉淀,并重新建構、呈現,我們才聽到了塔吉克民族的愛情古歌,看到了在“世界屋脊鋼鐵哨卡”天堂灣的旱廁里猝死的新任副連長楊烈和同樣死在天堂灣卻變成了天使的“黑白猴子”,更記住了從樂壩來到白山的凌五斗和他身上的種種奇跡。
盧一萍有一本小說集《天堂灣》,收入了《天堂灣》《一對登上世界屋脊的豬》和《樂壩村殺人案》三部中篇小說,總共十來萬字,這在他眾多作品中只是很小一部分,卻足以窺一斑而見全豹。通過這本書,大可了解他的總體面貌。僅就題目看,“天堂灣——世界屋脊——樂壩”,就有著明顯的地理標識作用。實際上,盧一萍的小說,主要就是寫“天堂灣”和“樂壩”這兩個地方(《一對登上世界屋脊的獵》的發生地也是海拔5400米的天堂灣)。如其所言,他的寫作對象,是那些已被流沙湮沒的故國、曾經在荒原上開墾綠洲的拓荒者、生活在高原上的游牧民、駐守在極邊之地的士兵,以及故鄉的人、故鄉的故事。盧一萍的寫作,往往帶有“親歷”的性質。這種親歷或許并非作為當事人身處其中,卻一定要親臨故事的發生地,對所寫的地方有所見,有所聞,有所體驗。盧一萍在帕米爾高原當過排長,在紅其拉甫的前哨班帶過哨(相當于哨長),采訪過喜馬拉雅山脈下的達巴邊防連,到過喀喇昆侖山口海拔5380米的邊防哨所,而小說里的“白山”“天堂灣”,則化成了一種概括性的想象。《天堂灣》就是一個聽來的故事——一名軍官到連隊報到時因高原缺氧猝死在廁所里的“事跡”——在講述者三言兩語講完之后,盧一萍并未簡單地記在采訪本上了事,而是來到那個無名死者簡陋的墳塋前,“能感覺到他的青春氣息依然能從冰冷的泥土下散發出來。”后來,在達巴邊防連,盧一萍又認識了一位姓馬的連長——“覺得他就是那位活著的死者”。這樣,那位無名的死者找到了原型,《天堂灣》得以完成。小說是以多位當事人、調查者口述的形式展開的,甚至死者楊烈,最后也以亡靈的形式出場,不得不面對自己的結局,親眼目睹自己的葬禮。情節當然出于虛構,但是“天堂灣”的冰岔口無疑是真實的,那里的月光是真實的,死亡是真實的,作家流下的淚水也是真實的。
再比如“樂壩”這個地方,確是盧一萍的老家,但是小說中的樂壩,也是出于“想象”。盧一萍曾說過:“……位于大巴山區的故鄉。這里感覺要狹窄一些,但想象的空間異常廣闊。它與我在新疆建立的文學地域從情感上是一體的。二者的共性是:都被遺忘,都不被世人了解,都是偏僻荒遠之地,歷來都是苦難之域。但它們在我心中,都能飛升起來,在天空中重新結合為一體,成為同一個故鄉,同一個王國,成為我心中的神山圣域。”依靠“想象”,盧一萍把老家的“鄉野之談”孕育成了小說,把實有的樂壩變成虛構的樂壩。天堂灣和樂壩只是兩個微不足道的小地方,卻為盧一萍提供了無窮的想象,成為獨屬于他的文學地域。盧一萍迷戀“故鄉”,以小說集《天堂灣》《父親的荒原》《銀繩上的雪》和長篇小說《白山》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皆帶有“從高原到低地”的地域特征,甚至可稱為“地域文學”。他把老家和客居之地反復書寫成了“同一個故鄉”,并且用文字與其建立了一種“可靠的聯系”——一種“生死相依的關系”。他小說里的“故鄉”因此不再是一個干巴巴的地名,而是一個豐富、生動且無限敞開的藝術空間。
盧一萍對特定地域的反復書寫很容易讓人想到所謂“戀地情結”——這一概念又譯作“場所愛好”,最早由法國哲學家加斯東·巴拉什在他的《空間的詩學》中提出,后由美籍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運用到地理經驗中,用以闡述人對地方的依戀,探究人與環境之間的情感關系。人皆有故鄉,都有自己熟悉的地方,甚至都會傾向于認為自己的家鄉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段義孚,提出“對故鄉的依戀是人類的一種共同情感。”故鄉有其特殊或值得記憶的性質,比如對地理景觀和地標的記憶,對聲音和味道的記憶,對隨時間積累起來的公共活動和家庭歡樂的記憶,都可能讓人產生揮之不去的依戀之情。俗語說:“窮家難舍,熱土難離。”故鄉是家的所在,是慣熟之地,是安頓肉身、停歇靈魂的地方,它承載了最為親切、穩定的生活經驗,與我們的血肉之軀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然而,就像段義孚說的那樣,中國有“安其居、樂其俗”,“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美國也有連續六代人從生至死一直生活在伊利諾伊州的哈默斯家族。盡管這些人具有強烈的戀地情結,但是“人們深深眷戀的地方都不一定是可見的”,這樣的地方只是一個封閉、靜止的私人空間,它只對特定的個人和群體有其意義,相對與之無關的其他人而言,你的故鄉只是你的故鄉,它和我毫不相干,甚至可以等同于不存在。所以,如何“讓一個地方成為可見的地方”?如何“使人類的地方變得鮮明真實”?身為地理學家的段義孚十分看重文學藝術的創造性作用,認為它能夠表現親切經驗(地方經驗),描述不夠引人注目的人文關懷領域,從而“引起對那些我們原本可能沒有注意到的經驗領域的關注”。盧一萍的創作實踐即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假如他不曾寫過《父親的荒原》《最高處的雪原》《夏巴孜歸來》《克克吐魯克》《白山》,不曾寫過“這些遍布于昆侖和阿里積雪覆蓋的群山、颶風橫掃的荒原、奔騰洶涌的河流、險惡卓絕的山谷和高聳云天的大坂妖魔鬼怪”,不曾寫過“由于天空中積滿了漠風揚起的沙塵,荒原的邊緣與天空的邊際一片混沌,天空和荒原是一色的,天空好像不是空的,而是懸著的另一個荒原”,不曾寫過“他的聲音撞到對河觀音巖植物繁茂的巖壁上,又彈回來,被村后山神廟周圍的林莽吸納,正要吞咽,覺得不行,味道不祥,又‘噗’再吐出,余音在樂壩村上空回蕩了好久”,我們又怎么可能知道白山、天堂灣、樂壩,又怎么可能看到在虛構中復活的無名者,怎么去尋找這個世界存在的理由?
盧一萍曾多次引述波斯詩人薩迪的話:一個人應該活到九十歲,用三十年獲取知識,再用三十年漫游天下,最后三十年從事創作。他似乎就是為小說而活的,只因不滿足于用文字虛構一種生活,便把生活過成了小說。他“戀地”,卻不是偏安一隅,而是盡可能地擴張自己的活動半徑,盡可能地進入凡塵世俗,潛入泥土之中。有人是為寫作“體驗生活”,他則是為寫作投入生活。當他發愿要為高原寫書時,就全身心做出了“準備”。在帕米爾高原這個“世界的扣結”上,盧一萍學會了騎馬、騎牦牛,認識了很多塔吉克鄉親,在氈房里和他們一起喝酒、吃肉、啃囔,那里的簡單和質樸,那種超驗主義的生活方式,讓他心甘情愿變成了一個土生土長的當地人。同時,他還幾乎跑遍了高原的每一個皺褶,并且利用各種機會走遍了新疆、藏北、川北和云南。這樣的漫游無疑有助于增強一個作家的地方經驗和現實感,它讓盧一萍置身于真切的寫作背景中,也讓他找到了理解這個世界的基點,從而將有限的地域化作了創造性的敘事空間。
盧一萍把帕米爾高原視作一個獨特的“新故鄉”,又說自己從事的是“牧人式的寫作”。其實這正透露了他作為外來者、漂泊者的身份。他當兵將近三十年,除了在高原上四處漫游,還有幾年到北京、上海的學習經歷,即便現在回成都定居,嚴格說也算不上回鄉——不過是離故鄉近了而已。況且,如移民美國的華裔作家哈金在《在他鄉寫作》中所說:“一個人不可能以同樣的個人回到同樣的地方。”哪怕他真的回到老家,恐怕也還是歸來的陌生人。因此,盧一萍終究是“一葉飄萍”,無論他身在何處,都是人在他鄉,是一個自我放逐的異鄉人。然而,對一個以寫作為信仰的人來說,這種狀態反倒給了他創造的自由,讓他在作品中建立了自己的“神山圣域”。段義孚在他的《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中提出》,我們的生活世界即由地方 (place)和空間(space)構成。“地方意味著安全,空間意味著自由。”地方是穩定的、封閉的,空間則是動態的、敞開的。“人類既需要空間,也需要地方。人類的生活是在安穩與冒險之間和依戀與自由之間的辯證運動。在開放的空間中,人們能夠強烈地意識到地方。在一個容身之地的獨處中,遠處空間的廣闊性能夠帶來一種縈繞心頭的存在感。”就此而言,盧一萍從未畫地為牢,他不斷地外出、漫游、求學、歸來,即可見一種空間意識,他未局限于寫寫地域化的風土人情,或是以獵奇的方式寫寫異域傳奇,而是通過開放性的書寫,讓這個神秘的地方視通萬里八面來風,擁有無限的空間感,也為他的言說提供了更多可能。正所謂“此心安處是吾鄉”,他在小說里安心,在語言中安家。就像哈金所說:這樣的“家鄉不再是只存在于一個人的過去,而是與現在和將來也有關的地方”。盧一萍如同不倦的游牧者,那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們,才關乎他的去向,那渺不可知的大荒之境,才是他的故鄉。
三
盧一萍,一個在別處寫作、為別處寫作的漢人。他在高寒的邊防哨所寫遙遠的故鄉,在喧囂的都市寫空寂的荒原。所以他總是身處世外,寫下的往往不是華屋廣廈,不是潮女型男,不是快節奏高效率的“當下”,甚至不是我們喜聞樂見的“現實生活”,且不說那種極為特殊的自然環境,即便是與時代同步的個人經驗,也似乎總是遲慢的、滯后的,甚至是逆時的。因此,盧一萍的小說不僅在空間上跟“現實”拉開了距離,而且在敘事時間上也幾乎不與“現在”合拍,他所講述的常常是一種“過去時”——是比他本人要“老”許多的陳年舊事。比如《白山》,主人公凌五斗的空間移動軌跡(樂壩——白山)和作者基本吻合,但是從年齡上看,凌五頭要年長二十多歲,算是盧一萍的父輩。他有一部小說集就叫《父親的荒原》,更是直接表明他講述的是上代人的故事。盧一萍很少把同代人作為敘事對象,他在小說里變成了背負更多滄桑的“父親”。如此,他的小說約略顯出一種“過時”的味道,那些無甚新意的人和事,反倒因為“過時”而珍貴、稀罕起來。
盧一萍算不上技術派,他的小說大都寫得平直,除了《天堂灣》《樂壩村殺人事件》等少數作品采用了多重敘述的方式,《我的絕代佳人》算是實驗文本,多數作品都像他本人一樣中規中矩,不溫不火,甚至可能顯得有點笨拙。像小說集《銀繩般的雪》《父親的荒原》收入的作品,基本是老老實實的寫人記事,沒有花哨的形式,也沒有曲折的情節,就是高原牧場的塔吉克族、藏族牧民以及邊關哨所的日常瑣事。但是這些小說往往在平直笨拙的敘事中包蘊著出其不意的內核,與我們司空見慣的主流世界相比,又像是不在同一維度,所以他寫的平常人物、普通事件,看上去反而很不尋常,很有些耐人咀嚼的怪味。
短篇小說《北京吉普》就寫了一個青年牧民,用馬鞭把縣長的吉普車打成了“癩皮狗”,原因只是縣長的兒子開的吉普車讓他喜歡的姑娘暈車了。這個破壞公物的青年為此坐了三年牢。令人匪夷所思的不是坐牢的人收獲了愛情,而是他出獄后竟然開上了北京吉普——縣長的兒子竟然也把自己的情敵當作英雄,讓他當上了縣政府的駕駛員。《最高處的雪原》寫的是負責飼養戰馬的戰士阿廷芳,為了找到失蹤的軍馬,在暴風雪中搜尋了四天,最后終于找到幸存的六匹馬,自己卻凍死在零下四十度的嚴寒中。《白馬駒》講的是一個塔吉克小伙子的愛情故事。因為心愛的姑娘巴娜瑪柯喜歡他家的白馬駒,他便想著假如自家的母馬再生一匹白馬駒,就把它送給巴娜瑪柯。當母馬懷上小馬時,他能跑了幾百里前去報信。但是沒想到,未等小馬生下來,他父親竟把母馬賣給了別人。上面三個故事大體可見盧一萍小說的平淡無奇,其實都沒有什么啊,他寫的很多人物都是笨人、實在人,身上有一股子傻乎乎的倔勁。你看,假如沒有這樣的倔勁,阿廷芳就不會連夜出去找馬,不會到大風雪中送死。假如沒有這樣的倔勁,小伙子怎么會跑那么遠的路帶去一句話?同樣,像《夏巴孜歸來》中的夏巴孜傻瓜,《等待馬蹄聲響起》中那一對眷戀草原故地的老人,《最迷人的吆喝者》中的賣烤肉串的熱合曼,《逃跑》中拼命參軍又拼命逃跑的柳嵐,《快槍手黑胡子》中的霸道而又厚道的光棍營長王得勝,特別是《白山》中不會說謊的凌五斗,這些人物大概都有一顆花崗巖的腦袋,不夠精明,不會變通,不知相機而動,只知以不變應萬變,他們像傻瓜一樣引人哂笑,更像傻瓜一樣觸動人心。
盧一萍就是這樣寫了許多非主流的怪人,作品的主旨卻再樸素不過了,無非是傳達德行良知,表現最基本的真善美罷了。正是在阿廷芳、夏巴孜、熱合曼、凌五斗這些“傻瓜”身上,能夠看到勇敢、誠實、忠貞、善良和真情尚未泯滅。他們像是時代的飛地里長出的樗材,即便一無可用,也有其不可復制的“孤僻動作”,而為某些闊人精英所缺少的,恰是那種無利可圖的“無用之用”。從這一點來看,盧一萍就像一個優雅的保守主義者,他喜歡回頭,迷戀過去,在小說里收藏了太多時間的皺紋。他曾在小說集《銀繩般的雪》的自序中說過:“小說是時間的產物。”“我現在寫出的文字,更多是我菲薄的時間的沉淀物,是對‘過去’的懷念。這些東西可能沒有多少價值。但是對我自己而言,我至少可以沿著這些文字,尋找時間的陳香,歲月的痕跡,尋找到那個微塵般的‘我’的一絲蹤跡。”他自稱寫下的可能沒有多少價值,又宣稱“寫作是我小小的信仰”。足可見這一粒微塵并非沒有自我,并非沒有方向,它就是那個隱現在作品中的“我”——盧一萍謙卑而篤定,他小小的信仰中自有其不可估量的價值,所以在他筆下,哪怕是一粒微塵,也可能蘊藏著神奇的力量。
他熱愛過時的東西,還有點兒保守,這樣的評價難免會讓人誤以為盧一萍是一個因循守舊、冥頑不靈的家伙。不過只要大致了解他的作品,就會發現他在骨子里絕不缺少一個現代知識分子所應有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寫作非但一點兒也不迂腐落伍,反而不乏勇猛無畏的先鋒之氣。從他年輕時寫的長篇小說《激情王國》,后來的《我的絕代佳人》,到近期出版的《白山》,始終貫穿著一種放縱想象、打破常規的野心。他的“保守”不過是以守為攻,他的“過時”不過是以退為進。他是過時的,又是超前的。他的作品里有塵土也有光明,有火也有冰。他一邊捍衛美好傳統,一邊奮不顧身地闖關破圍。所以,這個寫小說的漢人,既是古典的保守主義者,又是現代意義的先鋒小說家。這種狀態很像法國學者安托瓦納·貢巴尼翁所說的“反現代派”——如同波德萊爾、福樓拜、羅蘭·巴特那樣,他們“比現代派、比歷史的先鋒派還現代派: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超現代派,他們似乎與我們是同時代的,離我們很近,因為他們已經看破了一切。”“反現代派首先是那些身在現代的潮流之中又厭惡這種潮流的作家。”雖然諸如“現代派”“反現代派”只是舶來的概念,卻能為我們提供一些參照。盧一萍固然不是一個抱殘守缺的守舊派,但是也不是一個赤膊上陣的激進派。比起開風氣之先的先鋒派大佬,他像是遲到的小弟。比起曾經大出風頭的70后同儕,他好像一出道就已經老了。與現實主義相比,他有點兒超現實。與凌空高蹈的炫技派相比,他又太過于老實巴交。他好似天生反骨,卻絕非搗亂分子、破壞分子,而是溫和的抒情詩人、積極的悲觀主義者。正如貢巴尼翁所稱:“反現代派——不是傳統主義者,而是真正的現代派——只不過是現代派,真的現代派,沒有受騙的、更為聰明的現代派。”“反現代派,就是追求自由的現代派。”盧一萍未必現代,也可以是反現代的現代派;未必先鋒,卻可以是反先鋒的先鋒派。所以,我們才會看到,在《天堂灣》《白山》等作品中,盧一萍的既有實打實的笨功夫,也有天馬行空的神來之筆。就像他創造的奇特人物凌五斗一樣,一旦進入白山海拔4750米的高度,就會身具異稟,能夠說出常人所不能說的話,做出常人所不能做的事。盧一萍也在作品中獲得了自由言說的特異功能:他制造了一種由低地到高原的審美“落差”,同時也發現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時差”,他的小說便是在這樣的錯落反差中,具備了恣意馳騁的言說空間。
四
“我所偏愛的,是不受現代性欺騙的藝術家。”這是貢巴尼翁在《現代性的五個悖論》中說過的一句話。顯然,盧一萍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識,盡管時風多變,世相詼詭,他仍舊心如明鏡,未曾蒙塵,這樣的作家怎不令人偏愛?2016年正式退役之際,盧一萍寫了一首《卸甲詩》,其中有曰:“紅其拉甫曾勒馬,喀喇昆侖斗風寒。縱橫屋脊八萬里,只為斗室三千言。”對于盧一萍來說,當是早已寫出了可資懷念的“三千言”,但是對一個寫作者而言,卸甲并非意味著歸鄉,因為故鄉總是在遠方,他也只能用文字寫出下一個新的故鄉。
20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