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今《牧笛一聲天地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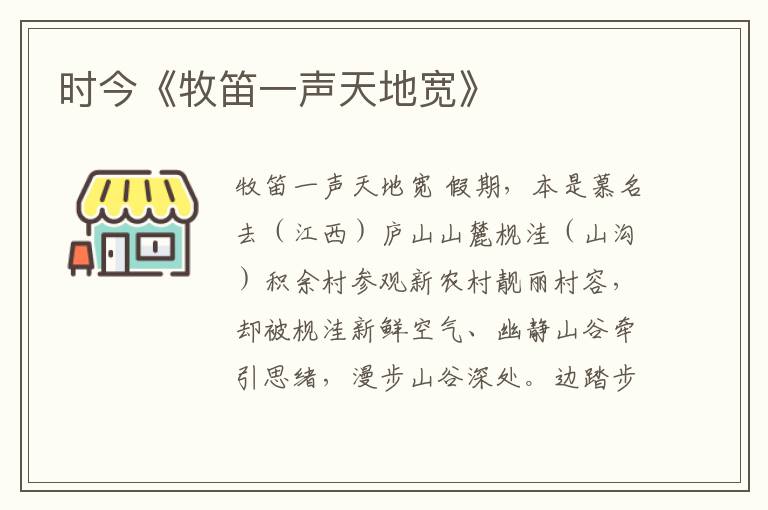
假期,本是慕名去(江西)廬山山麓枧洼(山溝)積余村參觀新農村靚麗村容,卻被枧洼新鮮空氣、幽靜山谷牽引思緒,漫步山谷深處。
邊踏步山道,邊四望枧洼。枧洼為廬山山南一條走向近東西的山溝。南為破山,北為坪嶺。蜿蜒溝底、山腰的小道,東可達溝外的環山通道、環城高速及鄱陽湖,西可攀吳障嶺、北山登山公路(吳障古道)。洼底平地,圍筑成一座小二型鄉鎮水庫。水庫簡單簡陋,一座大門緊鎖的二層控制室,一座聳立的庫閘,兩條“八”字形交匯的土壩,一汪淺淺的庫水,少見人跡,幽深清靜。
也許地形、水面抬升的緣故,從破山、坪嶺、吳障嶺,東出九條次級山脊,直奔水庫而來。自洼地,西生九條山溝,曲折地攀登遠處山峰。地貌異樣,難免產生幻覺,似乎水庫不僅是匯水之地,還是山脊潛沒之處。恍惚中,臆想平靜庫水之下,九條山脊如巨龍在翻滾攪動。冥冥中,揣測山谷深處,九條山溝幽深靜謐,其中一定有故事。
當然,還與自身有關。作為本地人,自小“中毒”太深,總認為“廬山有九十九座山峰、九十九條山溝,每座山峰都有先人遺跡,每條山溝都有歷史故事”,因此,潛意識認為,如此大的山溝,山中必有故事。
驀然,一陣罄聲,從山中傳來。透過云霧,聚焦定神,隱約看到水庫的北岔、水盡云深處,有一爿灰瓦黃墻的建筑。
以為“海市辰樓”,操本地口音,回首驚問庫工:
“那是何地?”
庫工淡淡回應:“廬山慧日寺。”
是被毀數百年的慧日寺!
文獻記載早已被毀?盡管一再獲得證實,口中還是嘀咕,心中仍有疑問。
看庫工狐疑的目光,只得自求安慰。也是,俗界之人不知佛界事,情有可原。更何況歷史上慧日寺并未列入廬山大叢林之列。
于是,開動腦筋,搜尋有關慧日寺的點滴,聊以彌補自己對慧日寺的無知。
廬山慧日寺始建于唐朝,距今千年有余。如今有人知道慧日寺,多與兩個人有關。一是北宋的蘇軾。當年,枧洼山路為自鄱陽湖上岸登廬山道路之一,往來山民客商、道人僧人、文人雅士,取山路上下廬山。上山之前,在慧日寺歇歇腳,次日上山。下山也在這地方歇歇,或陸路趕往江州城,或取鄱陽湖水路,經過長江、贛江南下北上各地。北宋元豐七年,蘇軾游歷廬山,與道潛登慧日寺樓觀,題名鐘上,后獨游白鶴觀,作《題西林壁》。
二是北宋年間慧日寺主持文雅禪師。文雅禪師生卒年限不詳,可其作品及故事如雷貫耳。其傳世之作《禪本草》。雖然僅區區二百余字,可對禪宗,乃至佛學有巨大影響。文中說:“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邪氣,辟雍滯,通血脈,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煩惱,去穢惡,善解諸毒,能調眾病。”將禪喻藥,認為“禪”是佛祖賜給世間治療眾生疾病的靈丹妙藥。
在其影響下,其師弟湛堂準禪師,即文準禪師,又被稱為泐潭(江西高安)文準,寫《炮炙論》一文。炮炙即炮制,本是將藥材加工成飲片傳統制藥技術。而在《炮炙論》中,文準禪師首先要求修禪者應熟讀《禪本草》,熟悉禪的“藥性”,而后“若克依此書。明藥之體性。又須解如法炮制。”所謂炮制,是用金剛手、大悲千手眼等對“禪本草”進行“加工處理”,熬出“湯藥”服用。《禪本草》和《炮炙論》都說修禪,互為表里。前者將禪喻藥,談禪性。后者則討論如何修禪。后來,無際禪師(明代)的《心藥方》、袁中道(明代文學家)的《禪門本草補》等,都是其風格的延續。《禪本草》雖然文章極端唯心主義,沒有實用價值。可對于佛學和信眾來說,無疑開創了佛教文化傳播的新形式,具有極為強烈的禪宗特性,在佛教文化史上亦有一定的地位,后人說到《禪本草》,必談及廬山慧日寺和文雅禪師。
文雅禪師之后,慧日寺幾度興衰,記載不多。清朝中葉,因天災而閉寺。同治《南康府志》卷23記載,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廬山“蛟”出無算,高下崩者以百計,沖倒慧日寺,沒僧人三口,破壞近山田地、山塘,淹死男婦六口。自此之后,枧洼登山之路荒廢,慧日寺也未重建。
循著罄聲,走近慧日寺,方知為近年重建新寺。新寺面積不大,占地不足十畝,四周依山就勢建有低矮的圍墻,將寺院圍成不規則的樟葉形。葉尖為一座低矮的天王殿,殿門黑漆草書寺名兼當山門。天王殿后,建有兩蓮池,池內種植睡蓮、蘆葦。
蓮池西,為小巧鐘樓。蓮池北,為完工不久的大雄寶殿,重檐歇山式屋頂,黛瓦黃墻,朱柱彩檐,為寺院僧人修行、香客拜謁場所。順東側圍墻,北為兩層寮房,供寺曾、居士、香客休息。南為老舊的平房,為經房、伙房、庫房。
恰好禪師、居士做功課,不便打攪。便請教盤桓寺中的湖北籍香客。
香客為常客,善言談,滔滔不絕地介紹慧日寺重建及僧人的佚事。
2002年,年僅25歲的心月聞熙禪師帶著幾位弟子,到荒山僻野重建慧日寺。一年之后,一點點、慢慢壘起了簡陋的佛殿、寮房和廚房,草創寺院。當時生活艱苦,土鍋土灶,打柴為薪,種菜為食。近幾年,才籌資建設天王殿、蓮池、鐘樓和大雄寶殿。
心月聞熙禪師畢業于國內知名大學,碩士專攻《易經》。畢業后,先在廬山東林寺入佛門,任知客。后離開熙熙攘攘的大寺院,尋找清靜地方清修。也許是對佛祖的敬佩,也許是慧日寺舊址僻靜,聞熙選擇遺址建寺,接續中斷三百余年香火,佛功居偉,僧界稱道。
而寺內唯一常駐楊姓女居士,也是傳奇。她是位三寶弟子,雅稱就是居士。皈依佛法,但并未出家修行。原學醫,為武漢某醫院醫師,已退休。兒孫滿堂,均在漢定居。2004年,偶然認識聞熙禪師并拜師,常住慧日寺至今。平日承擔寺院雜工、知客,負責后勤、接待等一并事務。雖身不著僧衣,剃度出家,但每天按時念經修行,虔誠執著。
仔細傾聽,漸入沉默。當年,文雅、文明禪師等一眾僧人,崇尚“不用求真并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五元燈會 卷十八)等不拘泥、不求名的修行理念,堅持“以心印心”,達到“明心見性”,恒心之下,寺雖小,得道大成;地雖偏,覺悟心得。如今,聞熙禪師清風為伴、明月相隨、鳥蟲和唱,安心參禪,佛學造詣日漸至深,寺有傳人。而且,寺間傳聞,不久將升任九江城中大寺能仁寺主持。
離開時,仍未打擾寺僧、知客,權當過客,悄悄潛行。撇去信仰,著實敬佩慧日寺歷代僧人“清心寡欲、執拗執著”的精神。這應該是山中小寺慧日寺的寺風、“人文圣山”廬山的傳統。同時,也深信這些傳統將代代傳承。
二〇二〇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