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叔河《今夜誰(shuí)家月最明》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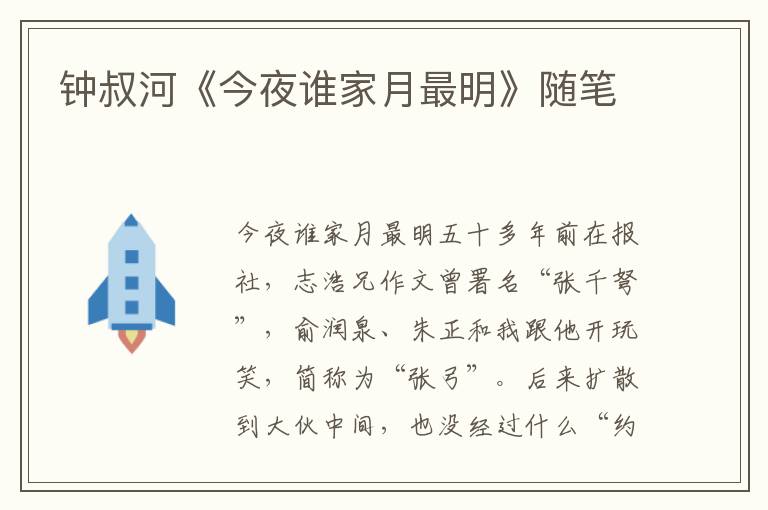
今夜誰(shuí)家月最明
五十多年前在報(bào)社,志浩兄作文曾署名“張千弩”,俞潤(rùn)泉、朱正和我跟他開玩笑,簡(jiǎn)稱為“張弓”。后來(lái)擴(kuò)散到大伙中間,也沒經(jīng)過(guò)什么“約定”,便“俗成”為“張公”,積重難返,就這樣喊下來(lái)了。
張公同我們幾個(gè),本來(lái)也只是一般的同事,僅僅因?yàn)槎枷矚g看些《聯(lián)共黨史》和《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以外的書,有一點(diǎn)共同愛好,見面時(shí)不免多談幾句。一九五五年反胡風(fēng),便把這四個(gè)人“整”成了“反革命小集團(tuán)”,隨后改為“反動(dòng)小集團(tuán)”,隨后又改為“落后小集團(tuán)”,最后才說(shuō)本來(lái)并沒有什么小集團(tuán),二三十歲的人卻都七老八十了。但這樣“整”也“整”出了一點(diǎn)副產(chǎn)品,就是我們之間不尋常的交情,既同為涸轍之鮒,自不能不相濡以沫也。
十多年前我寫了篇小文,題曰《卅五年前兩首詩(shī)》,這兩首詩(shī)便是志浩兄的《中秋對(duì)月同叔河作二首》,如今收在他這部詩(shī)集里。此詩(shī)和此文,即可以證明我們交情的久遠(yuǎn)了。如今志浩叫我為詩(shī)集作序,我想即以此舊文充數(shù)。杜詩(shī)云“庾信文章老更一九六一年中秋節(jié)的晚上,張公提了一斤月餅來(lái)我家,他住南門外侯家塘,我住北城教育街,相距約八九里。兩人都剛摘掉右派帽子,沒有正式工作,靠刻鋼板維生,刻一張蠟紙六到八毛,能將計(jì)劃供應(yīng)的食物買回就不錯(cuò),月餅理所當(dāng)然成了稀罕之物,很快便被孩子們分吃完了。
喝完一杯茶,閑話片刻,張公便起身告辭,我照例送他回去。出門時(shí)還不到九點(diǎn),從又一村到南門口,歷來(lái)繁華熱鬧的街道,因?yàn)椤按筠k城市人民公社”,撤并了商業(yè)網(wǎng)點(diǎn),“三年自然災(zāi)害”又帶來(lái)了商品匱乏,店鋪都已經(jīng)關(guān)門,時(shí)逢佳節(jié)卻行人特少。只有天上還未受到“人間正道”的影響,依舊是月到中秋分外明,電壓不足而黯淡的路燈為月色所掩,行道樹下黑暗得簡(jiǎn)直怕人,張公和我便在這黑暗中走著,一路伴隨著我們的,只有樹梢搖落的秋聲……
張公一直不做聲,我偶而說(shuō)句把話,他也只以哼哈回答,于是我也沉默了。出了南門口,路更寬,人更少,法國(guó)梧桐的颯颯聲也更響,寂靜中我的心只覺得一陣陣緊縮,張公卻忽然低聲吟詠起來(lái),是一首七言絕句:
今夜誰(shuí)家月最明,城南城北滿秋聲。
長(zhǎng)街燈盡歸何處,蕭瑟人間兩步兵。
“剛作的吧?”我問道。“是的,送給你的。”
“是首好詩(shī)”,我說(shuō),“不過(guò)這里只有一步兵,沒有兩步兵,我是既不能酒,又不能詩(shī)呀。”
張公不答話,卻低聲吟出了他的第二首來(lái):
艱難生計(jì)費(fèi)營(yíng)謀,日刻金鋼懶計(jì)酬。
未必此生長(zhǎng)碌碌,作詩(shī)相慰解君愁。
“也寫得好,只是太樂觀了。”我說(shuō),心中不禁凄然。
他勉強(qiáng)一笑,聽得出,笑聲也是凄涼的。
這時(shí)已經(jīng)走到侯家塘的十字路口,為了不打擾住在路旁菜土中矮屋里的張公的妻兒,我們便在路口分手了。
一個(gè)人踏著月色回家,夜深了,更冷清,我的心頭卻泛起了一股溫暖。
從那晚起,時(shí)間已經(jīng)過(guò)去了三十五年,這兩首詩(shī)卻一直存在我心頭,無(wú)論在月黑風(fēng)高的長(zhǎng)夜中,還是在陽(yáng)光燦爛的日子里,它們都是這樣的溫暖,這樣的鮮明。
——文章是抄完了,但還須說(shuō)明一點(diǎn),志浩兄這兩首詩(shī),集中自注作于一九六二年,我在文章中寫的卻是一九六一年。錯(cuò)的是誰(shuí)呢?也許是我吧,但白紙黑字十年前就已寫成,題目也不想從《卅五年前兩首詩(shī)》改成《卅四年前兩首詩(shī)》,于是只好像易子明同志給我作“小集團(tuán)分子”結(jié)論時(shí)宣布的那樣,再一次的“知錯(cuò)不改”了。
(二零零七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