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恒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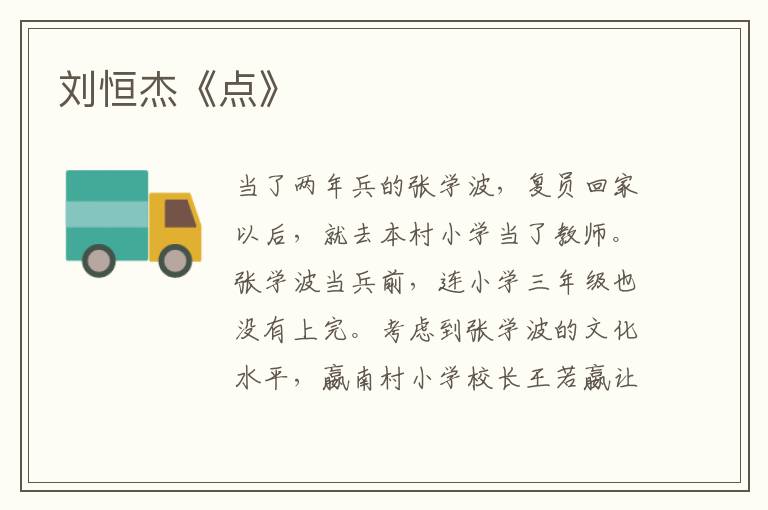
當了兩年兵的張學波,復員回家以后,就去本村小學當了教師。
張學波當兵前,連小學三年級也沒有上完。考慮到張學波的文化水平,嬴南村小學校長王若嬴讓他教一年級的語文課。幾天以后,王若嬴去聽張學波上課。張學波在教學生學漢字“tǎ(塔)”時,竟然拼出了一個“樓”字。因為課本上那“寶塔”一詞的右邊,畫著一幅延安寶塔的圖畫,張學波把那圖畫看成是一座樓了,所以,學生們也都異口同聲地,跟著他將樓讀成了“tǎ”。
那節課沒有聽完,校長王若嬴就拂袖而去。他一定要把張學波打發回家,這樣教下去,那不是誤人子弟嘛。但是,張學波卻哭著不肯走,說,這才來到學校不到一個星期就被攆回家,以后他就是捂著狗皮也出不了大門了,鼻涕一把淚一把,央求王若嬴好歹看在他舅舅的面子上,讓他在學校教完了這半年再走。張學波的舅舅是公社干部楊永勝,張學波能來小學當老師,就是他舅舅給嬴南村大隊書記王務德打的一通電話。
王若嬴就去大隊找王務德,說,堅決不能讓學波那孩子上課了,還把“tǎ(塔)樓”的事說了。王務德的女兒王蘭芳那時正上四年級,那天她也正好站在他父親的旁邊,雖然她學習也跟不上趟兒,但聽了王若嬴的話,也不禁大笑了起來,一直笑得直不起腰來。王務德也念過幾天書,也覺得這著實有點荒唐,但又礙于楊永勝的面子,就和王若嬴商量著,讓張學波在學校里當了一名校工。
當了校工的張學波,從此就有了一個外號,叫“tǎ(塔)樓”。
張學波知道自己教不了課,就好好干起了校工。他每天早晨總是早早地來到學校,先點著煤炭爐子燒上水,然后就去打掃衛生,打掃完衛生就去侍弄伙房后邊的那塊小菜地。菜地拾掇得差不多了,各辦公室的暖壺也都灌滿了,學生和老師這才陸陸續續走進學校。
張學波復員回家時,除了帶回來了一只馬蹄表,還帶回來了一臺收音機,他每天早晨都要打開收音機聽著收音機里的時間對表,因此,那馬蹄表盡管一停不停啪嗒啪嗒地走了四五年,一直沒有一分鐘的誤差。馬蹄表上有一只大公雞,隨著秒表啪嗒啪嗒地走動,那大公雞的頭也一抬一低,一抬一低,很好玩。課間,常有學生去看那只表,伙房太小,張學波就拿到外邊讓學生們看。學生們看著表,都覺得很好奇,那只大公雞成天抬頭低頭,從來也不停一停,它累不累?但時間長了,學生們也就不覺得好奇了。張學波在菜地里干活的時候,就把他那只馬蹄表放在地頭上,在伙房燒水時,就把馬蹄表放在伙房東邊的窗臺上或者靠北墻的那張小桌子上。
四五年級的大學生經常和張學波鬧著玩,說著他上課時鬧的一些笑話,有時還嘻嘻哈哈地喊出張學波的外號。都是一個村的,甚至還是街坊鄰居,張學波聽了,也只是咧咧嘴笑一笑,有時聽見學生說起來沒完沒了,或者說的過頭了,他要么坐在那里舉舉手做出一個要打人的樣子,要么就是把脖子上當啷著的哨子拿在手里做出要吹的樣子。學生們都知道張學波不會打人,但都害怕他吹哨子,他一吹哨子,就要忙不迭地向教室里跑,但是,不到上課的時間張學波是絕對不會吹哨子的。
張學波的外號一開始叫“tǎ(塔)樓”,后來又演變成了“哈嘍”。之所以演變成“哈嘍”,完全是因為在村東門口開理發店的徐紅芹。徐紅芹小時候曾經在東北哈爾濱的親戚家住過一段時間,回來后說話就有些撇腔。一天晚上,公社電影隊的老李來村里演電影,下午放了學,小學生們就直接從學校跑到放電影的場子上去占窩。那時,理發店里沒人來理發,徐紅芹正站在理發店的門口,等小學生們跑過理發店門口,她就問今晚演啥電影。小學生們早就知道了演啥,其中一個就一邊跑一邊喊:“《激戰無名川》!”徐紅芹聽見了,愣了一下,就撇著腔說:“啥?雞蛋五毛三?昨天才四毛五一斤,才兩天就漲錢了?漲到五毛三了?”正在這時,她看見校工張學波走了過來,就又問道:“哈嘍,你說說這雞蛋怎么就漲錢了呢?都五毛三了!”張學波聽了,自是一頭霧水,而小學生們卻都哈哈大笑了起來。從那以后,張學波的外號就由“tǎ(塔)樓”變成了“哈嘍”。
那外號傳得很快,以致傳到了張學波未婚妻的耳朵里,親事還差一點兒吹了。
張學波的未婚妻是馬泉公社馬泉村的,和嬴南村隔著二十幾里路。那年夏天的一天,嬴南村科技隊隊長王務來和保管張信堂,去趕馬泉集買噴霧器。那天是星期天,王務來的兒子王建昌和張信堂的兒子張學舉也跟著去了。王建昌和張學舉都是小學二年級的學生,七歲八歲正是狗也嫌的年紀,一路上,兩個人就像脫韁的野馬,不走人路,專門在溝邊地沿上蹦跶,要么就從麥地里岔。馬泉集的農具市場很大,各種各樣的農具都有,那些農具都是馬泉合作社擺出來的,以方便社員們挑選購買。賣噴霧器的在農具市場的最西頭,他們過去以后,很快就選好了兩臺,可是,等付錢的時候,才知道他們帶去的錢還差了七塊。人家又不賒,回去拿,路又太遠,來回有五十多里路,小麥現在正需要打藥,不敢耽誤一天工夫,那可都是給全大隊培育的優良麥種。王務來和張信堂沒辦法,就打算找找認識的人先借借,可兩個人又都想不起這附近有什么認識的人來,也想不起村子里誰家在這附近村里有親戚。
事情也是湊巧。正在他倆著急的時候,看見從南邊橋上過來了一個青年婦女,張信堂認得那婦女,那是張學波今年春節后才定了親的對象。張學波是張信堂近支的一個侄子,雖然不在一個胡同里住,但兩家還是一個家堂,定親后還請她來家里吃了一次飯,張信堂只知道她姓耿,但不知道叫啥名字。那小耿也認出了張信堂,就走過來說:“你不是俺叔?快上俺家里來坐坐。”張信堂說:“不去了,還要急著趕回去。”并說出了來買噴霧器錢不夠的事。小耿非要讓他們到家里喝碗茶不行。看到小耿真心實意的樣子,他們就沒再說別的,而且也真是渴了。那噴霧器攤子原來就擺在了小耿家的大門口。走進小耿的家,小耿就拿出十塊錢來給了張信堂,讓他們先坐坐,她出去一會兒就回來。張信堂和王務來喝了幾茶壺水,看見小耿還沒有回來,就要走。他們剛站起來,就看見一個男人從大門口走了進來,說:“晌午了,哪兒能讓你們走?親家來到大門口了,不吃口飯就走,這要傳到嬴南村,還不讓人笑話死我。”
聽話音這是小耿的父親了。緊接著小耿也提著大包小包走進了大門口。一會兒小耿的母親和妹妹也回家了。原來,那個賣噴霧器的售貨員就是小耿的妹妹。小耿的妹妹不好意思地朝他們笑了笑,就和姐姐到廚房忙活去了。小耿的父親是馬泉大隊的大隊長,很健談。說話間,小耿和妹妹已將滿滿一桌菜擺了上來,罐頭、香腸、豬頭肉等,大都是現成的。兩個小孩子見那么多好吃的,很高興,狼吞虎咽地吃飽了就到大門外邊去玩。小耿怕他們跑遠了,就也跟著出了大門。小耿問他倆叫什么名字,上幾年級了,誰教他們等,拐彎抹角就問到了她的對象張學波。開始時,兩個小孩子還矜持著,但當她問到張學波時,兩個小孩子就“tǎ(塔)樓”“哈嘍”起來了。張學波在課堂上說“tǎ(塔)樓”的時候,這兩個小孩子還沒上學,他們并不知道這“tǎ(塔)樓”的來歷,只是聽著大學生說他們也說。小耿聽得摸不著南北,只是被兩個孩子 “哈嘍”“tǎ(塔)嘍” 地逗笑了。
麥收以后,按當地的風俗,張學波割了一刀肉,買了兩瓶嬴水白干、兩條咸魚、兩個罐頭,去馬泉大隊看望岳父岳母,順便再把未婚妻領回來住幾天。雖然生產隊對社員出工抓得很緊,但定了親的婦女麥收以后去婆家住幾天,還是允許的。那天吃了午飯,張學波和小耿兩個人就一前一后走出了馬泉村。兩個人一邊說著話一邊向前走,小耿一會兒就說到了王建昌和張學舉那兩個小孩子上去了。小耿說,那天,那兩個小孩子真能逗,一會兒“tǎ(塔)樓”一會兒“哈嘍”的,問張學波是不是教他們上課,還問這“tǎ(塔)樓”“哈嘍”是咋回事?張學波開始還笑瞇瞇地聽著,但聽著聽著臉就騰地一下子紅了,一直紅到了脖子根。
到嬴南村的第二天,小耿就知道了張學波不再當教師了,而成了一個校工,也知道了他不當教師就是因為這個“tǎ(塔)樓”。小耿當天下午就跑回了娘家。其實,當校工也不錯,只是給老師們燒燒水,到了上下課的時間吹吹哨子,風吹不著雨淋不著,和站講臺的老師記一樣多的工分,有一樣多的補助,而且還比站講臺輕松多了。可小耿覺得自己受了侮辱,回到家就把自己關在屋里哭了一場,哭完了就對父母提出堅決要退婚,說四姨奶奶騙她,好歹她也是個高中生,當時就看中了他是個教師,原來連個“塔”“樓”都不分。小耿的四姨奶奶是泉河村的,是張學波母親的大妗子,也是這樁親事的媒人。
退婚這事很快就傳到了嬴南村。才定了的親事就吹了,這可是個大事。幾天后的一個上午,張學波的舅舅楊永勝就買了好酒好煙,去找到馬泉公社的一位姓韓的副主任一起去了小耿家。楊永勝許諾,一是保證兩年之內弄個煤礦正式工人的指標讓外甥去當工人;二是今年國慶節就把婚事辦了,結婚以后就安排小耿在嬴南村小學里當教師。嬴南村小學的那個校長王若嬴雖然難說話,但用誰不用誰當教師,是大隊書記說了算的。
張學波的親事差一點散了的事,王若嬴還是聽學校里的老師王蓮香說的。偌大個嬴南村沒有王蓮香不知道的事,她知道的事也從來沒有過夜的。王若嬴聽說這件事以后,心里就覺得有點對不起張學波,這親事真要是散了,張學波往后找對象就難了,真要是找不到對象,孤兒寡母的,他還不落下一輩子的埋怨。王若嬴看著張學波還年輕,人也憨厚老實,打那以后,一有空就教他漢語拼音,從a、o、e開始教。但張學波還不如黑瞎子掰棒子,黑瞎子掰棒子,到了地頭胳肢窩里還能剩下一個,可張學波到頭來是一個也記不住。看著他每次都學得一頭汗水,比推著滿滿兩簍子圈糞爬黃土嶺還累,王若嬴就不再教他漢語拼音了,轉而又教他九九歌,可是,那九九歌他背了倆月也背不下來,而且有時正背著“三七二十一”,一下子又“五七八十四”了。王若嬴覺得張學波在他跟前可能太緊張,就讓他抽空到班里和學生一起學,但張學波一次也沒有去。
張學波學文化不行,但種地炒菜做飯卻是一把好手,而且還會炒花生、炸油條、打火燒。尤其是那炒花生,從外表上看,一個糊的也沒有,就像是沒有炒過的一樣,但一捏開,簡直酥得不行。學校西邊原來有一堆碎石瓦片,張學波就清理出來刨出了一塊二厘大小的菜地,地雖然不大,但他埯上的蕓豆、架起的黃瓜、種上的白菜都有模有樣,逢上級領導來學校檢查工作或者老師們湊份子攢窮,也不用找人幫忙,張學波很快就能做出來七八個菜,而且做出的菜真正是色香味俱全。面食也不用出去買,張學波就去學校西邊校長王若嬴家的小南屋里挖來一瓢面。吃饅頭?張學波能左右開弓,兩只手一塊揉,一只手里揉著一個饅頭;吃面條?他搟出的面條不軟不硬厚薄均勻寬窄適度,看著就讓人眼饞。面條搟完了饅頭揉完了,那可真叫利索,面光盆光手光,真正的“三光”。酒喝完了,那邊要飯,這里熱騰騰的饅頭或者面條就端上來了。張學波說,他在部隊時干的就是炊事員。
王蓮香經常和張學波開玩笑:“學波,你說你這孩子,怎么就托生成了個帶把子的?”
結婚以后,張學波的妻子小耿就去嬴南村小學當了教師。小耿來學校不久,楊永勝就給張學波弄來了個煤礦工人的指標。但張學波他娘不讓他下煤礦,說當了幾年兵,這好歹回來了,不能再去干那個埋了沒死的活。楊永勝沒有辦法,就把張學波安排到了公社駐地東邊不遠的溫家埠鐵礦當了臨時工,每個月三十七塊五毛錢。張學波他娘不知道這鐵礦也得下井,就同意了。
去鐵礦上班不久,張學波就推著一輛小推車來到了學校,小車子的一邊拴著一個大鐵圈,像水車的轉輪那么大。張學波說:“這是點。我走了,不能讓王校長滿學校轉著吹哨子。就把這個點掛在王校長辦公室門前的老槐樹上,以后,上學放學上課下課就打點。”那個點,是張學波用他第一個月的工資買來的。那天,老師們七手八腳把點掛起來,用點錘子一敲,那聲音還真是響亮清脆。那從點上發出來的“當——當——”的聲音,就像打著顫一樣,一圈一圈飛向了校園的角角落落。那聲音傳得很遠很遠,全村的人都能聽到,以致各生產隊的隊長在喊社員上坡時,就常常喊著:“學校里都打起床點了,還賴在炕上不起!”
那時,村里人家很少有表,他們估算時間,有時是聽雞叫,有時是聽掛在墻上的洋戲匣子,有時是瞇起眼來看看天上的日頭。但勞累了一天的社員們,吃了晚飯頭一挨著枕頭就打起呼嚕來,早晨聽不見雞叫也是常有的事,而掛在墻上的洋戲匣子也是三天兩頭不響,不是誰家屋檐下的電線斷了,就是自家屋門口的地線露了出來,就是響的時候也是嗤嗤啦啦的。那當當當當的清脆的點聲,不但是學生們的鐘點,也成了全村人的鐘點。
張學波去溫家埠鐵礦第三年冬天的一個上午,礦上突然有兩個人來學校找耿秀芬老師,說張學波出了點小事故,要她跟他們去一趟。原來,前一天下午下班時,張學波和幾個下班的工友一起坐罐車從井下上來,那罐車不知道怎么的,突然晃蕩了起來。當罐車升到二十多米高的時候,站在罐車邊上的張學波突然從罐車里摔了出來……耿秀芬跟那兩個人趕到縣醫院時,張學波已經快不行了。
耿秀芬把耳朵湊在張學波的嘴上,聽見他斷斷續續地說:“秀芬,我一直想給咱嬴南村小學買個電鈴,把那個點換了,礦上的小學就有電鈴。我這就走了,你可一定替我買個電鈴,要買自動的,不用拉就……”話沒有說完,張學波就咽了氣。
給丈夫做完了一七的第二天,耿秀芬就從撫恤金里拿出一筆錢,去縣城買來了一套全自動電鈴。
張學波去世以后,他的母親每天以淚洗面,視線就漸漸模糊了。前幾年,張學波的妻子小耿退休了,退休不久,小耿要去城里給自己的女兒看孩子。小耿放心不下婆婆,要把婆婆也一塊帶到城里去,可婆婆說啥也不肯去。
自從村小學合并到鄰村的學區小學以后,新上任的村兩委要把原來的村小學劃成宅基地,那棵掛著點的老槐樹由于礙事也要刨掉。早已退休的王若嬴找到村干部,堅決要求把那棵古槐樹留下來。村委領導采納了王若嬴的建議。王若嬴拿出自己的積蓄,請來了兩名石匠,在老槐樹周圍壘起了護欄。那護欄四邊的石板上都雕刻著很精致的圖案,其中一幅是一個中年男人推著一輛小推車走進學校大門,那小推車的一邊就放著這個點。
二十幾年過去了,那點和電鈴還掛在那棵古槐樹上。那敲點的點錘子也在,有的時候,在護欄石上坐久了的王若嬴,會情不自禁地站起來,拿起點錘子敲一下那點,那點發出的聲音,依舊很響很清脆,全村的人都能聽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