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叔河《天窗》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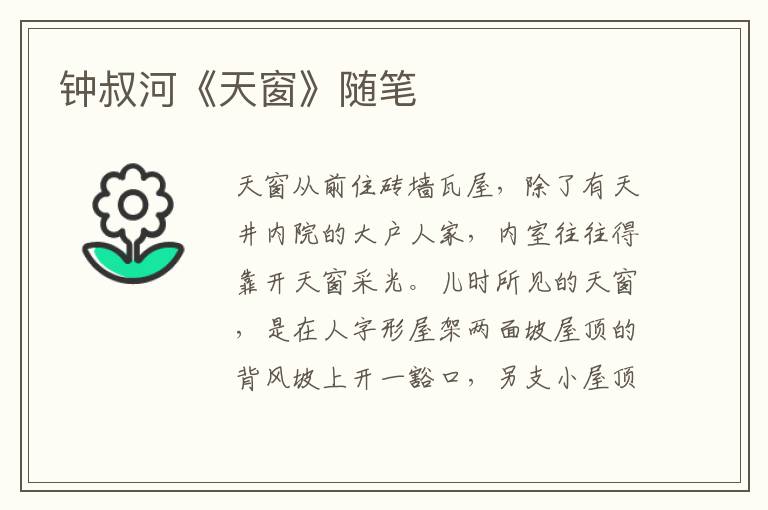
天窗
從前住磚墻瓦屋,除了有天井內(nèi)院的大戶人家,內(nèi)室往往得靠開天窗采光。兒時所見的天窗,是在人字形屋架兩面坡屋頂?shù)谋筹L(fēng)坡上開一豁口,另支小屋頂以遮雨,對外的口子以平板遮蔽;板可活動,上系一繩,需要采光時拉開,冬天或雨雪時則可關(guān)上。
后來到了長沙,有兩年住在開天窗的屋子里。這天窗卻已簡化為兩排玻璃瓦,只能采光,不能打開出氣了。少年多綺思,夢中乍醒,望著天窗灑下來的光越來越明亮,總有好夢難留的一種悵惘塞在心中,苦于無法排遣。假日遇大雨不能出門,又常常仰臥著看雨水從明瓦上迅速地流過,聯(lián)想到韶華易逝,人生無常,不禁生發(fā)出少年人常有的感傷。
有一個冬夜,一覺醒來,滿屋漆黑,連屋頂上原來總有的一點微光也消失了,真是伸手不見五指,本來熟悉的上下四周忽然變成遙遠(yuǎn)而不可知,不由得害怕起來,有點覺得窒息,鉆進(jìn)被窩再也睡不著。好不容易捱到外屋的人起床,一開門覺得特別明亮,原來夜里下了幾寸深的雪,看來晶瑩潔白的雪其實并不透光,竟將天窗完全遮死。
我想,人類學(xué)會開天窗,給閉塞黑暗的洞穴引進(jìn)光明和生氣,實在是一種技術(shù)的創(chuàng)造和文明的進(jìn)步,是猴子變?nèi)酥匾囊徊健6鴼v史變遷,“開天窗”到后世卻有了另外的意義。明郎瑛《七修類稿》:
今之?dāng)咳素敹鵀槭渍呖藴p其物,諺謂開天窗。
清末夏仁虎《舊京瑣記》:
朝殿試卷忌錯落,應(yīng)試者多習(xí)打補(bǔ)子,以極薄之刀將錯處輕輕刮去,復(fù)于本卷閑處刮取紙絨勻鋪于上,以水潤濕,使之粘連,殊有天衣無縫之妙。但藝稍生疏,或下手微重,穿紙成洞,又謂之開天窗,雖有佳卷,勢難前列。
黑吃黑吞財和彌縫考試卷,這就不好說是文明進(jìn)步不是了。
民國時期言論不自由,有所謂新聞檢查,報紙和刊物常常整篇整段被刪掉。普通的做法是“刪掉的地方還不許留下空隙,要接起來,使作者自己來負(fù)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責(zé)任”(魯迅《花邊文學(xué)·序言》)。但也有檢查者疏忽、被檢查者躲懶或有意消極抵抗的情形。于是版面上便會出現(xiàn)成塊的空白,這也叫做“開天窗”。關(guān)于這種“開天窗”,有一個有趣的故事。大約在蔣介石四九年元旦引退前不久,某報曾辟一專欄,評論每日時事,讀者頗為歡迎,每天都爭著看報上花邊圍著的這一塊。某日出報前檢查官嚴(yán)令:專欄本期太不像話,必須撤掉。當(dāng)時正值白色恐怖高潮,誰都不愿意碰在槍口上,當(dāng)然得撤。報紙印出來后,花邊圍著的一塊果然成了“天窗”,只在原該是標(biāo)題的地方仍有一行不大不小的字:
今日無話可說。
(二零零四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