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永敏《奔跑的蘆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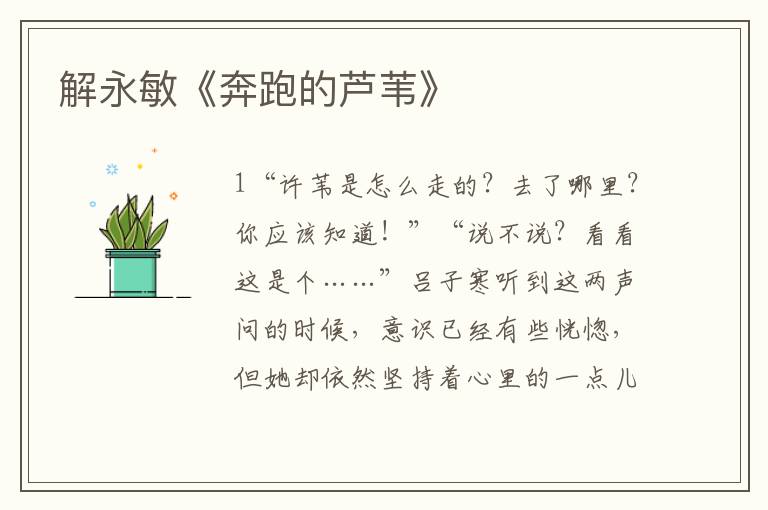
1
“許葦是怎么走的?去了哪里?你應(yīng)該知道!”
“說(shuō)不說(shuō)?看看這是個(gè)……”
呂子寒聽(tīng)到這兩聲問(wèn)的時(shí)候,意識(shí)已經(jīng)有些恍惚,但她卻依然堅(jiān)持著心里的一點(diǎn)兒高地,自己對(duì)自己喃喃自語(yǔ):“不知道……不……知道……”
“啊——”
呂子寒叫了一聲。緊接著,她的衣服被撕扯開(kāi)了,露出年輕女子豐腴的胸,豐腴的腿,還有豐腴的……
“骨頭真的比鐵硬!”
“那就試試?”
“好,試試!”
呂子寒叫了一聲。一根頭發(fā)絲一樣細(xì)的針,拖著一根通了電的線,慢慢刺向她的一只奶頭。她突然慘叫起來(lái),凄慘的叫聲驚著了旁邊廚房里的一個(gè)廚子,廚子說(shuō)咋會(huì)叫得這么瘆人?還是一個(gè)女人的!廚子的幫手說(shuō),這里哪天沒(méi)有叫聲?哪天沒(méi)有女人的叫聲?廚子不再吱聲,呂子寒凄慘的叫聲依然傳過(guò)來(lái)。那根頭發(fā)絲一樣細(xì)的針,依然在她的周身游走著……
當(dāng)年局子里審案子都用這樣的方式,骨頭再硬的人也受不了,一來(lái)二去,有什么說(shuō)什么,沒(méi)什么也會(huì)編出什么來(lái)說(shuō)什么。對(duì)了,那叫什么來(lái)?對(duì),老虎凳!只要給上了老虎凳,幾乎沒(méi)有人不說(shuō)話。不過(guò),這個(gè)叫呂子寒的小女子,還真就是硬骨頭!
這時(shí)候,一盆冰冷的涼水嘩地一下沖著她滿頭滿臉潑了過(guò)來(lái),她打了一個(gè)激靈,卻很不情愿地眨了眨眼睛,看到幾張猙獰著的臉。
“說(shuō)!你為什么不說(shuō)——”
猙獰著的臉上有一張嘴,那嘴里發(fā)出的叫嘯聲,再一次驚得呂子寒眨了眨眼睛,但她已經(jīng)沒(méi)有辦法說(shuō)話了,她的嘴上鮮血洶涌,噴涌著的鮮血堵住了她的喉嚨……
許葦很長(zhǎng)時(shí)間之后才知道呂子寒為他受了刑。那個(gè)年代,消息傳遞得慢,誰(shuí)有什么事,大都是過(guò)了很長(zhǎng)時(shí)間才被人知。許葦既然跑了出去,一時(shí)半會(huì)兒也就不敢回來(lái),不敢回來(lái)自然也就不知道呂子寒為他受刑。但知道這個(gè)事情之后,許葦先是淚水漣漣,緊接著就去警察局找人營(yíng)救。告訴他事情的人說(shuō),你找誰(shuí)營(yíng)救?都過(guò)去多長(zhǎng)時(shí)間了?呂子寒被弄到哪里去了都沒(méi)有一個(gè)準(zhǔn)確消息,怎么營(yíng)救?再說(shuō)這年頭,救一個(gè)人根本不容易!
許葦繼續(xù)淚水漣漣,然后一下跪在地上,沖著那個(gè)二層小樓的方向磕了三個(gè)響頭。然后,他喃喃自語(yǔ):“子寒,是俺害了你,但愿你能化險(xiǎn)為夷!”
……
以上幾個(gè)畫(huà)面,是我十六年前聽(tīng)一個(gè)老濟(jì)南人親口講的。
老濟(jì)南人講述這組畫(huà)面時(shí),說(shuō)自己當(dāng)年雖小,卻記憶深刻。他說(shuō)有些是親眼所見(jiàn),有些是聽(tīng)老人們所傳,但基本事實(shí)沒(méi)有太大出入,過(guò)去這么多年,依然想講出來(lái),想讓更多人知道,在濟(jì)南曾經(jīng)的東流水街上曾發(fā)生過(guò)這樣一個(gè)故事。
“你是寫(xiě)小說(shuō)的,給你講一個(gè)故事,能不能寫(xiě)一寫(xiě)?”
“能不能寫(xiě)得看故事有沒(méi)有內(nèi)涵,如果一點(diǎn)兒內(nèi)涵也沒(méi)有,再精彩也沒(méi)寫(xiě)出來(lái)的必要。”
“你呀,還真有點(diǎn)兒不知天高地厚!”
“是嗎?”
“當(dāng)然是!”
講這個(gè)故事的老濟(jì)南人姓廖,家住芙蓉街上的一處平房,許多人喊他廖三,所以我也叫他廖三。后來(lái),廖三對(duì)我說(shuō),別人喊廖三,你怎么也喊俺廖三?廖三這個(gè)名字是你能喊的?
我有些蒙。別人都喊你廖三,我怎么就不能喊你廖三?廖三說(shuō)俺比你足足大出差不多四十歲吧?我說(shuō)是,整整比我大了四十歲。他說(shuō)一個(gè)大你四十歲的人,你能喊廖三?我明白了,便不再喊他廖三,改稱他為廖叔。廖三聽(tīng)我喊廖叔,笑了,他笑的讓人看著很舒服。
這就對(duì)了,再怎么著大你這么多,也得喊一個(gè)叔不是?廖三說(shuō)著,又笑了,我也笑了。我和廖三都笑出了聲,爽朗的笑聲在芙蓉街上空回蕩著。
“別不上心,”廖三笑過(guò)又說(shuō),“你是個(gè)喜歡寫(xiě)東西的人,應(yīng)該把這個(gè)故事好好寫(xiě)一寫(xiě),挺有意思的。對(duì)了,這個(gè)故事俺一次給你講不完,有時(shí)間你就來(lái),聽(tīng)多了也就能體會(huì)到里面的一些事為什么發(fā)生。寫(xiě)下來(lái)登在你們辦的周刊上,起碼讓人看著好玩吧?”
廖三說(shuō)著的時(shí)候,右手捏著一根煙袋,捏一會(huì)兒把煙袋放在嘴里抽幾口,然后吐出一個(gè)很好看的煙圈,給人的感覺(jué)他是一個(gè)煙界高手。但他抽的是煙袋,那時(shí)濟(jì)南已經(jīng)沒(méi)多少人抽煙袋了,而且他煙袋鍋?zhàn)永镅b的始終是旱煙。我問(wèn)他為什么抽旱煙,不抽煙卷兒?他笑笑,說(shuō)你以為俺是多么有錢(qián)的主兒?能抽旱煙就不錯(cuò)了,還燒包的抽煙卷兒?你知道煙卷兒多錢(qián)一盒?拾起一盒都七八塊,有買(mǎi)煙卷兒的錢(qián)不如拿來(lái)買(mǎi)肉吃呢。
廖三說(shuō)他早年在一家工藝品廠退休,退休金不多,僅夠吃飯用,所以生活很簡(jiǎn)樸。
聽(tīng)廖三講這個(gè)故事,是在他芙蓉街上的一家小型玉器店里。廖三的玉器店也就七八平方,三面擺著柜臺(tái),中間一小點(diǎn)兒空地,客人來(lái)了都是站著看他的玉器品。他的玉器品還真不少,有大點(diǎn)兒的,也有小點(diǎn)兒的,有和田玉,也有翡翠玉、泰山玉,還有其他一些林林總總的東西。單看那些物件,還以為他是個(gè)很有錢(qián)的老板,其實(shí)他也就是混吃混喝而已,開(kāi)這個(gè)小店沒(méi)多大賺頭,用他的話說(shuō)除了房租、水電費(fèi)和稅,剩不下幾個(gè)子兒,只是為有個(gè)事情做而已。他說(shuō)人上了年紀(jì),有事做和沒(méi)事做不一樣,起碼對(duì)身心健康有好處。
廖三說(shuō)你知道濟(jì)南的東流水街嗎?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條街早已沒(méi)了,但那里發(fā)生的故事俺卻一直記著,那時(shí)俺還是個(gè)不到十歲的孩子,卻看到了在東流水街上抓人的情景。被抓的是兩個(gè)人,一個(gè)叫呂子寒,一個(gè)叫許葦。不過(guò),他們一個(gè)被抓住了,一個(gè)跑掉了。
天氣很熱,是個(gè)七月的正午。東流水街上人來(lái)人往,月芽泉、洗心泉、靜水泉、回馬泉、賢清泉以及顯明池邊……對(duì)了,你不知道,那個(gè)年代東流水街上充滿了泉子,一處處泉子清涼可人,誰(shuí)都想去那里涼快。所以,那一刻的幾處泉子邊游人如織。有穿著大褂的年輕男子,將腳伸進(jìn)泉水里泡著,手里還拿一本書(shū),專(zhuān)注地念著。也有一些十幾歲的流皮孩子,把腳伸進(jìn)泉水里泡著的當(dāng)口,還不時(shí)伸出手將泉水四處撩,偶爾撩到在泉邊路過(guò)的年輕女子臉上、身上,那涼便驚得年輕女子用手掩起臉面,忍不住發(fā)出低沉的驚叫。這自然中流皮孩子們的意,他們望著年輕女子的樣子,哈哈大笑,直笑得年輕女子白他們幾眼,然后緊跑幾步,離他們遠(yuǎn)了一些。而緊跑幾步的時(shí)候,年輕女子難免弄得自己花枝亂顫,也就引來(lái)流皮孩子們更加放肆的笑。
對(duì)了,這是在和你說(shuō)背景,故事發(fā)生的時(shí)候東流水街上的背景就是如此。可以想想,在這樣背景的一條街道上,突然發(fā)生一陣動(dòng)槍動(dòng)炮的事,會(huì)是什么樣子?
事情還真就在這樣的背景里發(fā)生了。
那些流皮孩子狂笑的時(shí)候,一陣槍聲打破了東流水街上的這般吉祥。那時(shí)人們特別喜歡互致吉祥,過(guò)年過(guò)節(jié)時(shí),不像如今先問(wèn)聲好,而是先問(wèn)吉祥。所以說(shuō)那陣槍聲打破了東流水街上的吉祥。
隨著激烈的槍聲,一個(gè)年輕男子慌慌跑到一處泉子邊,回頭望了一眼,見(jiàn)有人追了過(guò)來(lái),便撲騰一下跳進(jìn)泉子里。那時(shí)東流水街上的泉子和如今的泉子不一樣,每一處泉子差不多都水深三米或七八米,每一處泉子幾乎都與護(hù)城河相連。泉子一天到晚往外冒,如果不與護(hù)城河相連,東流水街不就被淹了?那時(shí)的東流水街是濟(jì)南的繁華之地,有很多店鋪,還有銅元局、面粉廠、造紙廠、印染廠什么的,一些小型阿膠作坊和電燈公司經(jīng)營(yíng)的也很火。現(xiàn)在一些上了年紀(jì)的老人想起東流水街,還都覺(jué)得可惜,為什么就不能保留下來(lái)呢?
話說(shuō)遠(yuǎn)了,還是接著說(shuō)跳泉子的年輕男子。年輕男人見(jiàn)有人追了過(guò)來(lái),一下跳進(jìn)泉子里,隨著他的那一跳,“啪啪”兩聲槍響,子彈“嗖嗖”飛了過(guò)來(lái)。當(dāng)時(shí),俺就在離泉子不遠(yuǎn)的一個(gè)店鋪門(mén)口,店鋪門(mén)口有個(gè)人在拉糖稀,老爹給了個(gè)小錢(qián),俺買(mǎi)糖稀吃。你不知道糖稀是什么玩意兒吧?如今賣(mài)那玩意兒的差不多絕跡了,也不是,春冬兩閑時(shí)黃河北的一些農(nóng)村還能看到。糖稀是“怡糖”的一種,做起來(lái)簡(jiǎn)單,吃起來(lái)甜柔爽口。是哄孩子的玩意兒,孩子們都喜歡吃。雖然一塊糖稀值不了幾個(gè)錢(qián),那年月也不是每家孩子都能吃得到。俺爹疼俺,經(jīng)常給錢(qián),俺家在東流水街上開(kāi)著阿膠作坊,每天能掙很多錢(qián),所以俺經(jīng)常有糖稀吃。
那一會(huì)兒,好多人都驚著了,子彈“嗖嗖”飛著,誰(shuí)看了都害怕。好在沒(méi)打著人,幾個(gè)穿便衣的警察,不對(duì),也有穿著制服的警察,追到那處泉子邊,又朝泉子里打了幾槍?zhuān)訌棸阉疀_起老高,水落下來(lái)的時(shí)候嘩啦啦響,挺嚇人。
那伙人沖泉子里打過(guò)槍?zhuān)裁匆矝](méi)看見(jiàn),就有些納悶。“奶奶個(gè)熊!就這大個(gè)泉子,他跳下去咋就沒(méi)影了?”一個(gè)小頭目對(duì)著泉子邊罵邊喊。“是啊,人呢……”其他便衣警察或穿制服的警察,都附和著小頭目,他們很納悶,跳進(jìn)泉子里的年輕男子是魚(yú),還是王八?跳進(jìn)水里咋就不見(jiàn)了?
廖三講述時(shí)表情很?chē)?yán)肅,根本感覺(jué)不到任何戲說(shuō)的成分。他說(shuō)這是真事,過(guò)去這么多年了,不講出來(lái)心里憋得慌。畢竟年紀(jì)大了,把當(dāng)初知道的事留下一點(diǎn)兒是一點(diǎn)兒。
廖三說(shuō)對(duì)于那個(gè)跳泉子的年輕男子,不僅警察納悶,周?chē)芏嗳硕技{悶,好端端一個(gè)人咋跳下去就消失了呢?
“要是淹死也就罷了,關(guān)鍵是人家沒(méi)淹死,淹死了早從水里漂上來(lái)了。”廖三說(shuō)那會(huì)兒他吃了糖稀,又往泉子邊上湊了湊,根本都沒(méi)害怕,只是看著那些便衣警察和穿制服的警察對(duì)著泉子說(shuō)來(lái)說(shuō)去。
“這是哪一年的事?能夠記起當(dāng)時(shí)的年號(hào)嗎?”我被廖三的講述吸引了,便想弄清這事發(fā)生在哪一年。廖三想了,說(shuō)那會(huì)兒俺七歲還是八歲,今年俺八十一,前推七十年,俺是十一歲,再減去三歲或四歲,應(yīng)該前推七十四年,那年俺七歲,因剛剛上了一年私塾,俺六歲讀私塾,當(dāng)時(shí)不愿意去,爹還揍了俺三巴掌,這事什么時(shí)候也忘不了,所以說(shuō)應(yīng)該是1926年,那會(huì)兒濟(jì)南還沒(méi)遭慘案。對(duì),就是1926年夏天的事。
廖三雖然經(jīng)常給人扯閑篇兒,但他講的這事很真實(shí)。我找了幾張紙,坐在他旁邊,一點(diǎn)點(diǎn)記著。他講得斷斷續(xù)續(xù),不是一次講完,什么時(shí)候去了,他得閑就講一會(huì)兒,不得閑還得忙活著給人講玉的知識(shí),畢竟他的生意是賣(mài)玉石。
2
認(rèn)識(shí)廖三是一個(gè)偶然,聽(tīng)廖三講述故事更是一個(gè)偶然。
十六年前,我正在芙蓉街北頭一家還算有影響力的新聞周刊做副總編,每天中午都和同事跑到芙蓉街上閑逛。芙蓉街上小吃很多,我們的午飯大多在那里解決。常聽(tīng)人說(shuō)芙蓉街上的小吃不衛(wèi)生,但我們根本不拿著當(dāng)回事,每個(gè)月混的銀子不多,能夠吃上芙蓉街的小吃已經(jīng)不錯(cuò)了。一個(gè)叫老四的同事說(shuō)得好,許多外地人花三五千塊錢(qián)跑到濟(jì)南來(lái)看大明湖,然后再到芙蓉街上吃小吃,咱天天在這里,隨便吃點(diǎn)兒什么也值五六百甚或上千塊呢。當(dāng)然,他這話有些自嘲,可作為新聞民工每個(gè)月混不了幾個(gè)銀子,只能靠自嘲進(jìn)行自我安慰。
那天中午,在芙蓉街上吃過(guò)大米面皮,我依然從南頭到北頭閑逛。不知不覺(jué),逛進(jìn)廖三的小型玉器店。說(shuō)是個(gè)玉器鋪?zhàn)痈线m,店面太小,只能稱鋪?zhàn)印2贿^(guò),廖三給鋪?zhàn)悠鹆藗€(gè)好聽(tīng)的名——石寶齋。
說(shuō)到這里,應(yīng)該詳細(xì)交待一下廖三這個(gè)人了。當(dāng)然,那天中午的時(shí)候我還不知道他叫廖三,和廖三根本都不認(rèn)識(shí),只是偶然逛進(jìn)了他的鋪?zhàn)樱峙既槐凰鲇屏耍统鲆粋€(gè)月的工資買(mǎi)下了他的一塊所謂和田玉。
“任何物品都是自然天成,但人卻非想求個(gè)靈字,實(shí)在不值。以玉見(jiàn)性,常表溫潤(rùn),清凈之心。試想一個(gè)佩玉之人若常以焦躁之心待人,配什么玉都會(huì)見(jiàn)損,這是自然道理。若明白,配何物都明理見(jiàn)性才是……”這是那天中午認(rèn)識(shí)廖三五分鐘后他的一番說(shuō)道。廖三的這番說(shuō)道是沖我而來(lái),因我拿起他的一塊很小的和田玉,左看看,右看看,像是要買(mǎi)下來(lái)的樣子。于是,廖三和我沒(méi)話找話說(shuō)了。他說(shuō),先生想買(mǎi)塊玉?是自己戴,還是給心愛(ài)的戴?聽(tīng)著“心愛(ài)的”三個(gè)字從一個(gè)八十多歲的老翁嘴里說(shuō)出來(lái),我有些驚。想這人怎么了?為了多掙點(diǎn)兒錢(qián),這大年紀(jì)了還想著“心愛(ài)的”?我告訴廖三沒(méi)有“心愛(ài)的”,只有自己,即便是花錢(qián)買(mǎi)塊玉,也是為了自己欣賞,聽(tīng)說(shuō)三年之內(nèi)人養(yǎng)玉,三年之后玉養(yǎng)人,就想買(mǎi)塊玉戴上三年,也讓玉養(yǎng)養(yǎng)自己,哪怕是多活上三年五載,不也是白賺的?廖三聽(tīng)著,笑了。從此,我和他成了莫逆之交,有事沒(méi)事都會(huì)到“石寶齋”找他喝茶,聊天。
廖三喜歡講故事,他講過(guò)燕子李三的輕功,講過(guò)韓復(fù)榘看打球,還講過(guò)大明湖里的蛤蟆,每次講都繪聲繪色,我曾問(wèn)他,是不是祖上是說(shuō)書(shū)的?他笑笑,說(shuō)祖上沒(méi)說(shuō)書(shū)的,可自己從小喜歡到大觀園聽(tīng)說(shuō)書(shū)的,一來(lái)二去,好像也有了這種天分。
講年輕男子跳泉子的故事時(shí),他說(shuō)你不是會(huì)寫(xiě)嗎?能把這事寫(xiě)出來(lái),讓很多人知道濟(jì)南東流水街上發(fā)生過(guò)一個(gè)故事,故事很凄美,也很感人,雖然已過(guò)去很多年,至今想起來(lái)依然感覺(jué)有味道。對(duì)了,廖老三從來(lái)不說(shuō)故事精彩,只說(shuō)有味道,有味道的故事也就是很精彩。
年輕男子跳進(jìn)去的是洗心泉,有人說(shuō),年輕男子跳下去洗心,竟然把人洗沒(méi)了影兒。
“奶奶個(gè)熊!咋就沒(méi)了影兒呢?難道他是一條成精的魚(yú)……”
警察小頭目依然在泉子邊上罵。這時(shí)候的泉水已清澈見(jiàn)底,根本沒(méi)有任何人跳下去的跡象。幾個(gè)穿便衣的和穿制服的警察,也隨了小頭目罵咧咧一頓,走了。
“知道嗎?有個(gè)年輕人成精了!”
“不會(huì)吧?”
“咋不會(huì),真的呢!”
東流水街上趨于平靜之后,幾個(gè)店鋪門(mén)口聚起不少人,有人說(shuō)著泉子里的稀罕事,有人說(shuō)著護(hù)城河里的稀罕事,所有的稀罕事都與跳進(jìn)泉子里沒(méi)了影兒的年輕男子有關(guān)。
其實(shí),誰(shuí)都知道有人在與政府作對(duì),政府派了警察天天抓人,卻天天抓不著。東流水街上的人很多,可總也不能亂抓,說(shuō)人家反對(duì)政府,是共產(chǎn)黨人,那也得有證據(jù)不是?
“站住!”
“哥,咋是你?”
“嗯,這么晚了還在街上?”
“等爹下班。”
“爹出來(lái)告訴他,說(shuō)俺這十來(lái)天出個(gè)遠(yuǎn)門(mén)。”
“你不上學(xué)堂了?”
“上,就是學(xué)堂安排的出遠(yuǎn)門(mén)。”
天黑下來(lái)時(shí),東流水街上的阿膠作坊門(mén)口,一小男孩突然被一年輕男子逮住。年輕男子輕聲說(shuō)著,小男孩點(diǎn)著頭。后來(lái),年輕男子撫摸了一下小男孩的頭,說(shuō)明兒讓爹給你剃剃頭,頭發(fā)長(zhǎng)了,天熱,一出汗都粘在一起,不難受?小男孩笑笑,說(shuō)用泉水洗洗就不難受了。年輕男子說(shuō)泉水很深,別淹著。小男孩抬起頭,有微弱燈光從店鋪里透過(guò)來(lái),照著小男孩的臉,也照著年輕男子的臉。小男孩說(shuō)知道不?過(guò)午一人跳進(jìn)泉里,沒(méi)影兒了。年輕男子說(shuō)影兒咋能沒(méi)?一定有。小男孩說(shuō)沒(méi)了,真的沒(méi)了。
“叭溝兒——”
“叭溝兒——”
又一陣槍聲從東流水街的北頭響起,年輕男子說(shuō)了聲不好,拍拍下小男孩頭,拐進(jìn)一條巷子。
“哥,哥……”
“喊誰(shuí)呢?”
小男孩的爹從阿膠作坊出來(lái),抬頭往響槍的方向望望,一把將小男孩拉進(jìn)懷里,說(shuō)出來(lái)干嘛?多危險(xiǎn)!小男孩說(shuō)出來(lái)接爹。小男孩又說(shuō),哥走了,說(shuō)學(xué)堂安排出遠(yuǎn)門(mén)。爹嘆口氣,說(shuō)隨他去吧……
3
好長(zhǎng)時(shí)間沒(méi)再去廖三的“石寶齋”。
廖三打電話來(lái)說(shuō)弄了上好的龍井,讓去嘗嘗。我說(shuō)在禁毒支隊(duì)采訪,忙得一塌糊涂。他說(shuō)再忙也得過(guò)來(lái)看看,有話和你說(shuō)。過(guò)了幾天,采訪結(jié)束,我去了廖三那里,喝著他泡的龍井:“廖叔有什么話和我說(shuō)?”
“那故事只講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不想聽(tīng)了?”
“當(dāng)然想聽(tīng),你繼續(xù)講。”
廖三笑笑,繼續(xù)講那故事。我了解他的脾氣,一個(gè)故事講不完心里鬧得慌。
廖三說(shuō)年輕男子跳泉之后沒(méi)幾天,濟(jì)南就出現(xiàn)一個(gè)奇怪現(xiàn)象,所有警察每天跑到護(hù)城河邊上,觀察里面有沒(méi)有蘆葦走動(dòng)。警察都像得了神經(jīng)病,一個(gè)個(gè)專(zhuān)注地瞅著河里漂著的每一根草木,還時(shí)不時(shí)地往里放槍。
“打槍?zhuān)俊蔽艺f(shuō)。
“是啊,打槍。”廖三說(shuō)。
“打什么?”我說(shuō)。
“打蘆葦。”廖三說(shuō)。
“蘆葦有什么好打的?”我說(shuō)。
“起初大家還以為警察在開(kāi)槍打護(hù)城河里的魚(yú),那年月護(hù)城河里魚(yú)多,個(gè)頭也大。后來(lái)才明白,年輕男子跳泉后逼得警察們天天瞎折騰。”廖三說(shuō)。
“怎么瞎折騰?”我說(shuō)。
廖三說(shuō)只要發(fā)現(xiàn)護(hù)城河里有蘆葦奔跑,就有子彈打過(guò)來(lái),槍聲叭溝兒叭溝兒的,弄得整個(gè)濟(jì)南像過(guò)年放鞭炮。后來(lái),有人知道了內(nèi)情,說(shuō)年輕男子嘴里含著一根蘆葦跳的泉,有那根蘆葦他就能從水下跑掉。
廖三很會(huì)講故事,講到這個(gè)橋段的時(shí)候卻有些一般了,根本沒(méi)有吸引力,而且也沒(méi)了剛講時(shí)繪聲繪色的情緒。我逗他說(shuō),廖叔,講累了?他抽幾口煙袋,說(shuō)永遠(yuǎn)講不累,想起這事心里就有壓力。我再逗他說(shuō),你壓什么力?故事里的年輕男子和受刑姑娘與你沒(méi)有半點(diǎn)兒關(guān)系。他又狠抽了幾口煙袋,說(shuō)別打岔好不好?
廖三說(shuō)當(dāng)年濟(jì)南許多泉子都通護(hù)城河,練過(guò)水下功夫的人很多,但能嘴含一根蘆葦在水下行走的,卻不多。所以,大家都說(shuō)那個(gè)年輕男子很厲害。
“幾十米啊!知道嗎?”廖三有些激動(dòng),“水下幾十米與路上幾十米,可是完全不一樣啊!”廖三生怕我不懂,說(shuō)改天找個(gè)有這功夫的人給你說(shuō)說(shuō),北園上馬家的馬小叼,說(shuō)是早年跟著燕子李三的師傅學(xué)過(guò),水下功夫那叫一個(gè)了得,從大明湖走進(jìn)護(hù)城河,又沿著護(hù)城河走出好大一截,路上的人根本發(fā)現(xiàn)不了,晚上水下更是他的舞臺(tái),護(hù)城河邊上無(wú)論有多少人,都發(fā)現(xiàn)不了他在水下走動(dòng)。
“有水下走動(dòng)功夫的人,嘴里含的蘆葦是特制的,據(jù)說(shuō)得有兩個(gè)頭通出水面,一個(gè)頭只能出氣,不能進(jìn)氣。當(dāng)然,具體俺也說(shuō)不清,只是聽(tīng)人家說(shuō)過(guò)而已。”廖三這樣說(shuō)的時(shí)候,還專(zhuān)門(mén)講了馬小叼水下偷女人的故事。說(shuō)是有一幫人收了錢(qián)財(cái),要幫人家把一大戶家的女人弄走,結(jié)果大戶家壁壘森嚴(yán),光保鏢百十個(gè),無(wú)法下手。于是,那幫人找到馬小叼,給了他一大筆錢(qián),他竟然真把女人從水下弄出來(lái)了。
這事聽(tīng)著有些懸,我說(shuō)會(huì)水下功夫的人能在水下走,不會(huì)水下功夫的女人怎么從水下弄走?廖三說(shuō)只知道馬小叼干過(guò)這回事,怎么干的不清楚。他說(shuō)馬小叼比他大六七歲,曾在一起喝過(guò)酒,酒桌上有人問(wèn)起,馬小叼說(shuō)讓女人嘴里也含根蘆葦,他在水下拉著女人走。大家都不信,馬小叼就有些急,說(shuō)一只手在水下抓著女人的一個(gè)奶子,那女人很老實(shí)地跟著他在水下走了差不多有三十米,結(jié)果他得了一大筆錢(qián),半輩子都吃香的喝辣的。我說(shuō)的是夏天吧?廖三說(shuō)當(dāng)然是夏天,冬天護(hù)城河結(jié)了冰,誰(shuí)也沒(méi)本事跑到水下去!
東流水街上店鋪很多,人也很多。
雖然那年月很封建,但流火的七月人們依然耐不住熱,與年輕男子一同走著的姑娘們穿著好看的旗袍。他們走著,離那幢后來(lái)傳說(shuō)有共產(chǎn)黨大官居住的二層小樓不遠(yuǎn)。年輕男子回頭沖姑娘笑笑,姑娘的臉一下羞得通紅。于是,年輕男子再?zèng)_她笑,姑娘便有意走慢了半步。年輕男子回頭的當(dāng)口,突然發(fā)現(xiàn)有幾名警察正沖一個(gè)穿大褂戴禮帽的人包圍過(guò)去。年輕男子輕喊了一聲:“不好!”隨即從懷里掏出一支很小的手槍?zhuān)瑳_警察“啪啪”開(kāi)了兩槍。
槍聲驚著的警察,他們立馬沖著槍聲奔了過(guò)來(lái)。年輕男子則箭步如飛,沒(méi)等警察們靠近,人已飛也似的沖到洗心泉邊。他回頭望了一眼,見(jiàn)警察們又沖他包圍了過(guò)來(lái),便很輕蔑地笑了笑,一下躍入泉中。而跟在他旁邊的姑娘,卻嚇得目瞪口呆。有警察圍住了她,也有警察朝年輕男子躍入的洗心泉追去。于是,警察的槍響了,咕咕嚕嚕一陣猛放,子彈到處亂飛,整個(gè)東流水街都被嚇著了,年輕男子影兒也沒(méi)有,穿旗袍的姑娘卻被當(dāng)作同伙抓進(jìn)了局子。后來(lái)知道,年輕男子在水下跑了,他有嘴含一根蘆葦在水下行走的功夫。
“再審,不信她不招!”
“她像真的不知情……”
“她是你家親戚?”
“不是,不是……”
那個(gè)年代的濟(jì)南警察局的確有些破舊了,在太平歲月里,看上去卻像剛剛被炮彈轟過(guò),有幾處院墻已經(jīng)倒塌,卻一直沒(méi)有整修,就那么塌著。即便如此,普通百姓也沒(méi)多少人去到那里——有時(shí)候,人們望著幾處倒塌的院墻,突然莫名其妙地沒(méi)了安全感。當(dāng)然,小人物的生活大多與警察局無(wú)關(guān),但與安全有關(guān)。姑娘也是小人物,卻因那個(gè)年輕男子與警察局發(fā)生了關(guān)系。
在局子里,姑娘被審得死去活來(lái),也被打得遍體鱗傷。更甚時(shí),幾個(gè)彪形大漢站在她旁邊,隨時(shí)發(fā)起攻擊的樣子。于是,姑娘害怕了,渾身打著哆嗦,卻什么話也說(shuō)不出。警察頭目還是不相信她不知情,訓(xùn)過(guò)負(fù)責(zé)審訊的警察,真的就令彪形大漢們輪流對(duì)姑娘進(jìn)行侮辱,彪形大漢還沒(méi)上手,姑娘撕裂的叫聲已在局子里回蕩了。于是,局長(zhǎng)兒追問(wèn):“抓了個(gè)什么人?”警察頭目答:“女共匪,在審!”局長(zhǎng)再追問(wèn):“審得咋樣了?”警察頭目又答:“不招,想要大漢們侍候!”局長(zhǎng)瞪了一下眼:“混蛋!那些漢子,三幾下就能把人弄死,人死了還招個(gè) !”于是,警察頭目哈了一下腰,說(shuō):“是哩,是哩。”
即便是那個(gè)年代,沒(méi)有真憑實(shí)據(jù)抓了人也得放。姑娘被關(guān)了三個(gè)月,受盡侮辱,警察局幾乎查了她的祖孫三代,發(fā)現(xiàn)她與共產(chǎn)黨沒(méi)有絲毫聯(lián)系,僅僅是那天與那個(gè)被懷疑為共產(chǎn)黨人的年輕男子走在了一起。因此,她拖著一個(gè)傷殘的身子被放了出來(lái)。
“子寒,子寒……都怪我……怪我哩……”
年輕男子在外地呆了很長(zhǎng)時(shí)間,又喬裝打扮回到濟(jì)南。回到濟(jì)南的第一件事,是跑去抱著姑娘大哭。結(jié)果姑娘不待見(jiàn)他,一遍遍攆他走,任由他涕淚漣漣,姑娘滿臉冷漠。
“你還是走吧!”呂子寒瞥了一眼許葦,“咱們僅僅是同學(xué),今后不會(huì)再有任何關(guān)系,你……再也別來(lái)了!”
“子寒,子寒……”
“走!你走……”
姑娘眼淚嘩啦啦流著,突然大聲吼叫起來(lái)。
“這個(gè)故事再往下講,可能俺也得哭了。”廖三說(shuō),“你不知道,那姑娘受到非人的折磨。”
“能說(shuō)具體些嗎?你說(shuō)具體了,我寫(xiě)起來(lái)生動(dòng)。”我說(shuō)。
“反正,不僅僅是用電針刺她奶頭的事。”廖三眼眶里真的閃出淚光,“更邪乎的沒(méi)法對(duì)你說(shuō),知道日本鬼子在東北折磨過(guò)趙一曼嗎?那個(gè)年代濟(jì)南的警察,折磨呂子寒一點(diǎn)兒也不比日本鬼子差。”
“呂子寒是共產(chǎn)黨?”我說(shuō)。
“那年月整個(gè)濟(jì)南也沒(méi)幾個(gè)共產(chǎn)黨,她就一年輕姑娘,至多十七八歲,人長(zhǎng)得漂亮,和許葦是學(xué)堂里的同學(xué),共產(chǎn)黨是咋回事估計(jì)都不知道,卻為共產(chǎn)黨遭了一次罪!”廖三嘆出一口氣,像是極度悲傷。然后,他一口接一口地抽煙袋,好半天不再說(shuō)話。
“不講了,再也不講了。”廖三突然說(shuō),“都過(guò)去這么多年,俺怎么給你無(wú)休止地講這個(gè)呢?講這事好玩,還是能掙錢(qián)?”
廖三小時(shí)候讀過(guò)私塾,喜歡咬文嚼字,他說(shuō)了一個(gè)“無(wú)休止”,讓我感覺(jué)有點(diǎn)兒無(wú)厘頭,便問(wèn)怎么會(huì)這樣想?他說(shuō)沒(méi)怎么,就是愿意這樣想。廖三像一個(gè)潑皮無(wú)賴,突然有點(diǎn)兒不講理了。于是,我刺激了一下他,說(shuō):“廖三,從今往后,我繼續(xù)喊你廖三,再也不喊你廖叔。”他說(shuō):“為啥?俺比你大著四十歲呢?”我說(shuō):“大一百歲也不再喊你叔,因?yàn)椤悴皇鞘澹 ?/p>
廖三郁悶了,半個(gè)多月沒(méi)再講述年輕男子的故事,即使我有意刺激他,他也不再接招兒。那些天,我三番五次往“石寶齋”跑,他不再泡茶,見(jiàn)了我和沒(méi)見(jiàn)著一樣,甚至連個(gè)招呼也不打。我說(shuō)他不夠朋友,他搖搖頭,望著我像不認(rèn)識(shí)似的。又過(guò)了幾天,他突然打來(lái)電話,說(shuō)咱們繼續(xù)講那故事?我說(shuō)你有病?他說(shuō)沒(méi)病,俺這么大年紀(jì)能有什么病?我說(shuō)神經(jīng)病,前些天說(shuō)不講了,怎么今天又要講?他說(shuō)前些天是前些天,今天是今天,你過(guò)來(lái),聽(tīng)俺把故事講完,講完了俺就消停了。
再到“石寶齋”時(shí),廖三笑模笑樣地看著我說(shuō),來(lái)了?我說(shuō)你講了半截就想撂挑子,讓我寫(xiě)出來(lái)的故事有頭無(wú)尾?他笑笑,說(shuō)先喝茶,然后俺接著講。于是,我們喝著他泡的一壺龍井,聽(tīng)他繼續(xù)往下講。沒(méi)想到,剛剛還笑模笑樣的廖三,講著講著又流下了眼淚。他第一次罵咧咧地說(shuō):“奶奶個(gè)熊!都過(guò)去這么多年了,重新拾起來(lái)心里咋還扎針一樣疼?”
4
“說(shuō)什么?你要娶誰(shuí)?”
“就那姑娘,她是個(gè)好姑娘!”
“好姑娘也不能你說(shuō)娶就娶?總得有點(diǎn)兒規(guī)矩吧?”
“這事我說(shuō)了算,至于儀式不儀式,你們不用管。”
“放肆!”
“不是放肆,是婚姻自主!”
……
父親與兒子在吵架,越吵越厲害。一把茶壺從室內(nèi)被摔到室外,隨著噼里啪啦的一陣響聲,父親吼罵起來(lái),兒子先是聽(tīng)著父親的吼罵,而后逃之夭夭。
“一點(diǎn)兒家規(guī)也沒(méi)有?瘋了哩!”
“再和他說(shuō)說(shuō),別發(fā)這么大火……”
“都是你慣的,這么大的人,娶妻竟然不聽(tīng)父母的!”
兒子逃了,父親更加氣急敗壞,但一點(diǎn)兒用也沒(méi)有,只能沖著自己的老婆撒氣。
幾日后,兒子突然在一家報(bào)館登出一則婚姻告示,內(nèi)容如下:
本人與呂子寒女士情投意合,即日起結(jié)成夫妻,萬(wàn)望家人與親友周知,特告。
許 葦
民國(guó)一十六年八月八日
“他還是兒子嗎?他是俺爹,俺是他兒子哩!”父親手里拿著報(bào)紙,看了一遍兒子的婚姻告示,氣得發(fā)瘋。之后,老人家撲通躺在地上,嘴里吐著白沫,像是不省人事。再之后,老人家臥床很長(zhǎng)時(shí)間……
廖三繼續(xù)講述這個(gè)故事時(shí),承認(rèn)了一個(gè)事實(shí):故事里的父子倆,一個(gè)是他父親,一個(gè)他大哥。我說(shuō)他講來(lái)講去是在痛說(shuō)革命家史,他說(shuō)所以才講講停停,因沒(méi)辦法一口氣講完,講到傷心處幾天幾夜吃不好睡不安,仿佛看到父親和大哥期待的目光,期待著他來(lái)拯救這個(gè)家。
“俺咋有那能力?”廖三又抽了幾口煙袋,“這么多年了,有些東西根本講不清,記憶力差是一回事,還有些屬于家丑不能外揚(yáng)。”
廖三還真就吊起了我的胃口。突然聽(tīng)說(shuō)上世紀(jì)二三十年代他們家出過(guò)共產(chǎn)黨人,頗感新鮮。便不再顧忌,問(wèn)他接下來(lái)還發(fā)生了什么。他說(shuō)發(fā)生了,要不這個(gè)故事也就沒(méi)有結(jié)尾了。當(dāng)然,有些事俺也編了編,但不會(huì)有太大出入,只是不想把某些不便透露的事透露出來(lái)。我說(shuō)尊重你的講述,你怎么講我怎么聽(tīng),至于今后寫(xiě)出來(lái)是什么樣子,得按照文章的規(guī)則來(lái)。
廖三說(shuō)父親看了那則婚姻告示,氣瘋了,卻又沒(méi)辦法,因大哥已和那姑娘不知去向。
“關(guān)鍵是嫌丟人,老爹可是東流水街上的頭面人物!”廖三說(shuō)著咳嗽起來(lái),嗓子里好像卡了東西,我遞一杯茶給他,他擺擺手,又喘出一口氣,說(shuō)嗓子里什么也沒(méi)有,想到過(guò)去,想到家人,氣就不夠用了。我說(shuō)那姑娘不是把許葦攆出來(lái)嗎?咋又嫁給他了?廖三說(shuō)想必是大哥做了工作,反正他登報(bào)聲明娶了那姑娘。我問(wèn)目前家里還有什么人?他說(shuō)這么大一個(gè)家就剩下他一八十多歲的老人,不過(guò)能講述一番過(guò)去的家事,對(duì)自己也是一種慰藉,總比一個(gè)人躺在床上想來(lái)想去好得多。
雖然廖三說(shuō)有些事不便透露,但最后還是把一切都講了出來(lái),比如父親不同意大哥許葦娶那姑娘,是因東流水街上的人都知道姑娘被抓進(jìn)過(guò)局子,被人禍害過(guò),還禍害的很厲害。他那樣的家庭,在那個(gè)年代娶進(jìn)這樣一房?jī)合眿D,老爹很沒(méi)臉面。再就是大哥參加的共產(chǎn)黨,老爹不了解是咋回事,只知道當(dāng)局天天追殺共產(chǎn)黨,老爹怕得要死,但又拿大哥沒(méi)辦法。后來(lái),大哥弄出個(gè)結(jié)婚告示,老爹也懷疑共產(chǎn)黨大逆不道,便也在報(bào)上發(fā)一告示,聲明與大哥斷絕父子關(guān)系……
老爹回到家時(shí),太陽(yáng)亮晃晃地在西天掛著。爹像熱著了,滿頭滿臉都是汗,他一下?lián)涞乖诖采希岩患胰藝樦恕V螅贈(zèng)]能起來(lái),阿膠作坊的生意差別人幫忙打理著。
那時(shí)候,護(hù)城河邊上再次聚集起很多警察。有警察舉槍往護(hù)城河里放,叭溝兒叭溝兒的。說(shuō)是東流水街上發(fā)現(xiàn)共產(chǎn)黨的老巢,包圍之后一個(gè)人影兒也沒(méi)有,卻隨著“撲通撲通”的跳水聲,好幾個(gè)共產(chǎn)黨從不遠(yuǎn)處的泉子里跑了。有警察說(shuō)護(hù)城河里又有蘆葦在奔跑,好像水下人的影兒都能看得見(jiàn),但沖里面打了很多槍?zhuān)谷蝗魏畏磻?yīng)也沒(méi)有。
“共產(chǎn)黨功夫真厲害,一根蘆葦含在嘴里,能在水下大步流星地走,槍子兒都打不著。”警察頭目站在城墻上罵罵咧咧,他手下們目不轉(zhuǎn)睛地盯著河中心。護(hù)城河兩邊長(zhǎng)滿了蘆葦,只有中間區(qū)域是清清的流水,警察們瞪大眼睛盯著,看到河中不有露出水面的蘆葦,槍子兒就“叭溝兒”一下打過(guò)去。
“給老子看嚴(yán)點(diǎn)兒,不信共產(chǎn)黨真的能趕上槍子兒跑得快!”警察頭目邊罵,邊指揮著手下亂折騰,卻依然沒(méi)能抓到那個(gè)叫許葦?shù)娜恕>炀珠L(zhǎng)急了,令人把護(hù)城河邊的蘆葦鏟了個(gè)精光。之后,護(hù)城河里再也沒(méi)有一棵蘆葦,光禿禿一片。
5
警察局長(zhǎng)命令手下,從北園路邊的田地中包抄合圍,用手槍逼迫著,終于將許葦幾個(gè)人逮捕了。那一刻,許葦?shù)匾恍Γ只仡^望了一眼上峰,上峰也是個(gè)戴著眼鏡的年輕人。見(jiàn)許葦在笑,上峰也在笑。這時(shí)候,一把手槍頂在上峰的腰上……
濟(jì)南緯八路附近有家不太出名的醫(yī)院,許葦和他的上峰——共產(chǎn)黨山東區(qū)的一位鄧姓重要領(lǐng)導(dǎo),被捕后沒(méi)多久就被送到這里住院。他們受刑太重,已是遍體鱗傷。鄧姓領(lǐng)導(dǎo)和許葦都略顯清瘦,但在他們身上彌漫著的是脫俗的文人氣質(zhì)和共產(chǎn)黨人的冷峻。他們無(wú)論出現(xiàn)在任何地方,都能很快在眾多人中看出有別于他人的獨(dú)特風(fēng)度。因此,韓復(fù)榘認(rèn)定所捕獲的幾個(gè)重要人物不能久留。他怕夜長(zhǎng)夢(mèng)多,加之鄧姓領(lǐng)導(dǎo)一身智慧,即便是在森嚴(yán)壁壘的監(jiān)獄里也能組織起越獄行動(dòng),竟然差一點(diǎn)兒越獄成功。
被稱之為泉城的濟(jì)南,其春天十分別致,護(hù)城河上雖然沒(méi)了蘆葦,卻有嘎嘎叫著的水鴨子。太陽(yáng)出來(lái)的時(shí)候,成群結(jié)隊(duì)的水鴨子在護(hù)城河里暢游,有水鴨子叼住一條魚(yú),其他水鴨子瘋狂地追逐,嘎嘎叫聲響成一片,春天的姿色也就在水鴨子的叫聲里展現(xiàn)得燦爛無(wú)比。
有資料顯示,鄧姓重要領(lǐng)導(dǎo)曾代表濟(jì)南共產(chǎn)主義小組赴上海出席過(guò)共產(chǎn)黨的一大,還先后領(lǐng)導(dǎo)過(guò)膠濟(jì)鐵路工人大罷工和青島工人大罷工。據(jù)說(shuō)韓復(fù)榘曾想親自審問(wèn),后因其他緣由,只到監(jiān)獄里看了看。正是他的這一看,幾天后緯八路刑場(chǎng)就響起恐怖的槍聲,鄧姓領(lǐng)導(dǎo)和許葦?shù)?2名共產(chǎn)黨人慘遭殺害……
“大哥赴死是預(yù)料中的事,爹早說(shuō)過(guò),他不講規(guī)矩,得惹大禍。”
“俺弟兄三個(gè),二哥得天花早夭,大哥有才,卻也只活了二十幾歲……”
廖三再一次講述許葦?shù)墓适聲r(shí),臉上已經(jīng)沒(méi)了傷感。他說(shuō)老爹臥床后依然掛著大哥,雖登報(bào)聲明斷絕了父子關(guān)系,可十指連心,天下父母什么時(shí)候都念著親骨肉。
“廖叔,有一事不明白?”廖三露出詫異的目光,“你姓廖,你大哥咋姓許?”
“年代不一樣,有些事你們年輕人想都想不到,早年共產(chǎn)黨哪個(gè)是真名?”廖三抽了一口煙袋,“俺大哥要是不用假名,怕是早被韓復(fù)榘給叭溝兒了,根本等不到與那鄧姓領(lǐng)導(dǎo)一起挨槍子兒。”
“聽(tīng)到大哥被槍斃的消息,難過(guò)吧?”我問(wèn)了一句天大的廢話,廖三卻給了一個(gè)異樣的回答,他說(shuō)家里人也沒(méi)多難過(guò),“四·一二”后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山東共產(chǎn)黨組織接連遭受破壞,父親早已把這個(gè)結(jié)果告訴過(guò)家人,但有兩件沒(méi)預(yù)料到的事還是發(fā)生了。第一件事是大哥被處決的那天傍晚,父親咽下了最后一口氣;第二件事是父親的葬禮剛過(guò),一個(gè)女人抱著一個(gè)半歲大的男孩闖了他們家。
“那個(gè)女人是誰(shuí)?”我說(shuō)。
“還能是誰(shuí)?”廖三說(shuō)。
“那個(gè)姑娘,你大哥的媳婦?”我說(shuō)。
廖三又抽了幾口煙袋,抽得很用力,以至于引發(fā)了好幾分鐘的咳嗽。看他咳得難受,我勸他把煙戒了,他根本不理,慢慢從放玉石的柜子里拿出一個(gè)方盒。方盒外面包了好幾層布,從布的顏色能夠看出已經(jīng)很陳舊。廖三不出聲息,輕輕翻動(dòng)著那幾層陳舊的布。終于,他打開(kāi)了盒子,從里面拿出一張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的照片。
“這就是他們。”我看到了照片上的一對(duì)母子。光陰明顯在這張照片上打下印記,拍攝年代已經(jīng)很久遠(yuǎn),但能看出照片中的母親很年輕,也很漂亮,她穿著旗袍,身材窈窕。襁褓中的小男孩有一雙水靈靈的眼睛,那眼睛像是望著母親,也像是望著這個(gè)世界,母親憂郁的眼神蒙上一層塵埃,一點(diǎn)兒也沒(méi)有穿透力。“只有他們母子的一張照片,至于以后的事,一概不知道。”
廖三的話讓我心生疑問(wèn),他父親葬禮后這對(duì)母子闖進(jìn)他們家,后來(lái)怎么啥都不知道?
“俺家人僅僅看了看他們母子,他們就離開(kāi)了,說(shuō)是被上級(jí)安排去了廣州。”
“完了?”我說(shuō)。
“完了。”廖三說(shuō)。
“結(jié)尾呢?”我說(shuō)。
“照片就是結(jié)尾,往后的事俺不知道,其他人也不知道。”廖三說(shuō)。
……
這好像是個(gè)沒(méi)有結(jié)尾的故事,又好像是個(gè)挺完整的故事。
講過(guò)這個(gè)故事三個(gè)月,廖三突發(fā)心臟病去世,“石寶齋”關(guān)門(mén)大吉。
我很后悔,怎么沒(méi)把照片復(fù)制一張留下來(lái)呢?本想按照廖三的意思將故事記下來(lái),再選個(gè)好的角度在周刊上做個(gè)選題,但周刊要求很?chē)?yán)格,所有選題必須配上能夠說(shuō)明當(dāng)時(shí)時(shí)代背景的照片,否則再好的選題也不能上。無(wú)奈,沒(méi)有照片選題也就沒(méi)做成,我也就沒(méi)把故事記下來(lái)。不久前,突然發(fā)現(xiàn)芙蓉街上原來(lái)的“石寶齋”成了賣(mài)大米面皮的小食店,我又傷感起來(lái)。又想起廖三的無(wú)數(shù)次講述,想起那個(gè)故事中的男人和女人,還有襁褓中的孩子。于是,在一個(gè)沉沉的夜里,我拿起筆,還是把故事一點(diǎn)一點(diǎn)記了下來(lái)。
無(wú)法猜測(cè)故事中的女人以及襁褓中的孩子命運(yùn)如何,但能肯定一點(diǎn),從那個(gè)女人穿著上看得出她熱愛(ài)生活,熱愛(ài)生命,甚至對(duì)生活有著很高的鑒賞水平。至于許葦和鄧姓領(lǐng)導(dǎo)是否如此,則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