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中的父親》王霞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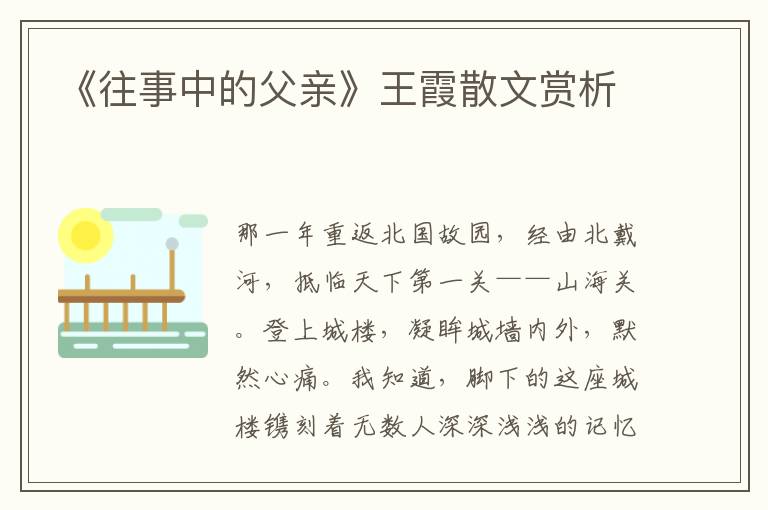
那一年重返北國故園,經由北戴河,抵臨天下第一關——山海關。
登上城樓,凝眸城墻內外,默然心痛。我知道,腳下的這座城樓鐫刻著無數人深深淺淺的記憶。
一腳關里,一腳關外。
一腳祖輩,一腳子孫。
我依稀看到,十來歲的父親,抿緊了嘴角,跟在陌生人的身后,匆匆走過這座關城,沒有回頭,沒有留戀。
多年以后,父親的眼里滿是懷念、渴望,年邁病中,數次蹣跚懵懂地想要走出家門……固執地要回那個土墻茅舍的家,這是怎樣積久成殤的疼痛啊。
父親這樣的,有一個專屬名詞:闖關東。他曾無數次在與徒弟們聊天時,提到這個字眼。彼時,我尚不諳世事。父親亡故,這個字眼也隨之消失。母親年邁,父親成了我們母女永恒的話題。父親的往昔,才結合著我那被喚醒的記憶,一點點清晰起來。
我來到這個世上的時候,父親已經53歲了。之后的歲月,父親只陪伴了我短短的12年。據母親說:父親是個脾氣暴躁的人。然而我的印象中,清癯的父親一直是微微笑著的,以至于我清晰地記得那兩道法令紋。
父親患有高血壓,這個家族的男人少有活過70歲的。我尚小時,父親中過一次風。那一天我放學回家時,父親已經在家里了。他的嘴有些歪斜,說話不清,動作蹣跚。從那一天起,每天晚飯后,都見母親在大鍋里熬中藥。一大鍋,倒在洗澡用的大鐵盆里,里面放一張小凳,然后扶著只身著短褲的父親坐進去,外面用大大的塑料布包起來,只把頭露在外面。父親在熱氣的熏蒸中表情先痛苦而后舒展。等水溫略涼,母親就用藥湯、藥渣替父親擦洗。就這樣,父親在母親的自行調治下,漸漸康復,一切如初。
這樣的幸運并沒有一直伴著我們。父親在66歲那年再一次病倒。這一次正逢唐山大地震。我們雖然遠在淄博,卻也感受到大震的余威。簡陋的地震棚里沒法子熏蒸洗,母親只得依賴醫院延醫用藥,可惜醫院也人滿為患,壓根住不進去。
父親臨終前終于住進了醫院,母親在醫院衣不解帶地照顧他。一個深秋的寒夜,很久沒回家的母親回來了,帶上了我和姐姐,去到了醫院。我看到了搶救室病床上的父親。他已經去了……
1982年的清明,我第一次踏上故鄉的土地,祭奠父親。
我記憶清晰:冀中的鄉村大路是黃澄澄的土路,一陣風兒過,就是一陣煙塵。印象中,路旁的兩排高大的白楊,新葉已經長出了,那種嫩嫩的新綠彰顯著春天不可抗拒的力量。這種新綠嵌入我的眼中、心里,成為故鄉的象征……
對于父親和老家的許多了解都來自于母親斷續的回憶——
父親八歲喪母,自幼學藝,十來歲獨闖關東。做一手好木匠活的他,大方豪氣,掙得多花得快,也一直沒有成家。后來,在撫順做工時,結識了我的舅舅。這個有著精湛手藝的大氣匠人得到了我姥姥的賞識,將母親許配給了他,那年父親已經三十一歲了。母親說,婚后三天回門,等她從娘家返回時,家里很多東西不翼而飛。她以為遭了偷盜,父親才告訴她,那些東西,甚至結婚的被子,都是借的。母親大哭一場,擦干眼淚,收拾殘局。在母親的料理下,這個小家一點一點充實。
傳統型的父親信奉男主外女主內,他把賺來的錢都交給母親安排生活,家里漸漸地有了積蓄。日子好過了,抗日勝利的消息也令人振奮。父親開始謀劃衣錦還鄉,他不顧母親的反對,把家當變賣,買了臺照相機。按父親的籌劃,一路上幫人拍照掙錢,再加上家里的積蓄,足夠回鄉買塊地了,從此就可以在故土過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穩日子了。可是被回鄉念頭纏繞的父親忽略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彼時還是兵荒馬亂。
母親回憶說,一路上風險迭出。先是照相機被沒收,父親差點被當作間諜抓起來;接著身上的錢被搶劫一空,只有母親塞在襪筒里的一點幸存了下來;還有在過大梁(音)河時,遇到了飛機轟炸,母親抱著哥哥懸在殘存的橋欄桿上,腳下是咆哮的河水……
歷盡風險,一貧如洗地回到了老家,冀中平原上的一個村子。在家的人都用一種蔑視的眼神對待母親,因為在城市長大的她干起農活笨手笨腳。父親也不會干農活。時日不多,要強的父母親苦掙苦熬仍無法維持生計,只得又一次背井離鄉,回到撫順市。
父親的墳不大,周遭都是干枯的酸棗棵子,已經有幾個人在那里砍了。這幾個人都是男性,有青壯的,也有年老的。穿著青黑為主、年紀大的都用白毛巾包著頭,就像地道戰里的鄉親們一樣。嬸娘跟我們一一介紹,這個是哥,那個是叔,全都憨憨地笑著。一個叫蛋兒叔的矮個子老者,拉著我直抹眼淚。嬸娘也擦著眼角的淚花說:你蛋兒叔跟你爸最好,要不是他爹就這一個兒子,他早跟你爸跑了……
祭奠之后,嬸娘帶著我們走訪鄉鄰。聽著那生疏卻親切的鄉音,述說著父輩的記憶……
祖母在父親8歲那年亡故。姑姑之下是兄弟三人,父親居長。
二叔一直在老家,娶妻生子。機智活絡的他是村里的抗日村干。開門是維持會會長,支應糊弄鬼子,關門是村支書,組織鄉親們支援八路軍。解放后,舉家遷到石家莊,不久就因腦溢血去世了。
三叔很小就當了小八路。從參軍,到抗美援朝,一直到解放后轉業回石家莊,他一直在呂正操將軍的麾下。
我們家與三叔一家的關系,在叔叔退役前是很密切的。叔叔的兩張嘉獎令,一張是林彪簽署的,一張是呂正操的親筆,全部鑲裱在鏡框里。林彪墜落蒙古溫都爾汗,嘉獎令不見了,鏡框里換成了我們兄弟姐妹們的各色照片。
父親在世時,最愛嘮叨的就是叔叔立功受獎,部隊把父親接了去參加慶功宴,呂正操將軍親自敬酒。其實,據母親說,接父親到部隊上,并且如此隆重,還有另一層原因,這件事在后來的文革中差點毀了全家。
那還是抗日戰爭中,冀中平原戰火正盛,時有八路軍戰士被俘。這些被俘的戰士統統被日寇押運到東北做勞工挖煤。為了搭救這些人,三叔奉命安排我父親做了警察署長。父親雖然沒什么文化,但是為人豪爽,且自小就在撫順市做工,人脈熟悉。在父親的努力下,救出了不少人。記得母親最常說的是一個姓張的,為了救他,父親把家里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變賣了,連母親唯一一件首飾——一枚鎦金銀戒——也賣了。被救走的人,后來沒一個回來看看的。而父親也從未為此居功,他認為這是幫中國人的忙,是為弟弟辦事,腦子里壓根沒有什么政黨的概念。
父親的倔脾氣是河北人的典型標志,為人耿介的他得罪了不少人。文革時就有人借此事整父親,說他是偽警察署長,是漢奸。父親被抓后,百口莫辯。幸虧部隊、老家地方政府都出面證實,才免于毀家之虞。
在這里應該提到一個略帶傳奇的故事,那也是我們舉家南遷的契機。1974年秋,父親去河南哥哥家探親。家住三樓,一樓住著哥哥的同事。一次,父親下樓乘涼,同事招呼在窗前坐坐。閑聊時,同事的父親在房間里招呼兒子,父親聽到了,站起來就進了他家,哥哥和同事感到納悶,就隨著進去。只見兩位老人面對面站著,互相端量,半天,互相一指:你,是你!
原來,同事的父親就是父親當年搭救出來的抗聯戰士,得救后,他一路東藏西躲,逃回了老家。直到解放后才又參加工作。由于那段說不清的歷史,文革中也被關押了若干年,獲釋后隨兒子落戶到這個中央直屬企業。
兩位老人相對落淚,那段歷史終于可以說清楚了。數日后,父親揣著一紙證言回到了撫順。轉過年,也帶著全家動遷到了洛陽。那位叔叔也姓王,家中最小的女兒長我一歲,我和她在一個學校讀書,成了好朋友,直到現在。
細細回憶,經歷豐富的父親應該是個沒有大志的人。母親說,解放后,父親有過兩次極好的機會進身官場,他都不屑地放棄了。一次,是部隊出面送父親進修學習,因為他文化太低,還給配備了專門的輔導老師。可按父親的話說,是活受罪,弄個小丫頭整天看著。他堅決不干就回來了。第二次,是由于在生產工藝上有了發明創造,單位把父親送去進行技術培訓。這個倒是他樂意的,就去了。結果又是因為文化課學習,觸犯了父親的倔脾氣,結果依舊是不領情地打道回府。他固執地認為,工人憑手藝吃飯,文化有什么用。對于母親積極參加街道的掃盲班學習,父親是極為不屑的。
所以,一直到退休,到離世,父親都只是一個大字不識的普通工人。他的身份就是八級木工,是我們兄妹五人的父親。而在我的心中,全然沒有母親、嬸娘、兄姊以及回鄉時鄉親們所說的倔強、暴躁、嚴厲、不羈,他留給我的是寵溺、微笑,永遠利落的衣著,以及精湛的手藝……
(作者單位:江蘇省南京市棲霞區堯化門區實驗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