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艷梅《總是人間苦,一醉解千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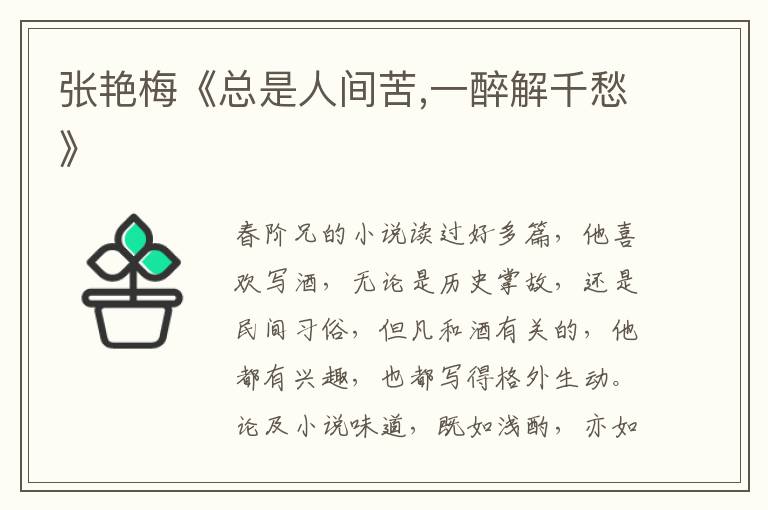
春階兄的小說讀過好多篇,他喜歡寫酒,無論是歷史掌故,還是民間習(xí)俗,但凡和酒有關(guān)的,他都有興趣,也都寫得格外生動。論及小說味道,既如淺酌,亦如暢飲;于小說氣韻,既有微醺的輕盈,也有宿醉的凝重。有人喜歡寫酒場和酒桌文化,其實是借酒寫官場勾心斗角,寫商戰(zhàn)暗藏殺機。春階兄不是,他筆下的酒,熱乎乎地流動在人心里,他寫喝酒,獨斟,對酌,一村人開懷暢飲,都有著對酒的鄭重。酒在春階兄小說中,不是勘察人性的媒介,而是孤獨者的心靈歸宿。
一、離鄉(xiāng)者的倫理糾纏
多年前,第一次讀到春階兄的小說,就是那篇《滿村酒香》,真是頗為驚艷。《滿村酒香》有著沉重的歷史縱深感,這篇《雪夜泥醉》則帶有尖銳的人生悲涼感。對于每一個從鄉(xiāng)村走出來,收入稍微高點,或者有點權(quán)力的人,遠(yuǎn)在老家的七姑六婆、鄉(xiāng)親鄰里,就難免有無數(shù)瑣碎的求助和期待。不斷去照顧和滿足他們的要求,自己會活得非常累;如果一件事不能滿足,就會背上忘本的罪名。“人一闊臉就變”可能并不是背后說說,甚至有時候來自長輩的當(dāng)面教訓(xùn)。親情和鄉(xiāng)情就這樣成為永遠(yuǎn)的生活負(fù)累和道德背負(fù)。
大家族與小家庭的矛盾是小說中的一條重要線索。這個矛盾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社會基本結(jié)構(gòu)有關(guān)。傳統(tǒng)宗法社會民間信奉的就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近代以來,中國城鄉(xiāng)之間流動性不斷增加,尤其是198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高等教育擴招,越來越多的鄉(xiāng)村人口進(jìn)入城市,讀書就業(yè),安家落戶,其中一部分人事業(yè)有成,有了一定社會地位,成為整個家族的支撐。
逄春階小說《雪夜泥醉》中主人公景之就是這一群體中的一員,人到中年,面對內(nèi)憂外困,心力交瘁。妻子的嘮叨指責(zé),老家人的生死變故,讓他大年夜寧愿在街頭游蕩,也不愿意回家。既不愿意回老家面對親人不停的追問和求乞的目光,也不愿意回到小家聽妻子各種說教。小說順序記述了一連串的生活瑣事。老家的大舅、小舅、小姨、哥哥、表弟、姐姐各種缺錢、病痛、打官司和意外事故,都等待他伸出援手。生活本已艱難,再加上人心涼薄,更讓人倍覺人世凄惶。妻子對錢和人都管得很緊,不喜歡老家人來打擾,經(jīng)常冷臉相對甚至惡語相加。也不是沒有渴望,一家人團聚,沒有懷疑,沒有指責(zé),吃著老娘包的熱騰騰的水餃,聊聊天,敘敘舊,可惜因為沒有足夠的金錢和權(quán)力幫助所有親戚解決問題,景之選擇了逃避,懷著不安、后悔、疑慮、孤獨和傷感,一個人在大年夜,在大風(fēng)雪里,在異鄉(xiāng)的城市,孤獨徘徊。小說至此,寫出了城鄉(xiāng)之間那顆無處安放的靈魂。
二、鄉(xiāng)村價值觀念的變遷
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三十年,鄉(xiāng)村和城市都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于鄉(xiāng)村而言,一方面,凝滯不動的小農(nóng)意識和文化惰性依然如故;另一方面,新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形態(tài)帶來了價值觀的嚴(yán)重混亂。當(dāng)下鄉(xiāng)村的物化傾向嚴(yán)重,逄春階在小說中借助不同人物之口反復(fù)說:老家是只認(rèn)錢不認(rèn)人了。親情異化,鄉(xiāng)情淡薄,有家難回,有鄉(xiāng)難奔,甚至害怕老家的人總是給自己找麻煩,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發(fā)達(dá)與忘本,就像一對孿生兄弟,折磨著離鄉(xiāng)者脆弱的情感,也折磨著絕望中掙扎的鄉(xiāng)親。
小說中寫到了很多細(xì)節(jié),買了牛,表弟媳婦不領(lǐng)情,二姑病了,還要景之出錢,真是里外不是人。大哥喜歡顯擺吹牛,要求景之幫忙找人升官,對于景之從電視臺工商部調(diào)到文藝部非常惱火。小姨因為被計生辦抓錯打掉了牙齒,一直索賠不成,無處申訴,小心翼翼討好景之期待他能幫忙討回公道,可是景之同樣無能為力。表弟車禍,小舅車禍,舅媽死了,小舅讓景之幫忙索要舅媽的賠償費。小說渲染了一個無聲的黑白雪夜,對照紅色的春聯(lián),炸裂的鞭炮,記憶里故鄉(xiāng)小路上所有時光的色彩,只剩下大舅車禍后地上的那一攤血跡。
一百年前,魯迅寫故鄉(xiāng),小說中的鄉(xiāng)土中國包含著眼前蕭索的村莊,小說敘事人仍舊對鄉(xiāng)村改造懷有期望和信心。那么,什么時候,故鄉(xiāng)不知不覺已經(jīng)完全變成了異鄉(xiāng)呢?三四十年代,沈從文、巴金等人寫下了知識分子漫長的精神還鄉(xiāng)道路。新時期以來,鄉(xiāng)土小說中的故鄉(xiāng)依舊保持著兩種形態(tài),精神的理想國和現(xiàn)實的烏托邦。逄春階筆下的故鄉(xiāng)已經(jīng)面目全非,從外到內(nèi)完全是異鄉(xiāng)。不僅僅是外在的變化,樹都砍光了,路也拓寬了;更主要是內(nèi)在的變化,是倫理秩序和價值觀的變化。從鄉(xiāng)村走出去的知識分子背負(fù)著故鄉(xiāng)的沉重親情債務(wù),并沒有改造鄉(xiāng)村的任何能力和愿望,與故鄉(xiāng)的隔膜愈來愈根深蒂固,甚至寧可大年夜浪跡在異鄉(xiāng)街頭的大風(fēng)雪中,也不愿、不敢回鄉(xiāng)。知識分子敗給鄉(xiāng)村現(xiàn)實,情感的力量遠(yuǎn)遠(yuǎn)不及金錢實利。金錢權(quán)勢對人心的腐蝕非常可怕,古風(fēng)醇厚的鄉(xiāng)土倫理秩序已經(jīng)蕩然無存,情感共同體也失去了依托。知識分子并沒有道德上的優(yōu)越感,文藝部也無法成為精神樂土,無非是不想被金錢左右。現(xiàn)實生活中做不到游刃有余,不得不面對鄉(xiāng)村倫理缺位、自身進(jìn)退兩難的困境。
三、底層人生的辛酸
底層是近些年作家們集中觀照的對象,底層文學(xué)熱有著復(fù)雜的社會背景和現(xiàn)實訴求。鄉(xiāng)村問題很多,城鎮(zhèn)化這一藥方并不能夠包治百病。《雪夜泥醉》中,老同學(xué)因為包工頭跑了,拿不到工錢向景之求助。看門的老趙頭與一群流浪貓為伴,差點在大年夜死于火災(zāi)。吉祥酒館的夫妻兩個因為一條炸魚怒目相對大放悲聲。夫妻倆開飯館小本生意慘淡經(jīng)營,一年到頭掙不了幾個錢,回老家過年成為巨大的負(fù)擔(dān),做個小生意又被工商勒索。一盤花生,一盤木耳,一盤芹菜炒肉,一瓶白酒,吉祥和景之兩個人喝得感慨萬千。回憶里有著童年的快樂,看著眼前各自的生活,兩個人無限傷感。說起不回老家的原因,都是因為各種沉重的親情索取,讓回鄉(xiāng)之路變得無比心酸和艱辛。一條掉進(jìn)爐灰里的炸魚,就像生活的希望,不能說沒有,卻又被太多塵埃湮沒遍體鱗傷。對于吉祥夫婦這樣的普通人,真的只是生存就已經(jīng)拼盡全力。寂靜而又熱鬧的大年夜里,吉祥妻子無法抑制的哭聲,讓平凡人生顯現(xiàn)出千瘡百孔的真相。
小說末尾,黑漆漆的夜,一群饑餓的流浪貓,半袋子帶著皮帶著土來自家鄉(xiāng)的花生,景之和工地上看門的老趙頭喝到爛醉如泥。老趙頭搓下花生殼上的干土送進(jìn)嘴里,就像吃藥一樣,用一口酒送了下去。這是怎樣的一種情感啊,老趙頭眼里的淚,就這樣一滴一滴滑落滿是皺紋和灰塵的臉,一直流進(jìn)讀者心里。多少人就像一塊泥土,只是已經(jīng)離開了家鄉(xiāng)的大地,流浪的泥土,在城市中漂泊輾轉(zhuǎn),最終成為被厭棄的塵埃。一把故鄉(xiāng)的土,就像一味藥,卻無法真的慰藉內(nèi)心的孤獨和兩難。
小說結(jié)尾寫道:“門外,鞭炮聲開始炸響,整座城市炮火連天,煙火彌漫。”兩個爛醉如泥的異鄉(xiāng)人,定格在這個舊年夜背景下。酒,給沉重的日常生活帶來片刻的輕盈;夜色,覆蓋了回家的路和無路可走的孤獨者。逄春階沒有刻意渲染人世艱難,也不回避生活悲苦,他寫出了我們每一個站在回鄉(xiāng)路口的人滿臉的憂戚之色。表面上,我們活得很熱鬧;夜深人靜時,我們的心四分五裂流離失所,這篇小說,給我的不只是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