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叔河《末世官僚地主魂》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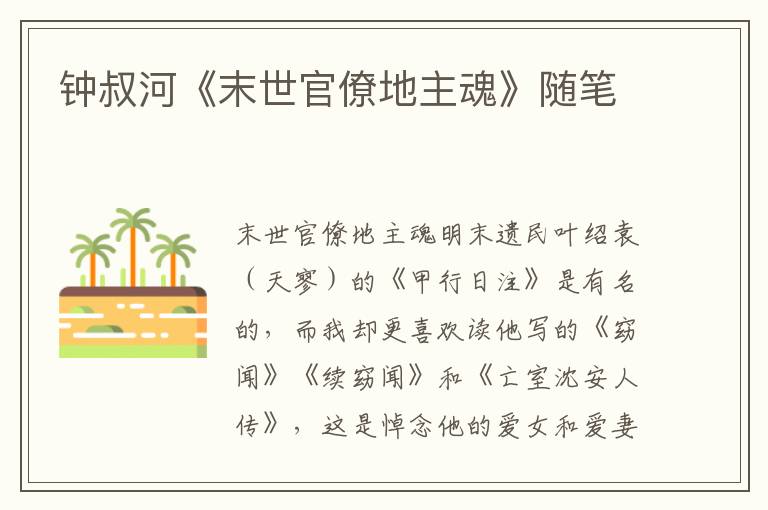
末世官僚地主魂
明末遺民葉紹袁(天寥)的《甲行日注》是有名的,而我卻更喜歡讀他寫的《窈聞》《續窈聞》和《亡室沈安人傳》,這是悼念他的愛女和愛妻的一組文章。
《甲行日注》所表現的是國恨,這幾篇文章抒發的則是家愁。自古才人,每多不幸,此固由于他們的神經纖維本來脆弱,易于感傷,亦因有理想主義氣質的人,每易和現實脫節,所以窮愁潦倒、別恨離愁就容易和他們結下不解之緣,而文思才情亦往往因此陶鑄而出,則不幸也者,實亦可謂為他們的(也許更應該說是我們的)幸運了。
不同境界的人,自有不同的幸福觀。《亡室沈安人傳》寫道:
自賦歸來,僅征藉數畝之入,君或典釵枇佐之。入既甚罕,典更幾何,日且益罄,則挑燈夜坐,共誦鮑明遠《愁苦行》,以為笑樂。諸子大者論文,小者讀杜少陵詩,瑯瑯可聽,兩女時以韻語作問遺……君語我曰:慎勿憂貧,世間福已享盡,暫將貧字與造化藉手作缺陷耳。
這樣的夫妻生活,恐怕只有李清照《金石錄后序》中所寫的才可以相比,在古代文人社會里要算是絕無僅有的了。
然而“造化”卻不讓他們這樣過下去,葉紹袁接下去就寫道:“昊天不傭,瓊章首殞。浸尋三載,家禍頻仍,君亦隨以身殉之。嗟乎,安得宛君而更與我語貧也,豈不悲哉。”這樣,葉紹袁在國破之前,即已家亡,所以他后來逃佛遁世,寫《甲行日注》,早有了“思想基礎”。
我一直看重晚明人的文章,因為在專制倒臺、傳統崩壞的時代,才容得一點思想的自由和個性的表露,這也就是“亡國之音”往往比較動人的原因。黑格爾不云乎:“智慧之鳥的貓頭鷹,只有在文明的暮色中才開始起飛。”如晚明者,豈非古代漢族士大夫文明“暮色”籠罩的時代乎?但留得幾首好文章,此時代亦即值得后人紀念,我們本不是鳳陽朱的家奴,大可不必為改朝換代而痛心疾首于三百年之后也。
大凡真能愛國家,愛民族,真能為國家民族作出一點犧牲,而不是專門講大話唱高調的人,于家庭骨肉之間,亦必有真感情,真愛心。我不相信刻薄寡恩的人,能夠有民胞物與的胸懷,有對國家民族的真正責任感。“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這兩句詩,驗之于亡國之后毅然舍幼子田廬作“甲行”的葉紹袁,也是不錯的。
為懷念亡女亡妻而寫的《窈聞》《續窈聞》,所記“走陰差”和“扶乩”,當然都是迷信。寫得出如此清詞麗句的人,未必竟像普通的愚夫愚婦。葉氏不云乎:“余賦性迂直,不敢欺人,亦不祈人信以為真有;雖群口交羨,無救我女之亡。”但沈安人卻似乎相信女兒確已仙去,她在《季女瓊章傳》中寫道:
初見兒之死也,驚悼不知所出,肝腸裂盡,血淚成枯。
后徐思之,兒豈凡骨,若非瑤島玉女,必靈鷲之侍者,應是再來人,豈能久居塵世耶?……嗚呼,愛女一死,痛腸難盡,淚眼追思,實實寫出,豈效才人作小說欺世邪?
迷信是精神的鴉片,靠麻醉以逃痛苦是可悲的,明知麻醉不能真解脫而亦不得不暫求麻醉就更可悲了。這一對并不怎么追求物質享受,只要有一點能使他們自得其樂的精神生活,便會覺得“世間福已享盡”的文人夫婦,逃仙逃佛,終不免家破人亡。三百年后的我們,讀其文,想其人,仍不禁對他們產生某種同情之感。聶紺弩詩云:“從來紅粉青衫淚,末世官僚地主魂。”其實,真正當官帶兵有田有銀的官僚地主,死了老婆還有他的小老婆,換了朝代還可以著他的“兩朝領袖”,他們是不會來寫什么《亡室沈安人傳》,更不會肯出家寫《甲行日注》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