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琇榮《一粒水紅色革命種子的燃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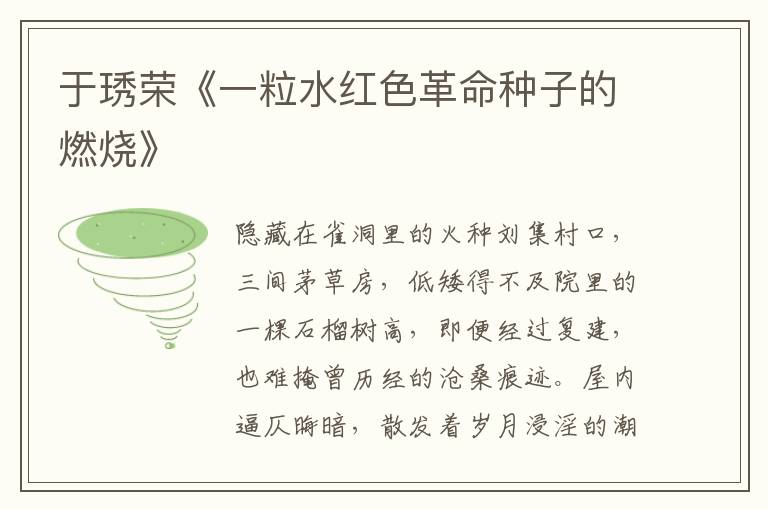
隱藏在雀洞里的火種
劉集村口,三間茅草房,低矮得不及院里的一棵石榴樹高,即便經過復建,也難掩曾歷經的滄桑痕跡。屋內逼仄晦暗,散發著歲月浸淫的潮涼。屋門右邊,四塊青磚呈“井”字形嵌在山墻里。那是雀洞。我很是詫異,劉世厚——一個仁慈到為鳥雀筑巢的農民,是如何在血腥屠殺中舉起了反擊的拳頭,并歷經動蕩混亂風雨飄搖的43年,將中國第一版《共產黨宣言》譯本保存至今。而那山墻雀洞,正是主要藏匿之處。
我在廣饒博物館見過那本書,平裝本,長18厘米,寬12厘米,比現在的32開本略小一點。書面印有水紅色馬克思半身像,上端從右至左模印著“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上署“馬格斯、安格斯合著”和“陳望道譯”。全文用5號鉛字豎排,計56頁。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初版”“定價大洋一角”字樣,印刷及發行者是“社會主義研究社”。
山東倚山臨海、民心淳樸、經濟富庶,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1914年歐戰爆發,歐洲各國幾乎全部卷入了戰爭,日本逼迫中國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二十一條”,并借機攫奪德國在中國膠州灣的租借地,使山東再次陷入了戰火硝煙之中。1919年,“巴黎和會”無理拒絕了中國代表提出的“廢除二十一條”“收回青島”等合理主張,引起了人民極大憤慨。在進步思想影響下覺醒了的青年學生,發起了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最終促使政府放棄在和談上簽字。自此,馬克思主義思想逐漸在中國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理論和人員基礎。而飽受戰火蹂躪的山東,也注定成為了革命洪流中的漩渦之地。
在這種情況下,1920年初,陳望道受上海《星期評論》編輯李漢俊等人委托,返回烏鎮老家,不分晝夜地依據日文、英文翻譯《共產黨宣言》,把一直在歐洲徘徊的共產主義帶到了中國,催生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一大”在上海召開,由此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1924年,劉子久受黨的一大代表、山東黨委王盡美同志委派,借探親之際,回到家鄉劉集,組織成立了第一個農村黨支部——劉集黨支部。1925年,劉雨輝將《共產黨宣言》帶到劉集,交給當時黨支部書記劉良才,1930年劉良才調任濰縣任縣委書記,將書交給劉考文。1932年,博興暴動失敗,劉考文預感可能被捕,又把這本書交給了共產黨員劉世厚保管。
劉世厚很清楚,接受保管這本書將意味著什么。當時,國民黨在統治區實行文化“圍剿”,頒布法令,把676種社會科學書刊定為“非法”的“禁書”,《共產黨宣言》是禁書之首,如果被發現藏有此書,可能被判處監禁甚至會被處死。但他還是接受了,因為這書里藏著他夢想中的好日子。他精心地用油紙把書嚴實包好,裝進竹筒,埋在了炕鋪下面。
1941年1月18日,日、偽軍1000余人,突然包圍了劉集村。劉世厚知道,此次敵人來者不善,一定會大肆清剿搜查。他忙把埋在炕鋪下面的《共產黨宣言》取出,塞進山墻的雀洞里,用碎泥土塊封住洞口,領著鄉親們逃往村外。
一月的魯北平原,北風凄厲、廣袤蒼涼,陰郁低垂的天空下,一拃長的干枯麥苗,像被抽了筋骨似的倒伏在大地上,遠遠望去,泛著一層虛浮的綠意。幾棵老榆樹散落其間,伸著干枯扭曲的枝椏絕望地在風中舞動,妄圖在空氣中抓到點兒什么,但除了幾聲老鴰不祥的聒噪,終究沒有什么也沒抓到。葦子溝迎著風口,肆虐的北風,呼呼地往溝里灌。村民靜靜地趴在葦子溝里,河溝里的水不深,結了一層薄冰,寒冷的凍土,隔著棉衣涼進了骨頭縫里。 寂靜,可怕的寂靜,大家屏住呼吸一動不動。一切靜謐得像場夢。只有額頭抹不盡的汗和咚咚急促的心跳,在昭示著一場災難正在發生。
透過蘆葦葉的縫隙,刀鋒一樣銳利的眼神盯視著正慘遭涂炭的村莊。忽然,一股濃煙在村落上空升起。火?火!有人發出驚呼。濃煙里,通紅的火苗跳躍著,舔舐著天空,一會兒工夫,整個劉集村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看著火勢越來越猛,劉世厚心急如焚,藏在雀洞里的《共產黨宣言》揪得他坐立不安。他心一橫,不顧他人勸阻,沿著地埂往村里跑去。燃燒的熱浪混著黏膩的血腥味在村巷彌漫,樹下、斷墻邊、院落里橫陳著他熟悉不能再熟悉的鄉鄰的尸體。劉世厚顧不得難過,小心翼翼地躲避著正四處搜尋的鬼子,悄悄地溜回家。家里此時已是破碎不堪一片狼藉,火苗正從屋頂、門洞、窗眼里向外瘋狂亂躥。他急忙撥開雀洞滾燙的泥土封口,直到摸到完好的竹筒,他緊繃的心才一下子舒緩下來。
他把竹筒揣進懷里,忍著大火的炙烤,蹲在墻角躲藏了起來。
遠遠地,他聽到一個人從墻外巷子里慌亂地跑過去,緊跟著,一陣嚎叫混著雜亂的腳步聲追了過來,隨后一陣槍響。又一個老鄉被槍殺了,劉世厚想。
不知道過去了多久, 雜亂的腳步聲遠了,零星的槍聲也停止了,整個村莊陷入了一片死寂。周遭靜得駭人,世界在這一刻仿佛被扼住了喉嚨。驚恐,在畢畢剝剝的燃燒聲以及房屋轟然倒塌的聲音里漸漸消失,只剩下憤怒和仇恨,在狠狠地撞擊著胸腔。
這次圍剿,釀成了駭人聽聞的“劉集慘案”,80多名村民遇害,500多間房屋被燒,而那本《共產黨宣言》,竟奇跡地保存了下來。
在此后的34年里,劉世厚把這本《共產黨宣言》藏進過屋檐瓦里、封進泥灶頭、糧食囤底下、山墻雀洞,他的生命好像只為這本書而存在,劉考文把書交給他時的諄諄囑托:“記著,人在書在”,劉良才被敵人用鐵釘活活釘死在城墻上的慘狀,讓劉世厚備感肩負的責任重大。
1975年秋,廣饒縣文物所所長顏華得知失蹤多年的《共產黨宣言》在劉世厚手里,便到他家里做動員工作,已84歲高齡的劉世厚老人一袋接一袋地吸著旱煙,就是不說話。顏華說,這是馬列思想在中國的第一本著作,是共產主義的綱領,這么多年,承載著多少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的痕跡,珍貴著呢。老人沉默良久,才把這本珍貴的書從藏匿地取出來,將散亂的頁碼訂好,在首頁的左上角鄭重地蓋上了一枚“劉世厚印”,將它獻給了國家。
走出茅草屋,陽光和煦,劉世厚的半身銅像迎門而立。老人仁厚安詳地微笑著,注視著來訪者行走在蓬勃的“中共劉集支部舊址”,與鳥雀和睦相處。
革命,在血腥的土壤里萌芽
1941年12月20日凌晨,黑漆漆的夜,分外寂靜,一輪鐮刀似的殘月斜掛在山頂。此時,正是睡意酣甜的時候,一片安逸的鼾聲在村莊里虛渺地飄浮著。村長林凡義躺在炕上輾轉反側,不幸的預感攪得他心緒不寧。前幾天,駐扎在小梁家的偽軍來要錢糧,被他堅決拒絕了。敵人不會善不甘休的,林凡義心里知道。忽然,他聽到幾聲狗吠,接著,整個村落里的狗瘋狂地叫了起來,此起彼伏不絕于耳。
鬼子來了。林凡義想著,心里反倒鎮定了下來。
村長林凡義對鄉親們說:“鬼子把咱們包圍了,沖是沖不出去了!咱淵子崖人是有血性的,寧死不當孬種。”村民異口同聲:“寧可站著死,絕不躺著活!”
這是場慘烈的不忍用筆去敘述的戰斗。 1500余名裝備精良的日、偽軍趁著夜色撲向了淵子崖。
淵子崖,位于沭河東岸,據《林氏續立石譜碑》記載:“大明洪武年間(1368——1398年),自新泰來復業,復遷蘭邑東鄉淵子崖村。”因村坐落在一深淵近處故名淵子崖。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為躲避匪盜禍亂,淵子崖沿村筑起了5米多高、1米多厚的圍子墻,墻上修了大小不等的炮樓、炮眼,很是堅固。
敵人開始進攻了,先是用炮轟炸圍墻和村莊,雨點一樣的炮彈砸向城墻。頓時,村子里硝煙彌漫、濃煙滾滾,不時有被炮彈擊中的房屋轟然倒塌成一堆瓦礫。有人從圍墻上的腳手架掉下來犧牲了,鄉親們拉來草苫,含淚為他蓋上。炮彈炸傷了肚子,腸子流出來,再填回去,用破布在腰上一扎,繼續戰斗。圍墻炸開口子,用門板、石塊把缺口壘上。老人、婦女、孩子把燒飯的鐵鍋砸碎,把鐵耙釘砸下來,當作土炮的砂子,青壯年手持幾支簡陋的槍支、鍘刀片與鬼子戰斗。村民林九蘭隱藏在圍墻豁子口旁,鬼子上來一個,他就用鍘刀砍死一個,上來一個,就砍死一個,砍倒第八個鬼子,終因體力不支,被鬼子的刺刀扎進了胸膛,犧牲了。
鬼子進村了,村民們邊打邊撤,用笊鉤、鐵锨、菜刀、鋤頭同敵人展開了更加慘烈的巷戰、肉搏戰。林九乾死了,他妻子怒吼著沖上去,用镢頭將鬼子的腦袋砸開了花,她摟住丈夫的尸體悲痛地號啕大哭,公公林秉標沖了過來,用一捆稻草輕輕蓋在兒子臉上,一把拉起兒媳說:“孩子,這不是哭的時候,站起來和鬼子拼呀!” 有的父子在巷口阻擊敵人,有的母女合力同鬼子廝打在一起。兒子死了,父親上;丈夫死了,妻子上;哥哥用身軀擋住了扎向弟弟的刺刀;姐妹與鬼子撕扯成一團,用牙咬爛鬼子的喉嚨;圍墻上,不斷有人摟著鬼子一起跳下摔死。村子里到處都是慘叫聲、怒罵聲、砍殺聲……
鮮血染紅了村巷、斷墻,染紅了天,街道上、院落里橫七豎八躺著犧牲了的鄉親。終于,附近的八路軍聞訊趕來增援,敵人這才退敗而逃。
夕陽西下,冬日的余暉抽走了人間最后一絲溫暖,像不忍直視這慘烈的人間地獄,用暗夜,一點一點遮蔽起飄蕩在這座英雄村莊上空的悲泣和哀傷。
此次戰役,村民犧牲145人,傷400人。斃傷日偽軍154人。這是一場真正的與敵人玉石俱焚同歸于盡的戰斗啊。
這樣的事在沂蒙老區俯拾皆是,幾乎每戶人家,都有支前模范,每個村莊都有抗日故事。這是一群有著怎樣脊梁的人啊?
當跟隨省作協采風團走進莒縣革命紀念館,我找到了答案:黨的一大代表王盡美分別于1924年和1926年介紹劉子久和宋壽田入黨。劉子久借回家探親之際,組織成立了第一個農村黨支部——劉集黨支部。宋壽田則受省委指示,回到家鄉莒縣開展農民運動,因此,莒縣群眾得以較早地接受到了進步的革命思想教育。
莒縣,人口不足百萬,新中國成立前的老黨員就達13341人。眾所周知,解放前,中華大地戰火紛飛硝煙彌漫,革命前途晦暗未卜,是他(她)們,在黑暗中點亮了曙光,并篤定地堅信光明終將到來,用心中崇高的信仰,堅信!
紀念館玻璃展板內,一張張因時間久遠而泛黃薄脆的入黨申請書上寫滿“蹩腳”的漢字,甚至有錯字、別字,但正是這些字,卻看得我肌膚戰栗,熱血沸騰,禁不住為自己填寫入黨申請書時的狹隘與淺薄而羞愧。
劉太花、入黨動機:為了抗日打鬼子,保家鄉。
董玉勝、入黨動機:為人民服務,不在(再)受壓迫,建設社會主義而奮斗到底。
李經崗、入黨動機:為了反(翻)身解放過好日子,有地位領導人民組織互助組。
“老頭子嫌乎俺成天往外跑哦,說不退黨就離婚,俺就說,寧可離婚,也不退黨。”薛貞翠老人說。
“是黨的人,就要聽黨的話,跟黨走。”86歲還擔任村支書的盧翠秀說。
“入黨為了打鬼子,不打鬼子,沒有家,沒有好日子過。”竺守海老人說。
大銀幕上,耄耋之年的老人提及過往談笑風生,曾經的生死一線在他(她)們眼里早已化作云淡風輕。那一張張溝壑縱橫卻樂觀豁達的笑臉,一句句樸實卻振聾發聵的話語,濡濕了我的眼眶。
蓬勃發展的根據地武裝
烈士陵園,曾是慶云小城里最好的一棟建筑。紅墻碧瓦,廊柱高聳,在蒼松翠柏的掩映下,愈加顯得莊重巍峨,尤其是那幾根爬滿山墻的紫藤,根系粗壯蓬勃,風吹枝葉,會發出一陣又一陣嘩啦啦的聲音,像海浪,穿過硝煙,淺吟低唱地訴說著被時間塵封的過往。
每到清明,武洪章會隨單位人員一起去烈士陵園祭掃。而在這個日子里,武洪章還會帶著祭品或者去鐵營洼,或者去東安務,那里一個是他二爺爺武大風的犧牲地,一個是武大風的衣冠冢。
1921年春,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創建了濟南共產主義小組,1924年11月,山東省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王盡美和鄧恩銘被選舉為領導人。王盡美負責魯南地區的黨組織活動,鄧恩銘則把革命的火種播撒到了津南、魯北平原,讓正在慶云中學求學的武大風得以接觸到進步革命思想。通過閱讀《共產黨宣言》以及更多的進步書籍,武大風的思想受到深刻教育,他堅信“只有共產黨,才能拯救勞苦大眾”。不久,他在劉格平的介紹下,加入了黨組織。
在《慶云縣志》人物傳記中,革命烈士武大風占了一個重要篇幅。傳記說:“武大風是慶云縣東安務村人,性行溫雅端莊,忠厚儉樸,素懷大志,堅貞有骨氣。”
“侵略者是弱糠,是經不起大風吹的。”他說。為此,他把名字由武同心改為武大風。
武大風被黨組織派往無棣縣工作,他挨家逐戶地宣傳抗日思想,不到3個月,就發展了40多人入黨,組建了160余人的地方武裝,除掉了60多個漢奸,策反80多名偽軍投誠,成功組織了“馬頰河暴動”。
蓬勃發展的抗日武裝活動引起了鬼子的注意。1941年2月3日(農歷臘月二十九)凌晨,日寇集中上萬兵力,趁黎明前的黑暗,把方圓10多里的鐵營洼圍了個水泄不通,采用騎兵與裝甲部隊在前,步兵緊隨其后的“鐵壁合圍”逐步縮小包圍圈的戰術,把武大風和戰士、鄉親堵在了包圍圈內。
在敵人猛烈的炮火攻擊下,武大風與大隊沖散了,和幾十名戰士、群眾被擠壓在一條深溝里,借助地勢與鬼子繼續戰斗。十多分鐘,陣地上、深溝里,已橫七豎八地躺著敵人和戰士的多具尸體。這時,通訊員報告,說東北方向已經把鬼子的包圍圈撕開了一道口子,可以從那兒沖出去。武大風看著不斷從路上倉皇逃難過來的群眾,又看了看在不斷組織進攻的鬼子陣地,說,你帶鄉親們走,我們阻擊敵人。話剛說完,他發現文書負傷倒在了溝沿上,他猛地沖上去,一把把他拽了下來。一發子彈擊中了他的左肩,鮮血一下子涌了出來,染紅了靛藍色棉襖。
子彈打光了,手榴彈用完了。武大風高喊,寧可戰死,不當俘虜!率領僅存的16名戰士與鬼子展開肉搏戰。戰士們躍出溝壕,與鬼子撕扯在一起,鋒利的刀刺狠狠扎向敵人。 激戰中,一顆子彈擊中了他,他猛地跌倒在地上,再沒有站起來。那一年,他剛滿28歲。
武洪章說,當家里人聽說“鐵營洼突圍”已經是在一天之后的事了。他爺爺推著獨輪車走了幾十里,去給武大風收尸。等走到鐵營洼,眼前的情形把他驚呆了,蠻荒的鹽堿洼地已成一片墳場,到處散落著殘肢和尸體,北風呼號,干枯的蒿草上掛著藍灰色或者土黃色碎衣條,在凄惶地搖擺,河溝里,厚厚的冰層上凝著一層瘆人的紅,那是血。
武大風犧牲后,肖華司令員寫詩稱頌:“生即正直舉止非凡系人中一大;死亦壯烈英勇不屈是無產作風上。”
敵人的殘忍沒有把革命者嚇倒,反而點燃了仇恨。各縣武裝大隊聯合展開了一系列的報復行動,給予鬼子以沉重的打擊。
1938年5月,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的著名論斷,指出,要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使每個士兵和人民都明白,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么關系。
民兵、武工隊等地方武裝的蓬勃發展,不僅為主力部隊提供了后勤保障,還為革命根據地的鞏固以及最終取得全面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炮火硝煙里的一抹紅
“我們該如何活下去?”
這是電影《柏林女人》中女主人公最后的一句話,她茫然空洞的目光投向虛無的遠方——一片硝煙彌漫滿目瘡痍的戰場廢墟。
也許戰爭的屬性是雄性的,但縱觀世界戰爭,女人,并沒有從戰爭中走開,甚至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戰爭的中心,承受著戰爭帶來的屈辱和累累傷痕。是啊,當家國零落,又能有誰可以僥幸逃脫,成為一名旁觀者呢!
如果日本鬼子沒有在1938年侵略臨沂,蒙陰縣李保德村的李鳳蘭會有一個熱鬧喜氣的婚禮,至少,會有新郎。但她沒有,她和一只披紅掛綠的公雞拜了堂。她心里有點兒失落,但不悲傷,她知道,新郎是喜歡她的,只是作為一名戰士,為了她和鄉親們能過上安穩日子正拼殺在戰場。婚后,她參加識字班,學著唱《小戰士》:
小戰士,不很大,
心里裝天下。
小戰士,不很高,
扛著槍,挺著腰。
離開了爹,離開了娘,
到處打豺狼。
不怕苦,不怕凍,
為了翻身鬧革命。
吃樹皮,穿草鞋,為了勝利早到來。
她跟著婆婆、嫂子備軍糧、做軍鞋、看護傷病戰士。她攤的煎餅,均勻薄脆,圓的像太陽。也許他會吃到呢!她想。她納的鞋底和鞋墊,針腳密實,花朵艷麗。也許他會穿到呢!她想。她照顧傷病員,不怕臟累精心細致。也許他受傷了,別人也正這么照顧他呢,她還是這樣想。她把滿心滿腹的情愫暗暗地融入了她的工作當中。
戰斗越來越激烈,死傷的人也越來越多,她的心也越來越沉重,等待中的每個嶄新一天,都讓她既渴望又恐懼。終于,她懸著的心落了地,等待有了結果:丈夫在戰場犧牲了。
“接到陣亡的消息,心里很難過吧?”幾十年后,有人采訪她問道。
“當時孟良崮正打仗,俺成天忙著糧食供給,哪還顧得難過。俺是黨員,有這個覺悟,想要取得勝利總要有人犧牲的。”老人微笑著,甚至帶有幾分羞澀地說。
老人后來領養了兩個孩子,于2008年去世,終身未再嫁。
在沂蒙山區,幾乎村村有紅嫂,家家有戰士。為合圍孟良崮,打敵人個措手不及,李明芳毅然決然帶領32名婦女,每四人一組,用8扇門板架起了火線橋,運送了整整一個團的兵力。冰冷的河水麻木了雙腿,甚至導致有的婦女終身不孕。蒙陰母親王換于,撫育了80多名革命后代,自己的三個親孫子卻因營養不良夭折。沂蒙紅嫂明德英,為救生命垂危的八路軍傷員,正在哺乳的她將乳頭放進傷員的嘴里,用潔白的乳汁挽救了傷員的性命。據說,曾有人因為明德英是聾啞人而質疑整個事件的真實性。其實,卑微與高尚從來沒有標準界定,心理殘疾比身體缺陷更讓人厭惡。還有身負重傷的女戰士辛銳,年僅23歲,面對鬼子的包圍,拉響了最后一顆手榴彈,與敵人同歸于盡……
據《戰爭和女人》一書中統計,僅抗日戰爭時期,就有15.5萬沂蒙婦女以不同方式掩護了9.4萬多名革命軍人和抗日志士,4.2萬名沂蒙婦女救護了1.9萬名傷病員。據資料記載,山東戰場女性參戰的多,爭取政權的少,尤其是以沂蒙山區為最。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
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遲浩田同志曾深情地慨嘆:“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人民……
勝利的堡壘 大后方
老家有兩間土坯房,已閑置多年,除了一臺體積龐大的織布機,就是些零碎的舊物。爺爺過世的早,奶奶靠為人織布維持家用,在那動蕩的年月,所歷經的苦難可想而知,但她很少提及,只一次,她撫摸著織布機動情地說,這可是活命的物件。單想想,禁不住讓人心疼起來。奶奶去世后,爸爸隔幾年,就會請人修繕一下。在記憶里,那房子,好像只是為了存放織布機而存在。
再次見到織布機,是在沂蒙的一個革命紀念館。一根繩索隔開一塊區域,里面一臺破舊的織布機、一架紡車和一輛似乎可以隨時架起出發的獨輪推車。織布機的擋板和紡車的搖柄已被磨得圓潤光滑,像浸了油 。旁邊一行豎排正楷黑字:男人支前上戰場,女人在家拼命干,做軍鞋,紡棉線,種地打糧全支前。
緩步從展館走過一圈,再站到這里,眼前的物件便生生活了起來:不分晝夜,紡車嗡嗡地轉動,人歇機不歇。織布機的梭子,鳥一樣,在細如發絲的棉線里上下翻飛,擋板咔嚓咔嚓地在后面緊緊追趕。憨實的沂蒙漢子,推起獨輪車,用一雙硬實的腳板,滿載著軍鞋軍糧和彈藥穿濰河、趟沂水、過吳家莊、瓦子口、太山營,推著小車跟著大部隊歷經睢寧、薛城、徐州等三十幾個縣市,往返數千余里,直把革命用小車推到滾滾長江的彼岸,推出了個孟良崮戰役,推出了個淮海戰役,推出了個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嶄新中國。
據蒙陰縣野店鎮板崮崖村“支前模范”包彥廷回憶:1941年沭河干旱,1942年又鬧嚴重蝗災,莊稼幾近無收,在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只能吃地瓜秧、樹皮,是八路軍從敵占區搞來糧食分給百姓,這才活了命。八路軍在前方打仗,咱咋能袖手旁觀,都爭著扛上槍,推著軍需物資去支前。他們避開大道,哪里山路難走走哪里,寒冬臘月,山上到處是積雪,他們就扛著物資攀著石頭爬,手凍僵、劃傷是經常的事。在護送的路上,無論怎么饑餓,也沒人抽一張肩膀上扛著的煎餅充饑。運送傷員回后方救治,遇到轟炸,會立刻趴到傷員身上保護傷員,有人還因此犧牲了。他樸實的話,道出了深厚的軍民魚水情。當時,沂蒙老區喊出了“最后一粒米做軍糧,最后一塊布做軍裝,最后一個兒子送戰場”的口號。
在淮海戰役中,群眾為了支援解放軍做工事所需要的木頭,把自己家的箱子、門板,甚至是為老人準備的棺材都抬了來,解放軍就用它們支撐起了密密麻麻的掩體、交通溝。當打完淮海戰役,解放軍部隊轉移時,吃驚地發現,周圍百十里內的村莊,家家戶戶都沒有了門板……被俘國民黨將領楊伯濤也看到了一幕:以前經過村莊,門戶緊閉,村鎮靜寂,現在卻是車水馬龍、熙熙攘攘,都是老百姓,有的給解放軍推車,有的給解放軍抬傷員,有的給解放軍做飯。更讓他不可思議的是,一輛輛大車滿載豬肉,而他前不久經過這里,連一頭豬都沒看到。他感嘆地說:民心向背至此,戰敗已成定局!
從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至解放戰爭1948年戰略反攻,沂蒙老區共有留下名字的6萬多名烈士,加上無名烈士共約近10萬烈士。 沂蒙人參加戰爭的時間從1937年至1953年,足足有16年。
孟良崮戰役,一舉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重點進攻。從沂蒙山發起的淮海戰役,更是敲響了國民黨統治的喪鐘。它的勝利,扭轉了解放戰爭的整體局面,打破了蔣介石以長江“劃江而治”的戰略妄想,此后,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接連打響,最終奪得了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
據統計,自1945年至1949年,山東先后動員1106萬多民兵民工,使用了146.8萬大小車輛,76.5萬大牲畜,出動了43.5萬副擔架,支援了華東、中原、東北、西北四大野戰軍作戰。將11億余斤糧食和大批彈藥、軍需物資運往前線,把20.3萬余名傷員轉移到后方,同時,還擔任看押俘虜,打掃戰場等戰勤任務。
毛主席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以及《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的講話》上多次提出,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群眾觀點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想問題從群眾出發就好辦。
穿過孟良崮革命烈士陵園紀念館的大門往里走,迎面就是革命烈士紀念碑,碑兩側是茂密的松樹林,一棵棵松樹蒼勁挺拔,像整裝待發的士兵。這里,埋葬著2865名在孟良崮戰役中犧牲的烈士忠骨。 墓地不高,在地面微微隆起,每個黑色大理石臥碑上都有一顆醒目的五星。五星下方,是烈士的名字,但大多臥碑上鐫刻著的是“無名烈士之墓”幾個字。無名烈士——埋葬著遠方母親永遠眺望不到的兒子,和一生割舍不下的牽腸掛肚。“無名”比“有名”更扣人心弦,更揪得人心疼。
走在“沂蒙情雕塑園”長廊,我在雕塑群“火線橋”前佇立。旁邊有兩個當地民工在低語,一個問:如果是你,你會去支前打仗嗎?另一個人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會。
我抬頭,發現孟良崮,海拔不高,山勢亦不陡峭,卻讓人感覺無比的巍峨——它的高大巍峨,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