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延安《藏在棉花里的暖(外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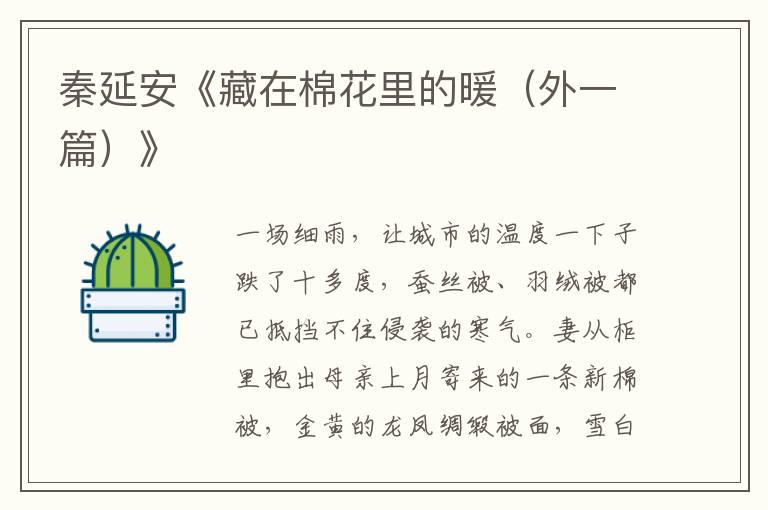
一場細雨,讓城市的溫度一下子跌了十多度,蠶絲被、羽絨被都已抵擋不住侵襲的寒氣。妻從柜里抱出母親上月寄來的一條新棉被,金黃的龍鳳綢緞被面,雪白的被里,包裹著云一樣潔白柔軟的棉花,浸滿了一床的暖意,就像母親舍不下的呵護與疼愛,讓這個初冬變得格外暖和。
記得國慶節回家時,屋門緊鎖,鄰居告訴我,母親去坡上拾棉花了。當我氣喘吁吁地爬到坡上時,只見雜草叢生的荒地中有一片碧綠的棉田,紅白相間的花兒開的燦爛,一朵朵棉球被秋風染得像雪花一樣潔白耀眼,還有那些沒有破殼的棉桃,就像一個個橄欖高高地掛在棉枝上。白發凌亂的母親正弓著背,一雙布滿老繭的大手,如老鷹伸出的利爪,很快地將一團團白色的棉花勾出,扔進掛在腰間的包袱里。
我喊著母親,母親也看到了我,那滿是汗水的笑臉如一朵咧嘴吐絮的棉花開在秋日的棉田里。母親說拾完棉花再回家,我也去幫母親。手下的生疏,讓我很快地便被母親拉下,而且還時不時地被尖利的棉殼戳傷手指。我勸母親別再種棉花了,既辛苦又費力。母親說,這是最后一年種了。收了棉花后,就夠給我做床新被子。再往后自己也種不動了,眼睛也看不見針腳了。母親的話就像棉殼一樣,劃得我心痛。
記得小時候,每年父母親都要種一畝地棉花。當大地落了入春的第一場透雨之后,母親便將鋪滿豬糞已經翻好的田地進行耙平,然后覆好地膜,開始種棉。在地膜上每隔三四寸鑿出小洞來,再將精心挑選的六七粒棉籽種進去,以保證出苗率。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并不是那么容易,洞要鑿得不偏不倚,籽要放得不多不少,填土要不深不淺,哪一步操作不當都會影響出苗。當棉田里的苗兒吐齊時,母親便開始“間苗”和“定苗”,經過不斷的篩選和優勝劣汰,最后每窩就留下兩三株長勢最好的幼苗。
迎風見雨,很快棉田里便是綠瑩瑩的一片。那些青枝綠葉的棉花棵,就像處于青春期的叛逆少年,一點兒都不讓人省心,幾天不管,就會狂瘋野長。整個夏天里,母親就像是長在棉花地里一樣,忙著修枝打杈,噴藥防蟲,沒有片刻的休息。在母親的精心照顧下,那些由青綠變成紫褐色的鼓鼓棉桃,便一茬又一茬地開始綻放,而拾棉花則緊跟著進行,否則一經雨淋,便變了品質。
秋高氣爽,湛藍的天空里飄著朵朵白云,炸蕾吐絮的棉田里,一朵朵白絨絨的棉花開得正旺。一家人撒在棉田里,緊張地拾棉花。一雙雙手,在棉田里歡快地游動著,舞蹈著,歌唱著,很快地,腰間的包袱便鼓鼓的如懷孕一般。棉花豐收了,一家人的吃穿便有了著落。
父親去世后,我們兄妹幾個勞燕分飛似的各奔東西,村里的土地也占用光盡,而堅持住在鄉下的母親,便在村人撂荒的山坡上開出了一塊棉田。每年入冬前,我們都會準時收到母親郵寄來的孩子們的新棉衣,細密的針腳,柔軟的棉衣,包含著萬分愛意。雖然因為暖氣,這些棉衣上身不了幾次,但每一年母親都堅持做著,郵寄著。
“花開天下暖,花落天下寒。”被陽光喂飽的棉花,總是一直綿軟在母親的眼里。她讓我明白了做人要像棉花一樣謙卑,不傷害別人也不傷害自己,既可以為別人抵御風寒也可以讓自己像陽光一樣溫暖。
做人就要做棵大白菜
“諸肉不如豬肉,百菜不如白菜。”第一次聽母親說這話時,我有點兒不解。但是當露水走成了白霜,金風換成了北風之時,不起眼的白菜就在鄉村變得炙手可熱起來。雖然也有蘿卜,但它總如二愣子似的不懂得變化。而瓷一樣白,黃玉一樣嫩黃的大白菜,卻在母親的手下千變萬化出了各種滋味,溫暖了寂寞漫長的寒冬。直至多年后,我才知道,其實不只是我,無論是人煙靜寂的鄉村,還是車水馬龍的城市,大白菜一直是千家萬戶冬日餐桌上的常客。
說起來,大白菜算是我的老朋友。打記事起,我就跟在母親的身后年復一年地種著大白菜。在母親的眼里,大白菜是平民生活中的重要意象,與大白菜和解,就生活化了。
俗話說,頭伏蘿卜,二伏白菜。沐浴著陽光雨露,攜著大地的體溫,不幾日,一粒粒如芝麻粒似的白菜種子,便鉆出黑暗的土壤,站成一畦碧綠,亮麗了整個菜園。間過苗的大白菜,迎風便舞,遇雨更倩,長得爛漫而又任性。最后,便如蠶吐絲似的,吐出一片又一片的綠葉,層層疊疊,豐美新鮮,猶如一朵朵盛開的花,就連蜜蜂都受到迷惑,不時飛來。此時,母親就用稻草如捆綁青春叛逆的孩子似的,將鋪散開來的葉子收攏捆縛起來。捆縛住的大白菜并沒有氣餒,她們抱緊內心的清白,收心養性,長得更加豐美起來。當鮮艷的西紅柿失色、攀高的豆角跌落、高貴的茄子耷拉下時……曾經卑瑣的大白菜,卻藏著陽光,猶如鄉下豐腴腰身的農婦,站得更有精氣神兒了,一直到白露為霜。看著在寒風中堅守的一棵棵大白菜,母親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做人就要做棵大白菜,經得起歷練,守得住清白。
母親的話語讓我對白菜有了新的認識。因其“青白高雅,凌冬不凋,四時長見,有松之操”,古人將大白菜稱之為“菘”。“早韭欲爭春,晚菘先破寒。人間無正味,美好出艱難。”貶謫的蘇軾在收種大白菜時,便悟出了發人深省的人生哲理。在詩人楊萬里眼里,白菜則是“蘆菔過拳菘過膝,北風一路菜羹香”。并在《進賢初食白菜因名之以水精菜》中,將其喻之為“水精菜”,可見“百菜之王”的稱號并不是空穴來風,徒有其名。從此,白菜一詞也就李代桃僵,世人皆知。而對于畫家齊白石來說,白菜更是寓意非凡。他畫一枚柿子、一棵白菜,叫《一世清白》;畫一堆柿子,幾棵白菜,叫《事事清白》。
當然,“蘿卜白菜,各有所愛。”雖然很多人認為白菜是上不了臺面的菜種,但這并不影響它在老百姓心中的位置。無論是涼拌、干炒、醋熘、燉燒,還是做餡、配菜、漬酸菜,都滋味悠長。不管是成都的麻辣火鍋,還是哈爾濱的殺豬菜,抑或是西安的大燴菜……大白菜總是扮演著重要角色,用它豐富的營養填補著北方人冬季干癟的腸胃。而在川菜里,白菜更是被推為蔬菜之首。有一道“國宴”上的傳奇名菜,叫開水白菜。一星油不見的清湯盛在白凈的碗里,里面擱著幾棵白菜心。看似最寡味的一道素菜,可吃在嘴里,卻味蕾全部綻放,讓人驚為世間絕味。
雖然久經風雨,飽受烈日與嚴寒,但不惹眼、不膩口的白菜,不僅將自身修煉成了菜園里內涵豐富、底蘊深厚的堅實風景,更是用沉甸甸的身子守護著內心的一塵不染,潔白無瑕,在平淡中給人以驚奇。做人就要做棵大白菜,母親的這句話讓我受益無窮。
本欄責編 李春風
郵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