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蔚州》梅潔散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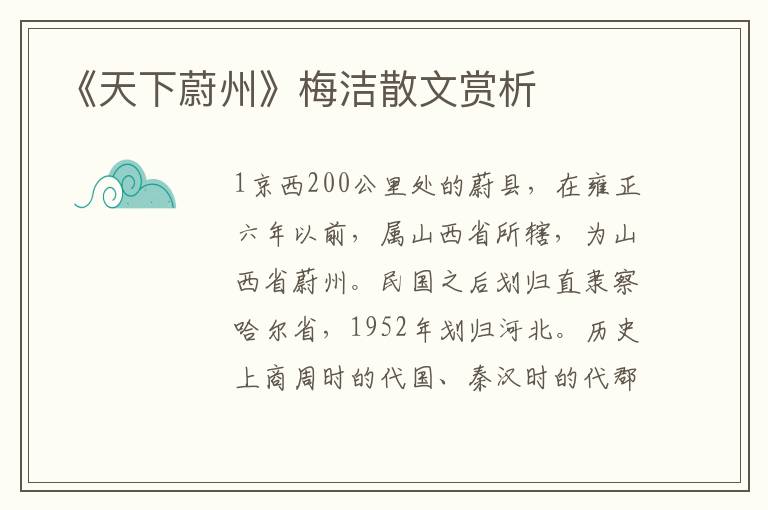
1
京西200公里處的蔚縣,在雍正六年以前,屬山西省所轄,為山西省蔚州。民國之后劃歸直隸察哈爾省,1952年劃歸河北。歷史上商周時的代國、秦漢時的代郡均指蔚縣。北魏時,原代郡所轄的懷荒、御夷第一次改稱蔚州,僑置平遙,北周靜帝(公元579年)時,正式移置今蔚州城。蔚州作為“城”存在,距今已有1436年。
地理意義上的蔚州屬恒山山脈以北寒涼的塞外。由山西境內自西向東橫貫而來的蒼茫恒山走到蔚州時分了個小叉,蔚州就是嵌在這個山叉里東西長160華里、南北寬40華里的一帶平川。
很長的歷史時期中,匈奴人萬馬奔騰,他們鐵騎滾滾從這一帶平川飛駛而過;當“燕云十六州”被割讓給契丹人之后,“十六州”之一的蔚州(那時蔚州轄四縣)就歸了同樣是“鐵騎滾滾的遼國”;再后來,又歸了依然是“鐵騎滾滾”的蒙古人;直到明清之后,這“一帶平川”從東到西才逐漸形成了八大商業集鎮,其中之一就有那個2800多年前的代國國都代王城。在長達五百多年的明、清時期,八大集鎮始終維持著繁華的古代商貿,而古代商貿的發展共同鑄就了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漢人——或許有匈奴人、契丹人抑或是蒙古人的后裔——沉穩、冷靜,勤奮、節儉,精明、強干,思想多于言語、喜怒不形于言表,獨立孤傲的自我意識以及敬業、責任、吃苦、耐勞、意志力和生存力等等作為人的優秀素質。故此,蔚縣人有“張家口的猶太人”之稱。甚至說:“天下十三省,能不過蔚縣人”。我們從這些“說法”中應該可以領略到蔚縣這一地域里人群的出色。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伊始,京、津、冀1300多名大學畢業生被分配到張家口,其中70人分到了蔚縣,我是70人中一員。我們那個年代的分配,包含有“發配”和“知識分子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旨義,而蔚縣當年是張家口地區最貧困的縣域。我在蔚縣一待就是14年!我在那里與我的大學同班、一個極具蔚州人優秀素質的青年結婚、生子,14年和以后的許多年里,蔚州無數“謎”一樣的文化現象和人文景觀都令我驚詫不已——
首先是遍布蔚州的古建筑,這些古建筑包括古塔、寺廟、古堡、戲樓和民宅。如果說那座建于遼代時期的十三層古塔和一些寺廟我們在別的地方也可以找到的話,那么,那些古堡、戲樓和民宅就實在為中國一絕。在蔚州,無論高山還是平川,無論山地還是丘陵,有堡就有村,有村就有廟,有廟就有戲樓。蔚州歷史上有八百城堡之說,這足以說明蔚州曾經是冷兵器時代戰事頻繁發生的邊地。八百古堡最終成為八百村莊,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進行的文物普查發現,蔚縣有738個村莊,村村建有古城堡,有700座古戲樓。這些古城堡、古戲樓全部為明清建筑。經過十年“文化革命”的浩劫之后,1984年蔚縣再次進行文物普查,發現保存完好的古戲樓仍有300余座。那座屹立在古代國遺址上的代王城戲樓是一座三面戲樓,就是說它的東面、北面、南面都可以唱戲、看戲,這座建筑極其精美,如同古代亭閣般的戲樓是蔚縣古戲樓中最獨特的一個。“文革”時為保護這座戲樓,人們用土泥糊住戲樓四壁,然后在上面寫上“革命口號”,才幸免紅衛兵造反派的破壞、摧毀。蔚州還有諸多造型別致的穿心戲樓、排子戲樓、庭院戲樓,真是洋洋大觀。戲樓在蔚州也被稱為戲臺、樂樓、歌臺,這些青磚筒瓦、雕龍畫鳳、飛脊斗拱、彩繪紛呈的古代文化娛樂設施,星羅棋布般出現在蔚州,這不能不使人深思:這里究竟發生過什么?這里的人群在崇尚、敬畏著什么?它身后博大深邃的歷史文化背景又是什么?
蔚州的民宅建筑也極其獨特,明洪武年間建成的蔚州城為州城,這整整一城池的民居,全部仿老北京的四合院建成,這些四合院如今大部保存完好。當你穿行在一街一巷的灰墻黑瓦、古石老磚的院落中間時,你不能不產生這樣的暢想:這會不會是當年被召到京城建元大都、故宮的三千蔚州男兒的遺傳?在蔚州地域的西端,有一個與山西接壤的古鎮暖泉鎮,暖泉鎮是蔚州八大商業集鎮中最獨特、最美麗的地方,它的獨特、美麗在于它有南方水鄉之韻:當你看到繞街的小河從人家的門前汩汩流過,當你聆聽一街一河的杵衣聲和村婦們此起彼伏的歡笑聲時,你無法不生出“塞北江南”的快樂與喜悅。暖泉鎮最令人驚異的是它無與倫比的古民宅古民居,鎮里的西古堡村是蔚州八百古城堡中最耀眼的一個,它的城堡呈“甕城”形,“甕城”建筑應追溯到元代。在甕城內的民居民宅大都為明清古建筑,高大的木門樓、大青磚砌墻、無處不在的磚雕木刻……西古堡村至今保存完好的古代民居民宅院落有180多個,走進這些四進四出、甚至九院相連(當地人稱為“九連環”院)的古民居古院落,你無法不產生如同走近山西祁縣喬家大院一樣的歷史感和滄桑感,你無法不想去追問:是誰在這里建造了如此的氣宇軒昂?他們背后龐大的財政支持如何而來?
我想說的第二個方面是蔚州的民間藝術。“大紅燈籠高高掛”在這里的許多古鎮有數百年的習俗,每逢春節,成千上萬的各式燈籠把大街小巷掛成了一個燈的海洋,惹得京、津、張家口的城里人年年絡繹不絕地趕來看燈。蔚州的剪紙藝術應該說是中國民間藝術一絕,由民間藝人手中上百把小巧玲瓏的雕刀、刻刀(而不是其它地域剪紙用的剪刀)在白紙上雕刻出來的數以百萬、千萬計的花草、魚蟲、戲劇人物,用快樂飽滿濃艷鮮活的大紅大綠的色彩點染之后,便走向了世界。蔚州剪紙最富吸引力的是古代戲劇人物臉譜。蔚州人從王老賞始,世代相傳,已將中國戲劇中的2400多個古代人物的臉譜刻成了剪紙,那臉譜上瀑布般流泄的黑胡須、白胡須根根細如發絲,蔚州人可以在這方寸白紙上,以陽刻法刻下近千刀!于是,那黑胡須、白胡須硬是有了飄拂感。現在,不僅在中國的旅游商店、機場、國際商貿活動場合無不出售、交換、展示著寫有“中國剪紙”的蔚縣剪紙,就是前些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也將校內的六大景點以蔚縣剪紙的藝術樣式向國內外朋友和全校師生贈送了20萬套。蔚縣剪紙的藝術特色、淵源已被蔚縣文化人田永翔撰文介紹到世界50多個國家。
蔚縣繼王老賞之后,又出現了周永明、任玉德、仰繼、陳月新,以及周永明之家族、子女(周河、周廣等)、焦氏家族、盧海、李閩等等一大批大師級人物和藝術新秀。
周永明一生創作了1500種剪紙作品,尤其是他創作的戲曲小臉譜成為我們這個世界經久不衰的喜愛;任玉德集三十年剪紙藝術生涯,創作了2500種剪紙作品,其創作的無數剪紙精品和在蔚州戲曲大臉譜基礎上誕生的任氏泥塑鏤空臉譜成為中國民間藝術之瑰寶,他的許多剪紙作品被制作成郵票、明信片并在國內外獲得各種大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授予周氏兄妹等7位蔚州青年剪紙藝人“民間藝術大師”稱號;新寫實主義剪紙藝術創始人李閩拓開了蔚州剪紙藝術的新領域,他把剪紙藝術發揮到了神妙的極致:他的極具震撼力的剪紙人物肖像和山水作品完全可以與攝影、版畫等高雅作品媲美,他創作的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肖像酷似一幅逼真的攝影,被外交部以6萬元收購贈送了奧巴馬本人,致使這個大洋彼岸的世界對中國民間藝術驚嘆不已;盧海創作的“紅樓十二金釵”惟妙惟肖,在世界20多個國家的銷售經久不衰……
蔚州剪紙人才濟濟,薪火相傳,大師輩出。這是蔚州剪紙的大幸,也是中國民間文化的大幸。
我收藏了一些蔚縣剪紙,一有閑暇,我就喜歡翻弄出這些藝術品陶醉一番,我常常想,這原本由大姑娘小媳婦們繡鞋上的紙“花樣”,怎樣在數百年里發展成為蔚州男女老少都能從事的且有了絕妙藝術造詣的民間藝術?我還想,由繡鞋的紙“花樣”最后走上了遍及城鄉人家的彩色“窗花”,蔚縣人對生活有著怎樣的審美追術呢?
還有“蔚縣秧歌”,這是一個蔚縣在明清時代發展、完善起來的地方劇種,這個劇種在上世紀50年代由中國文化巨匠郭沫若評價為“百花叢中一點紅”。“秧歌”的發展也是一個謎。你想,一個沒有水澤的塞北高寒地帶,何以將南方的“秧歌”、將江西的弋陽腔(后發展為京腔)、將元代在民間廣泛流行的道家音樂“道情”以及今天家喻戶曉的“山西梆子”,水乳般交融成為自己數百年不衰的一個劇種,蔚縣曾經經歷著怎樣的南北文化大流通?
我想說的第三個方面是關于蔚縣的能工巧匠。前面說過,在張家口一帶,幾百年來都流傳著一種說法,即“天下十三省,能不過蔚縣人”,隨著這一說法的另一種說法,叫“凡是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蔚縣人”。還有人說,“蔚縣人尿泡尿捏個狗頭哨都能賣錢”。在計劃經濟年代,凡說這話的場合,人們都是帶有嘲諷或戲謔的意味。但在商品經濟發展的今天,我們完全應該將此理解為蔚縣人頑強的生存能力。蔚縣工匠藝人之多、門類之全、分工之細都是中國的許多縣市無法企及的:木匠、石匠、銅匠、錫匠、銀匠、畫匠、麻繩匠、柳編匠、氈匠、蘿匠、靴匠、帽匠、筆匠、油匠、香匠、紙匠、席匠、餅匠,還有燒沙鍋的匠、捏瓦盆的匠、剪窗花的匠、卷花炮的匠,當然,最多的還是毛毛匠。蔚縣匠人常常是一村一鎮地集合性出現,如瓦盆窯的燒窯匠,辛莊的磚瓦匠,小貫頭村的泥匠,紙店頭村的紙匠,而南張莊家家戶戶是剪紙藝人……
蔚縣人在古代就懂得了我們今天依然遵循的商業法則,那就是專業化分工和規模經營,蔚縣匠人最反對“樣樣精通,樣樣稀松”,蔚縣人的生命里深深地潛隱著“凡事追求極致”的生存要素。蔚縣人歷來是忙時為農、閑時為匠,當他們在土地上刨不出食來時,他們就身懷絕技走四方。他們曾數千人到京都參與建造皇宮,小貫頭村的泥匠們蓋起了一個張家口市;他們織的麻布數百年里都是朝廷貢品,北京前門的繩麻店全是蔚縣人所開,紙店頭村的白麻紙銷到了大江南北;遍布蔚州大地的古建筑、古民居、古戲樓、古廟宇都是蔚州工匠藝人自己的創造,他們甚至可以將蓋好的戲樓僅拆去邊墻、再整個地移到指定的地方……
2
當然,最了不起的還是那些為張家口成為馳名中外的“皮都”做出了歷史性貢獻的“毛毛匠”。
我在《張庫大道》一文中曾寫道——
是張庫商道的繁華,使廖廓草原興起了偌大的城市烏蘭巴托、恰克圖、呼和浩特、包頭和沿路無數的縣、鎮、旗、盟,其中,最大的受益之一是張家口成為馳名中外的‘皮都’。從乾隆年間(1728年)始,張家口的皮毛作坊已鱗次櫛比,從業皮毛的工人已數以萬計。此時的張家口已開始由軍事營堡向商業市鎮過渡。這個時期的張家口,毛皮業的聲譽已響徹海內外,由此出現了一個這樣的現象:即全國各地的皮市價格,非經張家口定價而不進入交易。張家口的毛皮業在中國毛皮業發展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在張家口從事毛皮行業的人員多半來自今天由張家口市轄的蔚縣、陽原、宣化、懷安等地人,而其中蔚縣人是最為輝煌的成功者。在張家口近八百家毛皮行業中,有一半以上為蔚縣人所開,在三萬多從事毛皮業的人員中,有近兩萬人是蔚縣人!在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中,蔚縣的“毛毛匠”幾乎遍布中國,而中國最出色的毛皮商清一色為蔚縣人。這曾是一個歷史現象,也曾是一個商業奇跡。
當年,僅蔚縣城內的毛皮商號就達百余家,從事毛皮行業的有五千余人,多達半個城。一批又一批技術精湛的毛皮匠人被張家口的大商號紛紛聘請去當了經理、案頭(皮貨裁剪技術人員)。在晉商風云天下的時候,蔚縣的“皮小子”們以自己獨特的毛皮手藝和頑強的意志一個個走向了人生的成功:蔚縣下平油村田旺高開設的“謙生義”皮號,從咸豐、同治、光緒、宣統、民國一直經營了下來,蔚縣的許多村鎮都有“謙生義”的作坊,生產的羔皮百分之八十銷往山東,當年,濟南皮貨商們非“謙生義”貨不買;“逯元昌”皮號生產的鼠皮、紅狐皮、白狐皮、沙狐皮、黃鼬皮等細皮貨一直遠銷歐美;而“德巨生”皮號生產的皮襖、皮褲、坎肩等一直是撫順、大連、內蒙、新疆、庫倫、恰克圖的搶手貨;宣化、張家口的“德興齋”、“德興玉”、“德壽隆”蒙靴業老字號為蔚縣人李鹽房所開,當年張家口、宣化有蒙靴業字號80余家,從業人員兩千多人,多半為蔚縣人,每年銷往蒙古地的各式蒙靴20余萬雙,蒙古活佛、四十八家王爺每年輪流去北京朝貢,路過宣化時都住李鹽房家,一律免費吃住。
最顯赫的要數王樸(當地口音念po)。蔚縣城鄉四處流傳著一句俗語:“不吃不喝,趕不上王樸”。王樸是蔚縣涌泉莊人,自小挑著扁擔隨父賣煤,常常躺在城門洞里睡覺。十三四歲時王樸就領著十歲的三弟到宣化府學皮毛手藝,弟弟學細皮行,王樸學老羊行。每天從老羊皮上鏟肉渣、泡皮、揉皮,又臭又熏又累,吃盡苦頭。后因不忍欺辱和人打了架而被老板開除,走投無路的王樸一狠心就用幾張老羊皮和已學會的手藝在張家口自己租房干了起來。王樸的故事很長,王樸的發達不無傳奇,我這里暫不細說。我們只須知道王樸后來開的“德和隆”皮貨商號最終發展成為張家口、北京、天津最大的商號之一,在王樸四個兄弟共同經營下,他們在天津擁有了三家合資企業和龐大的進出口貿易,他們和晉商一樣,在天津開了銀號。他們在北京大柵欄開了有名的“德聚隆”商號,經營皮革和進口百貨,其四弟王槐成為名滿京津的“王四爺”。王樸兄弟用在北京、天津、張家口、蔚縣城開辦皮貨店、百貨店、綢緞鋪、面鋪、鞋帽鋪、鹽坊、銀號的錢,開始大量購置房地產:在蔚縣老家涌泉莊、閻家寨、南留莊、北方城等村鎮購買土地達三千余畝,在張家口壩上大青溝購地一萬多畝。王樸涌泉莊的莊園占地60多畝、14個院落、220多間房舍,在閻家寨有房180余間,在張家口、宣化有房100余間,在蔚縣城有房產40余處、500余間,另在北京、大同、呼和浩特、包頭、大青溝的房產無計其數……
那年夏天,蔚縣文聯副主席田永翔先生陪同我在蔚縣大地行走,我們走過了古代王城,走過了涌泉莊、北方城、宋家莊,走過了“江南水鄉”般美麗的暖泉。一路我都在想,蔚縣人普遍具備的鉆研精神、精益求精精神、鍥而不舍的創業精神,絕對是那些遍布蔚縣城鄉的工匠藝人精神的世代傳承。蔚縣人這種精神的形成與傳承,絕對是遇上了一個經久不衰的商業競爭機制。沒有競爭,他們何以求精?沒有求精,他們何以生存?那么,他們遇上了什么樣的競爭時代呢?
綜上所述,蔚縣的“古建筑之謎”、“民間藝術之謎”、“古老而現代的商業精神之謎”都曾讓我困惑、追問了很長年代,終于有一天,我在瀚海般的閱讀里,在十幾年的行行復行行中,一切都豁然開朗。原來,這一切都與古老的張庫商道有關。
3
張家口的國際商貿活動應追溯到明初。如果從明洪武年間開始移民山西人到張家口計起,這塊原為匈奴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來了去了的馬踏之地便成為了漢人與北方多民族的融合之地,這段歷史已達600余年。而作為商埠的張家口,如果從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明廷批準在今張家口大境門外正溝、西溝與成吉思汗敗北的子孫后裔們開辦“以布帛易馬”的邊界“貢市”(后稱“馬市”),到1929年中俄(蘇)斷交、商貿停止,一條從張家口至庫倫、一直延伸到恰克圖(今蒙俄邊界上的一個城市)的長達4300多華里的中俄貿易商道,整整運行了377年!如果說張家口是中國北方絲綢之路的“旱碼頭”,那蔚州絕對是搭在碼頭和航船上的一塊堅實的跳板。
蔚州坐落在恒山余脈和燕山余脈的夾縫之中,層巒疊嶂的恒山、燕山,屏障般把蔚州乃至張家口地域千萬年地擋在了寒冷的塞外。然而,大自然奇跡般地在蔚州南北的山脈中,留下了八大通口,古時叫關隘,這八大關隘在南邊自西而東有石門峪、北口峪、九宮口峪、松枝口峪、金河口峪,在北邊自東而西為鴛鴦口峪、榆林關、五岔口。所謂峪,即是恒山、燕山山脈中“蛛曲蟻穿”般的百里大峽谷。在沒有路的年代,在有路而沒有火車、汽車的年代,人類是從這些大峽谷中艱難地走進來又走出去,最終走向了文明。由于這些“峪”的存在,蔚州自古成了軍事上的鎖鑰重地,也成了張庫商道上重要的商貿基地。
從南邊穿越“千夫拔劍,露立星攢”的北口峪(歷史上著名的飛狐峪),就到達保定的淶源;穿越懸崖如刀劈斧砍般的石門峪,就通往了山西的靈邱、太原;松枝口峪通往易縣、保定;金河口峪通往淶水、高碑店。在北邊過鴛鴦口峪經宣化到達張家口、庫倫和恰克圖;過榆林關往陽原東城到懷安、經大青溝直達內蒙草原;過五岔口經陽原西城直達山西大同。
我們由此可以想見當年精明的晉商、饒舌的京商、沉穩的蔚商以及南來北往的外國商、中國商們通過蔚州境內的八個大峽谷穩步走向張家口、走向庫倫、走向恰克圖,折轉身,走向北京、天津、上海,一直走到武夷山的茶山、走向蘇杭的綢緞和走向武漢、襄陽的碼頭時的情景。在數百年的走來走去中,走出了商道上蔚州古老的繁榮、古老的文化、古老的生命精粹,走出了蔚州大地上繁華的八大商業古鎮,走出了馳名中外的百年“皮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