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孔乙己》講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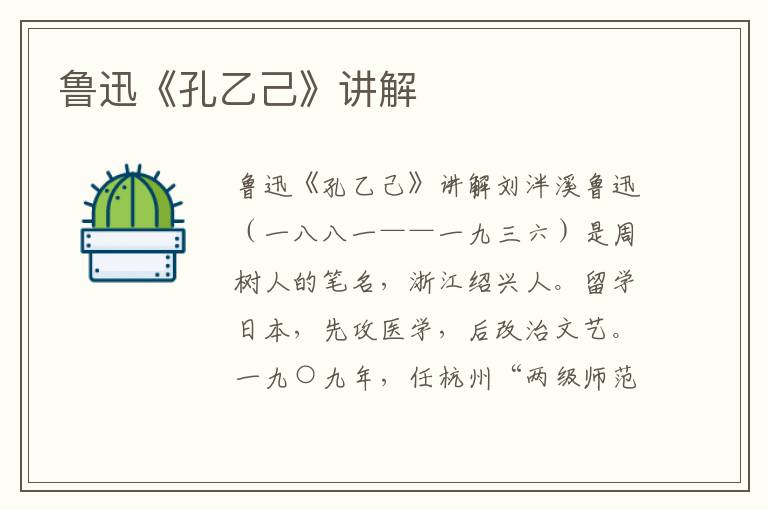
魯迅《孔乙己》講解
劉泮溪
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是周樹人的筆名,浙江紹興人。留學日本,先攻醫學,后改治文藝。一九○九年,任杭州“兩級師范學堂”的化學和生理學教員。次年,改任“紹興中學堂”教務長。一九一一年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任教育部部員。繼隨部移至北京,兼任北京大學、師范大學及女子師范大學的國文系講師。后復南行,任廈門大學文學教授。一九二七年二月,抵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教授兼文學系主任和教務主任。三個月就辭職了。從此便結束了十八年的教育生涯。離廣州后,寓居上海,努力于著作翻譯,一直到死。想對他的事跡知道得詳細一點,可參看《魯迅自序傳略》、《吶喊自序》及許壽裳編的《魯迅年譜》。
魯迅的著作有:小說集《吶喊》《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野草》;雜文集《熱風》《華蓋集》《而已集》;文藝史《中國小說史略》等。翻譯有《小彼得》《桃色的云》《豎琴》《苦悶的象征》等。現在所見的《魯迅全集》,是一九三八年“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的。
《孔乙己》選自《吶喊》,為一九一九年所作之短篇小說。這篇東西的主旨,是寫被八股枷鎖束縛住了的封建知識分子沒落的悲哀。孔乙己,這可愛而又可憐的小東西,他一心一意想撈個秀才,過去的一段時光,自然是專從八股文中討生活,因此,他的血肉,他的靈魂,于不知不覺中,已由于中毒而枯萎,結果弄成“好喝懶做”,“不會營生”。倘使社會仍舊停滯不前,長衫階級不管肚子里裝的是什么東西,依然被社會重視,那么一般封建知識分子正在做“春風得意馬蹄疾”的美夢。像孔乙己這樣的人物,當然不會出現,而魯迅的這篇小說也就無從產生了。可是時代是毫不容情的,好像滾滾的水流不憐惜沉淀的泥沙一樣。我國自從甲午中日戰爭失敗以后,曾經發生過戊戌政變、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這一連串的維新與改革,都是志在把中國從落后的狀態里拯救出來。雖然沒有達到理想的境地,但畢竟也算是一番改革:滿清政府推倒了,科舉廢除了,新文化萌動了。在這激變的時代里,一般前進的知識分子便撞破了舊文化的樊籬,加入了革新的隊伍。而那些被“科舉”“制藝”剝奪了靈魂的軟癱書生,就只好任憑命運嘲弄了。
魯迅是從舊社會奮斗過來的。在新文化運動的前前后后,他是善于使用文藝匕首的戰將。他愛中國,他愛中華民族,他站在暴風雨的前哨,察覺出了時代的脈搏和聲音,想表現自己的愿望,同時也就發現了隱藏在黑暗的社會現實里面的病態和丑惡。魯迅,他是精于醫道的,他曉得中華民族的病根由來已久,他的使命是要給中華民族洗滌靈魂。他于是用銳敏的眼光觀察,用解剖的利刃分析,最后,以藝術的匠心,給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國農村塑造出好些典型人物,奠定了中國新小說的初基。由于他的小說,我們才真正認識了落后的中國農村。像《阿Q正傳》,早為中外人士所稱頌;而《孔乙己》尤為現代知識分子所喜愛。原來像孔乙己這一類型的人物,和我們相去不遠。試想我們的祖代,不還和孔乙己常來常往嗎?就是我們的血液里,誰能說沒有殘留著孔乙己的成分。無怪乎馮文炳說:“我讀完《孔乙己》之后,總有一種陰暗而沉重的感覺,仿佛遠遠望見一個人,屁股墊著蒲包,兩手踏著地,在曠野當中慢慢地走。我雖不設想我自己便是這‘之乎者也’的偷書賊,但我總覺得他于我很有緣法。”從孔乙己的沒落,我們應該知所警惕。
沈雁冰說:“《孔乙己》是笑中含淚的短篇諷刺。”馮文炳也說過:“魯迅君的刺笑的筆鋒,隨在可以碰見。如《白光》里的陳士成,《端午節》里的方玄綽,至于阿Q,更要使人笑得個不亦樂乎,獨有孔乙己我不能笑。第一次讀到‘多乎哉?不多也!’也不覺失聲,然而馬上止住了,陰暗起來了。……”真是呢,一連讀上幾遍之后,弄得我們哭也哭不出來,笑也笑不出來,只覺得一陣陣的心酸。這的確得歸功于作者那諷刺的筆鋒。諷刺和理想原來是一個東西的兩面。理想派只寫美點。諷刺派則抓住社會的惡點,加以放大,目的卻還是使惡點泯滅,使美點發揚光大。所以理想派與諷刺派,二者似相反而實相成。無論理想派也罷,諷刺派也罷,總得對于社會人生有所愛。理想派是不必說了。諷刺派若無所愛,會陷于刻薄、冷酷、狠毒,也便不成其為諷刺了。魯迅一九二八年在《小雜感》里曾說:“人感到寂寞時,曾創作,一感到干凈時,即無創作,他已經一無所愛。創作總根于愛。”這很可以作他那諷刺筆觸的注腳。由此,我們更加了解魯迅嫌惡中國人,咒罵中國人,譏刺中國人,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的,和一般的漫罵冷嘲絕不相同。單看他對于孔乙己的處理也就可以明白。他不一起頭就把這個可憐的角色扔在死沉沉的地方,卻安插在熱鬧快活的場合,讓他從笑聲里走向沒落死亡,這給人的印象是多么深刻,使你讀后心頭上不但感不到輕松,反倒增加上重量了。
笑——一根譏刺的針,貫穿著作品的骨干,可說是這篇小說的一個特色。
還有一個特色,是純凈的素描。純凈的反面是蕪雜。我們見好些作品,里面充滿了虛意浮詞,好像作者故意賣弄他的技巧。在《孔乙己》里,每句話都有用,每個字都有用。而在字里行間,卻閃耀著作者智慧的光輝,洋溢著作者對人生透視的力量。可見字句經濟的來處,原來是作者靈魂深湛的表現。還有比這個更美的嗎?張定璜的話倒是很愜當的。他說:“他知道怎樣去用適當的文字傳遞適當的情思,不冗長,不散漫,不過火。有許多人費盡苦心去講求涂刷顏色的,結果不是給我們一塊畫家的調色板,便是一張戲場門前的報告單。我們覺得他離奇光怪,再沒什么。讀《吶喊》,讀那篇那里面最可愛的小東西《孔乙己》,我們看不見調色板上的糊涂和廣告單上的丑陋,我們只感到一個干凈。”
關于《孔乙己》的結構方法,全文分上下兩部分,而以第九段為分水嶺。第九段只是一句話:“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么過。”這一句話的上半句,“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正是以上八段的結束。因為以上八段,都是從小伙計眼中看出孔乙己的日常生活,并道出他那使人快活的情形。其實這些使人快活的也正是孔乙己的不幸與可憐處,他的生存地位原是如此的。第九段的下半句,“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么過”,正是以下四段的開始。因為以下四段是小說中新的發展、新的變化,由孔乙己的失蹤以至復現,而寫出了小說的最高點。又因這小說顯然是兩部分構成的,所以前后兩部分的空氣也完全不同,這表現在文字上,就是前后兩種不同的節奏。在前半中,孔乙己在第三段才被介紹出場,而這一段的最后一句就是,“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到了第四段的最后,又是由于孔乙己的自己辯護,由于他的引經據典,之乎者也,而“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第六段的最后,仍然是“在這時候,眾人也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第六段的最后,“于是這一群孩子都在笑聲里走散了”,雖然字句不同,然而同是一種情調,同是一種節奏的回旋,是非常清楚的。在后半中,第十段剛開始,掌柜的正在慢慢地結賬,忽然說,“孔乙己長久沒有來了,還欠十九個錢呢!”第十一段,于久違重逢之后,掌柜的又說,“孔乙己么?你還欠十九個錢呢!”而第十二段中,將近最后,到了年關,掌柜的又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了第二年的端午,又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這些相同的句子,就造成了后半的節奏。把前后兩部分綜合起來看,情調雖不相同,但作者的寫作方法卻是一貫的,全文都是用了這種相同或相近的句子作為波瀾,以中間第九段作為一個橋梁,這樣一波一波地把文章推移下去。
此外,尚有幾點應該注意的地方:
小說之所以容易引人入勝,往往由于作者用了一種逐層剝脫的寫法。譬如《孔乙己》的第四段,作者介紹孔乙己的時候,說他“皺紋間時常帶著傷痕”,讀到這一句怪使人納悶;再讀到“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還是納悶;直讀到“我前天親眼看見你偷了何家的書,吊著打”,才弄得個水落石出。但是他為什么偷書呢?到下段才明白。又如第十一段,小伙計先聽到“溫一碗酒”,然而聞聲不見人,站起來看時才見是孔乙己坐在門坎上。孔乙己原是穿長衫而站著喝酒的唯一的人,這次卻是坐在門坎上了。以下方說看見他盤著兩腿而且下面墊一個蒲包,直到掌柜的出現,方點出他又偷了東西,被打折了腿,最后方說看見他滿手是泥,因而知道他是用手走來的。假如魯迅并不這么表現,而是換了一種次序,先說遠遠地看見孔乙己匍匐而來,那就要減少很多力量。
《孔乙己》第八段,寫孔乙己分給孩子每人一顆茴香豆,這可以說是全文中最精采的一段描寫。每人一顆,甚至還用五指將碟子罩住,連忙說,“多乎哉?不多也!”這正說明了他那天真可愛的風趣。他喜歡小孩子,小孩子也喜歡他,但他的處境之困難,也實在叫他無可如何。由于這一段描寫,孔乙己的性格就完全活現了出來,而且使我們深深地感到,在這個潦倒的書生身上,還有“人性”存在。作者一再寫他因聽到別人說他偷竊而漲紅了臉,并且說別人憑空污他清白,說偷不算偷,說折了腿是跌斷的,這些不但未曾引起我們的憎惡,反而使我們同情他,感到他的善良與自愛。于是我們相信,那使他陷于這種困窘的,不是由于他自己,卻是由于一種更大的外在的力量了。這正是魯迅在藝術表現上的成功,而在這整個的表現中,卻以第八段為最好。
(原載《國文月刊》第51期,194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