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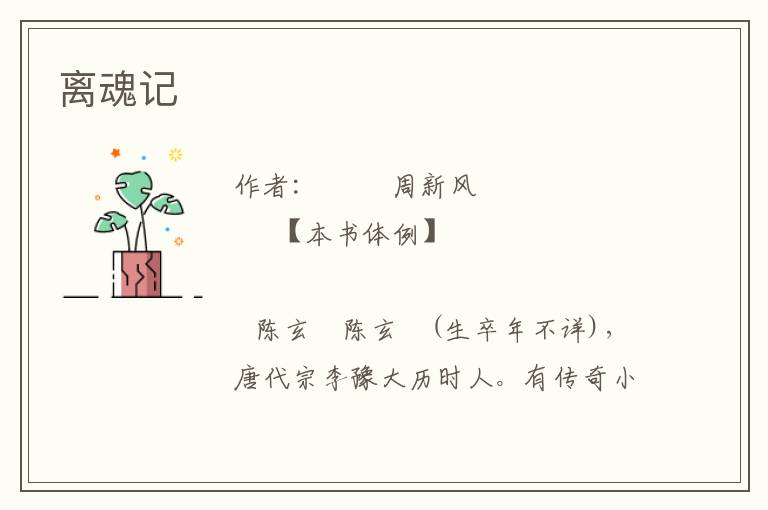
作者: 周新風 【本書體例】
陳玄祐
陳玄祐(生卒年不詳),唐代宗李豫大歷時人。有傳奇小說《離魂記》傳世。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性簡,寡知友。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范。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后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后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郁抑,宙亦深恚(huì會)恨。托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慟,訣別上船。
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xiǎn顯)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夢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于船,連夜遁去。
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nǎng)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
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妝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xī希)然而合為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親朋間有潛知之者。后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并孝廉擢(zhuó濁)第,至丞、尉。玄祐少常聞此說,而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歷末,遇萊蕪縣令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鎰則仲規堂叔祖,而說極備悉,故記之。
(選自《太平廣記》)
唐朝天授三年(692),清河縣張鎰,因為做官的緣故,把家搬到了衡州(今湖南衡陽)。他性情疏簡喜靜,知心朋友很少。他膝下沒有兒子,只有兩個女兒。長女早亡,幼女名叫倩娘,端莊艷麗,無人可比。張鎰的外甥王宙,太原人,自幼聰明穎悟,容貌俊秀。張鎰一直很看重他,常說:“將來一定將倩娘嫁給他為妻。”后來二人各自長大成人。王宙與倩娘常常日夜思念對方,家里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心思。后來張鎰的幕僚中,有一個將赴吏部應選的候補官員求娶倩娘,張鎰答應了他。倩娘聽說后郁悶不樂,王宙也很氣惱,托詞說自己該進京調職,請求離去。張鎰阻攔不住,就送給他一大筆費用。王宙心懷怨憤,與張鎰一家告別上船。
太陽落山時,船行至離州城數里處。夜半時分,王宙還沒有入睡,忽然聽見岸上有一個人的腳步聲,不一會兒來到船邊。詢問是誰,才知是倩娘赤腳步行而來。王宙驚喜得幾乎發狂,拉著倩娘的手問她從哪里來。倩娘說:“你對我如此深情厚意,我睡夢中都感覺到了。現在父親違背我的意愿,要將我另嫁他人。我知道你深情不變,想舍身相報,這才逃離家庭來投奔你”。王宙大喜過望,高興得手舞足蹈,就將倩娘藏在船上,連夜逃走。
他們加倍趕路,幾個月后到了四川。在這里一共生活了五年,生了兩個兒子,與張鎰從無書信來往。妻子倩娘常常思念父母,哭著說:“我從前不忍辜負你,背棄禮義趕來投奔,到如今五年了,和父母難以相見,我還有何面目活在世上?”王宙憐惜她,勸她說:“我們這就回去,你不要傷心。”于是一家人動身回衡州。
到了衡州,王宙獨自一人先來到張鎰家,首先為自己與倩娘私奔之事道歉。張鎰說:“倩娘病在閨房中好幾年了,你為什么要編造出這樣的謊話!”王宙說:“倩娘如今就在船上。”張鎰大驚,急忙派人去驗證真假。果然看見倩娘在船上,臉色和悅歡欣,向來人詢問:“父母大人可安康?”家人驚奇竟有這種怪事,趕緊跑回去報告張鎰。閨房中的倩娘聽說后,歡喜地從床上起來,梳妝打扮換上新衣服,微笑不語,走出房來和船中的倩娘相互迎接,竟然合為一體,二人的衣服也都重疊在一起。張家認為此事不正常,不敢對外聲張,只有親屬中有暗地里知道的。
此后四十年中,倩娘夫妻先后去世。兩個兒子都由孝廉登科及第,官至縣丞、縣尉。我小時候經常聽人說起此事,但說法多不一樣,有的說那都是虛構的。大歷末年(779),遇見萊蕪縣縣令張仲規,他完整地述說了事情的本末。張鎰就是仲規的堂叔祖,所以張仲規說得很詳細,我就將它記載了下來。
古時候人們認為,人是由血肉之軀和靈魂所組成;靈魂又是可以離開軀體的。這便有了失魂之說,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就有一篇作品題為《招魂》。陳玄祐的這篇《離魂記》正是借用了這一失魂之說,構思了一個動人的愛情故事,從中抒發出封建社會人們對美好愛情生活的向往。
故事的主人公倩娘與王宙兩情相悅,本極符合封建社會中的姻緣模式——即父母之命。如果沒有意外,有情人成眷屬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正當二人“常私感想于寤寐”時,張鎰卻出爾反爾,又將女兒許給“賓寮之選者。”為此,倩娘郁悶不樂,王宙“亦深恚恨”,兩代人之間的沖突也由此而起。
王宙憤而離開張家,表達了對舅父的不滿,但思念倩娘之情,卻使他夜半難眠。倩娘感其“深情不易”,遂“徒行跣足”、“亡命來奔”,也表現出對愛情的忠誠,對禮義的背棄。一對有情人,“倍道兼行”,連夜而去。蜀地生活五載,生育二子。倩娘思念父母,一家人“俱歸衡州”。至此,作品似乎是對現實生活中某一對青年男女私奔故事的客觀再現,雖然也有其思想價值存在,但在眾多反映愛情生活的文學作品中卻落入了俗套。
作者陳玄祐的高明之處正在于他的作品來源于生活,卻又遠遠地高于生活。在這個較為圓滿的愛情故事接近尾聲之際,又異峰突起,交待出離家出走的乃是倩娘的“離魂”,而倩娘本人則“病在閨中數年”。這樣就促使人們去重新思索作品的真正寓意。
我們認為,小說末尾對倩娘靈魂出走的揭示,使得這篇作品本身無論是在藝術上,還是在思想內容上都有了更深刻的含義。首先,它顯示了作者奇特的藝術想像力,使作品打破了一般小說的構思模式,而在虛幻中有真實,真實里有虛幻。其次,它使小說的主題思想在已有的反抗包辦婚姻、追求愛情幸福的基礎上,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它顯示出愛情是什么力量也禁錮不住的,即使能阻擋住肉體,卻擋不住靈魂的向往。小說中的倩娘,人雖呆在閨中數年,其離魂卻追隨意中人而去,就極形象地闡明了個中道理。不僅如此,作者又以其浪漫主義的藝術想象,將愛情的力量給予了合乎情理的夸張。我們看到,失去了靈魂,失去了愛情,倩娘久病在床,不過是徒具人的外形罷了。而她那出走的魂靈則顯得那么真實可愛,富有極強的生命力,不僅能與王宙私奔至蜀,而且還能“生兩子”。這看似荒唐怪誕的情節,卻是作者對人世間至情至理的揭示。
倩娘,一個美麗的女子;離魂,一個自由的芳魂。這一形象,這一魂靈,超越了時間、空間,不僅在元代鄭光祖的雜劇《倩女離魂》中再度出現,即便是時至今日,仍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