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guó)文藝美學(xué)要略·論著·《圖畫(huà)見(jiàn)聞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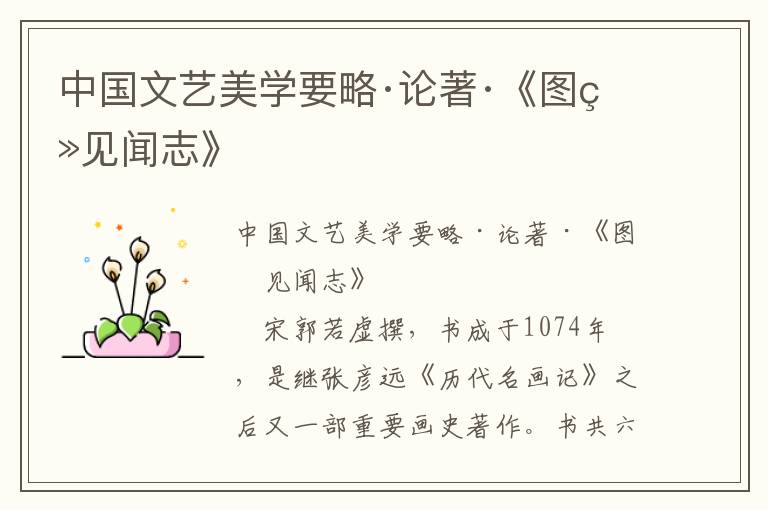
中國(guó)文藝美學(xué)要略·論著·《圖畫(huà)見(jiàn)聞志》
宋郭若虛撰,書(shū)成于1074年,是繼張彥遠(yuǎn)《歷代名畫(huà)記》之后又一部重要畫(huà)史著作。書(shū)共六卷,第一卷《敘論》十六篇,是郭若虛主要美學(xué)觀點(diǎn)所在。第二卷至第四卷是《記藝》,即畫(huà)家傳。第五卷為《故事拾遺》,第六卷記《近事》,材料豐富,為研究畫(huà)史提供了重要材料。
在《敘論》中,郭若虛首先指出了繪畫(huà)藝術(shù)的社會(huì)職能。他說(shuō):“蓋古人必以圣賢形象,往昔事實(shí),含毫命素,制為圖畫(huà)者,要在指鑒賢愚,發(fā)明治亂。”他把人物畫(huà)提到了各類繪畫(huà)的首位。強(qiáng)調(diào)畫(huà)各種人物時(shí),應(yīng)該有“制作楷模”:“釋門則有善功方便之顏,道象必具修真度世之范,帝王當(dāng)崇上圣天日之表,外夷應(yīng)得慕華傾順之情,儒賢即見(jiàn)忠信禮義之風(fēng),武士固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俄識(shí)肥遁高世之節(jié),貴戚蓋尚紛華侈靡之容,帝釋須明威福嚴(yán)重之儀,鬼神乃作丑䰩馳趡之狀,士女宜富秀色婑媠之態(tài),田家自有醇甿樸野之真。”這是把各種人物類型化,指出了各類人物的共同性,但卻忽略了具體人物的個(gè)性要求,因而易使繪畫(huà)走向模式化。
郭若虛非常推崇謝赫的六法論,特別是“氣韻生動(dòng)”一條。他說(shuō):“凡畫(huà)必周氣韻,方號(hào)世珍,不爾,雖竭巧思,止同眾工之事,雖曰畫(huà)而非畫(huà)。”他對(duì)“氣韻生動(dòng)”的觀點(diǎn)推崇備至,并認(rèn)為, “六法精論,萬(wàn)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者可學(xué),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fù)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huì),不知然而然也”。他把“氣韻生動(dòng)”當(dāng)作區(qū)別畫(huà)家與工匠畫(huà)的標(biāo)準(zhǔn),還說(shuō)對(duì)其只能生而知之,并非通過(guò)長(zhǎng)期磨練可以得到的。他還說(shuō): “氣韻本乎游心,神彩生于用筆。”這就是說(shuō),氣韻不是由客觀產(chǎn)生,而是源于作者的主觀頭腦。關(guān)于如何才能達(dá)到氣韻生動(dòng),郭若虛說(shuō): “竊觀自古奇跡,多是軒冕才賢,巖穴上士,依仁游藝,探賾鉤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畫(huà)。人品既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高矣,生動(dòng)不得不至。”這不僅把繪畫(huà)當(dāng)作了上層少數(shù)人抒發(fā)“高雅之情”的工具,而且把氣韻直接歸結(jié)于作者的人品了。 郭若虛的觀點(diǎn),影響巨大, 以至成為后來(lái)士大夫畫(huà)家自我標(biāo)榜的理論根據(jù)。
郭若虛的美學(xué)思想,從人品決定氣韻出發(fā),特別重視繪畫(huà)的風(fēng)格美。他評(píng)論畫(huà)家作品時(shí),多著眼于風(fēng)格的美丑,如董源是“秀潤(rùn)”,李符是“雅淡”,胡九齡為“瀟灑”,汪士元?jiǎng)t“清奇”。他鄙薄的是陳用智“格缺清致”,高克明“殊乏飄逸之妙”,孫太古則“傷豐滿,乏清秀”等等。他認(rèn)為徐熙和黃筌兩家的區(qū)別是“黃家富貴,徐熙野逸。”并指出這種不同的原因在于,一是“各言其志”,二是“耳目所習(xí)”。他從畫(huà)家主觀思想情趣和客觀生活環(huán)境兩方面,論證了風(fēng)格形成的根源,這一點(diǎn),對(duì)文藝美學(xué)中風(fēng)格這一范疇的研究,不無(wú)啟發(f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