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guó)文藝美學(xué)要略·學(xué)說(shuō)與流派·文德說(shu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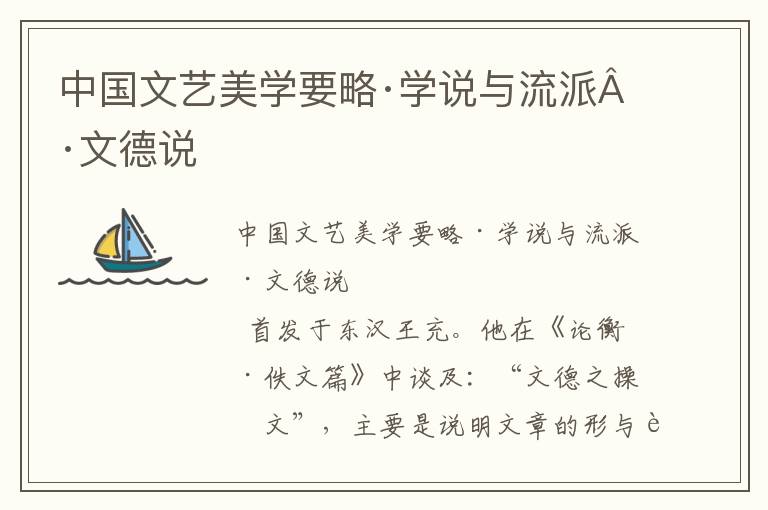
中國(guó)文藝美學(xué)要略·學(xué)說(shuō)與流派·文德說(shuō)
首發(fā)于東漢王充。他在《論衡·佚文篇》中談及:“文德之操為文”,主要是說(shuō)明文章的形與質(zhì)務(wù)求一致,因?yàn)椤胺蔽柠愞o”便是言過(guò)其實(shí), “無(wú)文德之操”。這是針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形式主義流弊而發(fā)。
文德專(zhuān)指作品的品質(zhì)和作用的,見(jiàn)于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篇中: “文之為德也大矣”。至北齊楊遵彥,文德則已有作者的道德修養(yǎng)的涵義。 《魏書(shū)·文苑傳》中載有楊氏所作《文德論》,內(nèi)曰:“以為古今辭人,皆負(fù)才遺行,惟邢子才、王元景、溫子升彬彬有德素”。
對(duì)文德論述最詳者當(dāng)推清代章學(xué)誠(chéng)所撰《文史通義》內(nèi)篇中的《文德》一文,然而具體含義已與上述諸說(shuō)有異。他認(rèn)為: “未見(jiàn)有論文德者,學(xué)者所宜深省也”。這里的文德謂“著書(shū)者之心求也”,其實(shí)是指著作者和批評(píng)者的態(tài)度修養(yǎng):作者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須“敬”,批評(píng)者的態(tài)度則須“恕”,所謂“凡為古文辭,必敬以恕”。就“敬”而言,如“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于水,言為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 “敬”就應(yīng)包括“修德”和“養(yǎng)氣”兩方面的功夫,而其根本則在于“修辭立誠(chéng)”。章氏顯然是從儒家美學(xué)立場(chǎng)來(lái)解釋“敬”的,即要使它合乎“從容中道”,其消極性不難見(jiàn)出。而“恕”則是一種既不苛求古人,也不一味寬容,而是“能為古人設(shè)身而處地”的態(tài)度。批評(píng)者必須深知“古人之世”,而且要能深知古人“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yōu)樂(lè)之不齊”,不以一種恒定的模式度量一切古人。只有這樣,才有較為恰切的批評(píng)結(jié)論。這無(wú)疑是孟子的“知人論世”觀念的進(jìn)一步發(fā)揮,不無(wú)合理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