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美學基本理論·主從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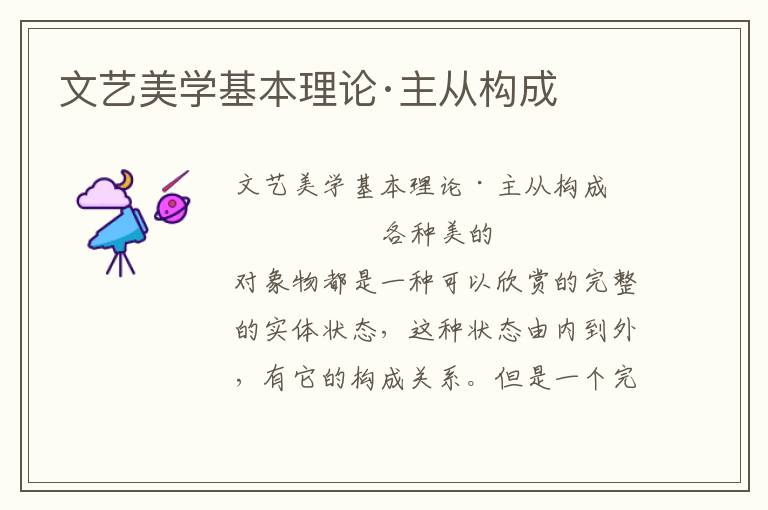
文藝美學基本理論·主從構成
各種美的對象物都是一種可以欣賞的完整的實體狀態,這種狀態由內到外,有它的構成關系。但是一個完整狀態的構成,在一定的網絡關系上,必然表現為主導與從屬,并由此派生為整體與局部、起始與承續等關系狀態。
主導與從屬關系。這是事物的矛盾關系中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導方面的法則造成的。在自然美與藝術美的對象中,都是如此呈現著。比如日落的景色中,不論在天宇中,還是在山河上,落日在一段有限的時間內,就成為這個范圍內的主導景物,襯托它的或是大漠孤煙,或是長河映照,或是歸舟浮海,或是余霞鋪錦,如果沒有特定的主題及種種襯托,就構不成落日時刻的美。云南石林中“母子攜游”,如果沒有天然生成的處于前端位置的宛似母親的石柱,后邊的那個有似童子的矮石柱,就不會取得現有情況下的觀賞和審美價值。在藝術作品中,主次或賓主關系就更為突出了。一部塑造人物形象的作品,有多種人物,其中必有處在中心地位的主要人物,如《哈姆萊特》中的哈姆萊特, 《祝福》中的祥林嫂。一部頭緒繁多的小說,情節雖然復雜,但其中必有主線,如《紅樓夢》中的愛情線索。《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對珂賽特的撫育過程。在美術作品中,如《拉奧孔》群雕的中心不僅在拉奧孔身上,更在其臉部,整個雕像群的律動所向,都灌注于這個主導部位。 《最后的晚餐》中,以耶穌為中心,構成與十二個門徒的有機聯系。如果離開了這個中心,畫面上的一切都將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藝術美是由各部分綜合成的有中心的整體。
整體與局部關系。整體與局部關系是從主從關系派生的,但又不同于主從關系。因為主從關系中的對立面都是實體存在的部分,只是所處的地位不同;而整體與局部關系中的整體并不是單獨存在部分,而是由許多局部構成的,只是在美的形式構成時,任何局部都必須是整體的一個和諧有機的部分。一部多幕多場的戲劇,它是一個整體構成,但整個見諸于各個分體部分,每幕每場都必須與整體相聯系,達到增之則多,減之則少的地步。比如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散曲中的“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這其中以天涯斷腸人的所見,掃視存在于秋郊的十種景物,它們每一部分都與整體密切聯系著,構成了秋途夕照中宇宙荒涼、生意衰竭、悵觸無邊、希望斷絕的形象畫面。庫爾貝的畫《篩麥的女子》中,處于畫面中心位置的篩麥農婦,她動作熟練,姿態優美,但明顯表露了持續勞動后的疲乏感。在這個疲乏的人物形象上,畫家特意畫了她的兩只被拖帶的鞋子,右腳上的一只已經大半脫腳掉落,這個局部表現,是從神經到生理真正疲乏的一個透視窗口;又與畫面上另一斜倚在麥袋上挑麥粒的婦女,以及打掃風車的男人形成和諧襯托。
起始與承續關系。這是事物按照規律運動,以及藝術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在結構形式上的具體表現。我們在欣賞自然美的時候,比如站在黃山的蓮花峰頂,看腳下的群峰蜿蜓,在云霧繚繞中綿亙不盡,這山連山,云繞云,峰回路轉、松石點綴的景色構成中,存在著一種起始與承續關系。作為人自覺創造加工而成的藝術作品,這種意味是更強的。如賀知章的詩《回鄉偶書》,在結構形式上最主要的特點,就是起始與承續關系的處理巧妙,使詩句連環遞進,波瀾跌宕,造成了特殊的感人效果。如首句起始于“回”,這個“回”是“少小離家老大回”,詩情里蘊含的是一個“久”字。 “久”又作為一個原因遞進到第二句: “鄉音無改鬢毛衰”。 “鬢毛衰”是“久”的結果;而“鄉音無改”,正表明鄉情之深。這就成了第三句詩“兒童相見不相識”的原因:那些小孩子看見與自己講著同樣口音的老人從外地來此,鄉音熟悉,因而交談無礙,面容陌生,故而發問。這樣,第四句“笑問客從何處來”,自然應勢而成。賀知章的這首膾炙人口的千古名篇,每一句都是結構律式中不可移易的部分,它的獨特的藝術美也正在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