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鳴上筮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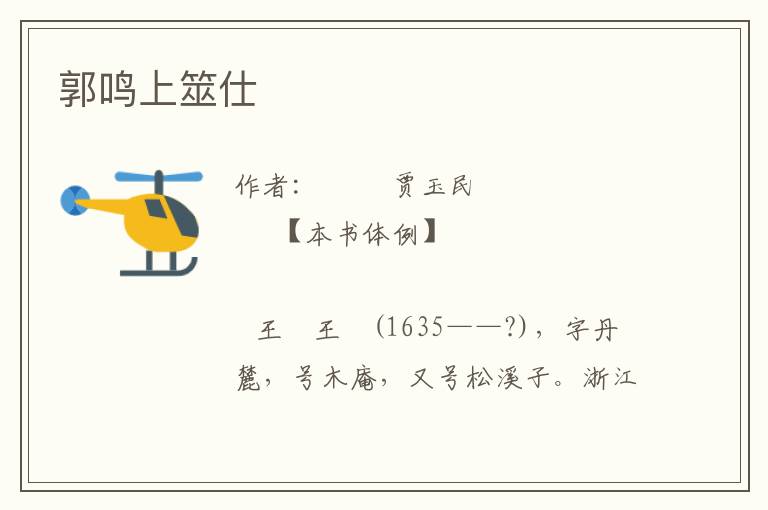
作者: 賈玉民 【本書體例】
王晫
王晫(1635——?),字丹麓,號木庵,又號松溪子。浙江錢塘(今杭州)人。二十八歲時患喉病幾死,醫生以為讀書過苦所致,遂棄舉子業。博覽群書,又好賓客,文人名士多與交結。著有《遂生集》、《霞舉堂集》、《雜著十種》、《墻東草堂集》等。所著筆記小說《今世說》八卷,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刻,以后有多種刻本。仿《世說新語》體例,記清初以來文人軼事。
郭鳴上筮(shì士)仕,授昆山縣令。縣故劇難治,吏人且多豪猾。郭赴官,未至縣五百里,吏人十數輩迎于道。乃詐稱疾不起,自懷部牒間道行,一晝夜抵縣。守縣吏方會飲堂廡,見一老書生儀狀樸野,直上堂踞坐,皆大怒,叱逐之,不肯去。視其手中所持,若文書狀,迫視之,則部給昆山知縣牒也。大驚,互相推擠,仆堂下。前迎令者,怪疾久不出,伺得其故,亦馳歸,適至,共叩頭請死罪。郭笑遣之。吏愈恐不肯起。乃諭之曰:“若所為,我盡知之。今為若計,欲舞文亂法快意一時,而身陷刑戮乎?欲守公奉法、飽食暖衣、與妻子處乎?”皆曰:“欲飽暖守妻子耳。”曰:“果爾,我今貸若罪,后有犯者,殺無赦!”吏皆涕泣悔悟,終郭任無犯法者。
(《今世說》卷二政事)
郭鳴上出來做官,被任命為江蘇昆山縣令。這個縣本來非常難于治理,而且衙門的吏役人員又多是豪強不法之徒。郭上任途中,離昆山還有五百里,而昆山縣衙的吏役十多人就趕去于道上迎接。郭鳴上于是假托生病不能起來接見他們,而暗中自己帶著吏部的任命書從小路走了,一晝夜就到達了縣里。看守縣衙的吏役們正在大堂旁宴會聚飲,見一個老書生,樣子土里土氣,徑直走上大堂就坐到了縣太爺的位子上。眾人大怒,呵叱著攆他,他也不肯離開。吏役們看到他手中拿著一件文書樣的東西,挨近一看,原來是吏部給昆山知縣的任命書。眾人大驚,你推我擠,紛紛跪倒在堂下。被派去迎接縣令的人,也奇怪他為什么病這么久不出來,等探聽清了原因,也迅速返回,恰好趕到,于是都一齊叩頭請罪。郭鳴上笑著讓他們走開,這些吏役們更加恐懼,不肯起來。郭鳴上告誡他們說:“你們的所作所為我都知曉了。現在替你們打算,是想舞文弄墨、貪贓枉法,得意一時,最終判刑、殺頭呢,還是想奉公守法、飽食暖衣、與老婆孩子歡歡樂樂呢?”都回答說:“我們不過想飽食暖衣、與老婆孩子常相守而已。”郭鳴上道:“果真是那樣的話,我今天就寬恕了你們的罪過,以后若有違犯者,定然殺無赦!”吏役們個個痛哭流涕決心悔改,一直到郭鳴上任期滿了沒有一個犯法的。
在封建社會里,“官”和百姓等級森嚴,很少有直接接觸的機會,這些吏役們便是“官”與百姓的中介,他們或為虎作倀、狐假虎威,欺壓良善;或舞文弄墨,貪贓枉法。糊涂官則放縱他們為所欲為,即使是“清”官,也免不了受其愚弄、挾制。本篇所寫的昆山縣之所以難于治理,重要原因就是吏役們“且多豪猾”。新縣令要來上任,他們竟迎出五百多里,企圖以其奉承的故伎把新縣令籠絡;面對那“儀狀樸野”的“老書生”則又那樣豪橫,“皆大怒,叱逐之”;當發現此“老書生”即是縣令時,又驚恐萬狀,“互相推擠,仆堂下”,“共叩頭請死罪”,何前踞而后恭!郭鳴上這個縣令對他們的懲治真是令人發噱而感到痛快。作者對這輩人似乎十分熟悉,對其一舉一動都能洞悉其心理。如當郭鳴上“笑遣之”時,他們反而“愈恐,不肯起”,為什么?因為他們這些久混官場的人物,自知本來面目已被縣令看破,但尚未得到縣令明確的寬恕,如何肯走呢?只有等郭鳴上說出“我今貸若罪”的話之后,他們才感到有了保障,才“涕泣悔悟”而去。
因此,要想當清官,想當一個有所作為的官,往往需從擺脫吏役的蒙蔽著手。明代蘇州知府況鐘,初到蘇州時,“佯不解事”,表面上裝傻,對公事處理都聽吏役的意見,這些人十分高興,“謂太守愚”。沒想到況鐘私下里調查個明白,一個月后,集合吏役,一件件都擺得清清楚楚:哪些事該辦,你們阻止了;哪些事不該辦,你們慫恿我辦了。必然是你們受了賄賂,才故意這樣作的!一下子把吏役們治得老老實實,成為著名的清官。本篇的郭鳴上之所以要先給吏役們一個下馬威,大約也因為他出身貧寒,對吏役之害有所體會。郭鳴上是山西省介休縣人,四十歲時才以老秀才的資格被貢舉入京,任命為昆山縣令,可見其半生坎坷,對下層社會的呼聲應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他上任時沒有什么隨從,仍然是“儀狀樸野”的本色,甚至避開大路,特意從小路“一晝夜,抵縣”,觀察吏役們的真相。然后對他們恩威并用,指明出路,治服了他們,使得他們“終郭任無犯法者。”作者在這不足三百字的短文中,從外貌,從行為,從擲地有聲的語言,把這個形象寫得十分生動。當然,象這樣的“好官”,在那時是太少了,而且郭鳴上本人不久也就去世了。因其大得民心,所以“吏民聚哭于庭,闔縣皆罷市往吊”。郭鳴上的遺物只有幾件破衣裳,而且也沒有兒子,遺體沒法運回故鄉,昆山縣的人們就把他葬在了本縣馬鞍山,并建廟祭祀。葬殯那天,其他縣的人都來了,有幾萬人參加,“吏民哭之,如其私親”。可見愛民者,民亦愛之;脫離人民者,人民當亦棄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