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寶中《河灘上的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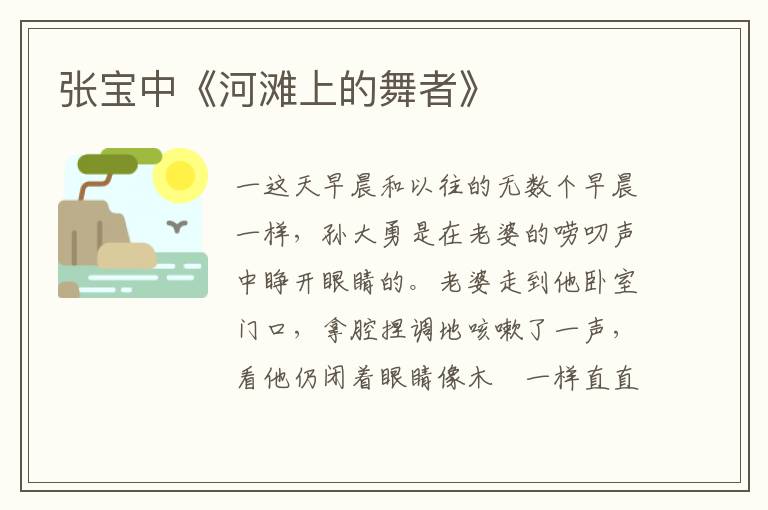
一
這天早晨和以往的無數(shù)個早晨一樣,孫大勇是在老婆的嘮叨聲中睜開眼睛的。老婆走到他臥室門口,拿腔捏調(diào)地咳嗽了一聲,看他仍閉著眼睛像木條一樣直直地躺著,就開始嘮叨:“你就是一頭豬,只知道吃和睡。工作都找了一個月了還沒著落,居然還睡得這么香。家里只有三萬多塊錢了,孩子上學(xué)正是花錢的時候,一點(diǎn)都不知道發(fā)愁。你的體重應(yīng)該比正常人輕一些,因為你沒心沒肺。”
老婆嘮叨著走開了,去拉窗簾、開窗戶,然后去衛(wèi)生間洗漱。這當(dāng)兒,孫大勇翻了個身,睜開眼睛,面對著白色的墻壁,咧著嘴得意地笑。老婆洗漱完畢,去廚房做早飯,同時又開始了嘮叨:“咱們可是說好了,一個月以內(nèi)必須找到工作,可是今天已經(jīng)是第三十天了。今天你要是再找不到工作,就死外面別回來了。”
孫大勇的老婆以前不愛嘮叨,是從最近三四年開始愛嘮叨的。對她來說,嘮叨就像呼吸一樣,是一種生理需求。看見衣服扔在沙發(fā)上,看見茶杯沒蓋蓋,看見飲水機(jī)反復(fù)加熱……都禁不住嘮叨。想起一些陳谷子爛芝麻的舊事也嘮叨。這些舊事包括:和孫大勇談戀愛的時候,孫大勇經(jīng)常給她做魚吃,結(jié)婚后一次都沒做過;孩子小的時候,上幼兒園都是她接送,孫大勇從來沒管過;十年前孫大勇有過一個相好,當(dāng)時周圍人都知道了,只有她一個人蒙在鼓里;她過生日,孫大勇從來沒給她買過一件禮物;結(jié)婚十八年,孫大勇從沒陪她逛過街……
為了躲避老婆的嘮叨,三年前孫大勇開始和老婆分屋睡。他家的房子是兩室兩廳,老婆睡臥室,女兒睡書房,他睡飯廳。飯廳和廚房連著,中間有一扇推拉門把兩個空間隔開,就成了一個獨(dú)立的空間;吃飯只能在客廳。這間本來是飯廳的臥室只有八平方米,放一張單人床,放一張電腦臺,再放一個衣櫥,就滿滿當(dāng)當(dāng)?shù)牧恕?/p>
每天晚上,孫大勇都把自己關(guān)在這間小屋里,在網(wǎng)上看新聞、聽音樂、斗地主。老婆在客廳里,蜷縮在沙發(fā)里看電視;她喜歡看相親節(jié)目、娛樂節(jié)目和電視劇。電視里插播廣告的時候她會大聲問:“你在干嗎?”孫大勇大聲說:“沒干嗎。”老婆又問:“沒干嗎,那你在干嗎?”孫大勇大聲說:“沒干嗎,就是沒干嗎。”有時候,孫大勇在網(wǎng)上看到了駭人的新聞,比如飛機(jī)失聯(lián)、客輪沉沒等,就會呼地從電腦臺前站起來,抬腿往客廳走,想和老婆說說。可是,當(dāng)他開了門探出腦袋,看見老婆正張著嘴對著電視機(jī)哈哈大笑時,又把腦袋縮了回來,輕輕地關(guān)上門。他坐下來,使勁伸著脖子盯著電腦顯示器,不住地驚嘆,自言自語地發(fā)一通感慨。
老婆做早飯的時候,孫大勇麻利地起了床。今天他穿了黑色的西褲、白色的短袖襯衫、锃亮的黑皮鞋,看上去很精神。老婆在廚房里把鍋碗瓢盆弄得叮當(dāng)響,透過推拉門的玻璃瞄了他一眼,說,四十好幾的人了,孩子都上高中了,還打扮得跟相親似的,真是腦袋瓜子進(jìn)水了。孫大勇進(jìn)了衛(wèi)生間,把門插上,還開了燈。蹲完馬桶,洗漱完畢,他在這個狹小封閉的空間里,嘴里哼著優(yōu)美的曲子,肩放平,膝放松,大腿和臀部夾緊上提,抬頭,挺胸,收腹,立腰,轉(zhuǎn)胯,旋轉(zhuǎn),留頭……他跳起了拉丁舞。
孫大勇迷上拉丁舞有半個多月了。
一個月前,也就是五月中旬,孫大勇失去了工作。這是他第二次失去工作。第一次是九年前,他所在的服裝廠倒閉了。他們廠沒有自主品牌,主要業(yè)務(wù)是承攬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一些服裝企業(yè)的來料加工,賺取加工費(fèi)。他的崗位是倉庫搬運(yùn)員,工作不太累,收入還湊合。他曾打算這輩子就當(dāng)搬運(yùn)員了,一直當(dāng)?shù)酵诵荨]想到,在他當(dāng)了十四年搬運(yùn)員之后,那些客戶終止了合作,服裝廠倒閉了。孫大勇的老婆也在廠里,是縫紉工,和他同時下了崗。之后,老婆一直在一家超市做理貨員,每天早晨九點(diǎn)準(zhǔn)時出門,風(fēng)雨無阻。孫大勇則在一家高檔寫字樓干物業(yè),具體工作是管道維修。他每天穿著咖啡色的工裝,工具包里背著扳子、鉗子等工具,在各個樓層穿梭。他那身工裝很像電影里舊上海英租界巡捕的制服,褲腿還有些短,看上去很滑稽。“巡捕”一當(dāng)就是九年。一個月前,那家高檔寫字樓更換了物業(yè),他就第二次失去了工作。
從失去工作的第二天開始,除了周末,孫大勇每天都騎著電瓶車,帶著晚報的招聘專版出去應(yīng)聘。卻總是無功而返。他沒文憑沒技術(shù),年齡又大,那些用人單位讓他等通知,然后就沒有然后了。他想繼續(xù)在物業(yè)公司干管道維修,可是跑了幾家物業(yè)公司,都不需要人。他原以為自己不缺胳膊不少腿的,找個工作是小菜一碟,沒想到那么難。時間一天天過去,他心里也越來越惶恐不安。他仿佛跌進(jìn)了深不可測的谷底,使出吃奶的勁兒也爬不上來;又仿佛在漆黑的地道里爬行,一絲光亮都看不到,不知道該往哪兒爬、能不能爬出去。
孫大勇真想去建筑工地上搬磚,真想騎電瓶車跑快遞、送外賣,真想去農(nóng)貿(mào)市場租個攤位賣菜,真想每天早起炸油條、攤煎餅馃子,真想在小區(qū)看大門。甚至真想收廢品。他們小區(qū)院子角落里有幾間物業(yè)的平房,有個從農(nóng)村來的收廢品的老頭兒租住在那里,晚上聽收音機(jī)打發(fā)時間,一天三頓吃面條,身上總有一股刺鼻的汗臭味。他很羨慕那個老頭兒,真想向老頭兒請教請教這一行的規(guī)矩,然后自己也買一輛三輪車、一桿秤,去別的小區(qū)收廢品。只要有事干有錢賺,不怕出大力流大汗,干什么都情愿。可是,這些營生他是不能干的,因為會給老婆和女兒丟人。
半個月過去了,孫大勇找工作沒著落,老婆就讓他去連襟的物流公司或小舅子的飯店上班。連襟和小舅子都表示愿意接納他,并安排他從事“管理工作”。比起搬磚、收廢品等,不知舒服多少倍。可孫大勇心里已打定主意,哪怕讓他干副總,他都不干,因為那畢竟是“寄人籬下”。連襟和小舅子都是能人,喜歡穿西服打領(lǐng)帶,頭發(fā)梳得像狗舔的一樣,看上去牛哄哄的。連襟比他小四歲,和他說話的時候一口一個“大勇哥”,臉笑得跟菊花似的。但他知道,如果他成了連襟的下屬,連襟那張臉就不總那么好看了。小舅子的飯店他更不能去,因為十年前的那次外遇,他被小舅子揍掉了一顆后槽牙,至今看見小舅子還想咬,哪能再去端他的飯碗?做人,總要有一點(diǎn)骨氣的。他咬著后槽牙向老婆承諾:一個月內(nèi)一定找到工作。他繼續(xù)帶著晚報的招聘專版,一家一家地去報名、面試。
這段時間,孫大勇每天晚飯后都出去走走。一天晚上,在一家休閑廣場,他被吸引住了。在廣場一角,有人用繩子圈了一個邊長大約七八米的正方形,花花綠綠的繩子固定在四輛電瓶車上。正方形里面有二十多個人,五六個男的,其余都是女的,一個六十歲左右的老男人正在教拉丁舞。老男人高高的瘦瘦的黑黑的,大長臉,抬頭紋很密,眼皮有些耷拉,因而眼睛成了三角眼。打扮得卻像個文藝青年:長頭發(fā)扎成馬尾辮,穿著印有杰克遜頭像的黑色短袖T恤、滿是口袋的黑色休閑長褲、馬靴一樣的黑色休閑皮鞋。他腰里掛著個揚(yáng)聲器,麥克風(fēng)在嘴邊,不斷地向大家發(fā)出各種指令:方形步、影子位、古巴搖擺……老男人還不時放著音樂跳給大家看,那么個老男人舞居然跳得很火辣很魅惑。
看著那個老男人跳拉丁舞,孫大勇忽然頭皮發(fā)麻,脊梁溝子發(fā)緊,腦子里冒出一個念頭:我也要跳拉丁舞。他站在那個四方形外面發(fā)了很長時間的呆。散場的時候,他問老男人學(xué)費(fèi)是多少,老男人說二百塊錢包教包會。他急忙從褲兜里掏出錢來,把兩張百元鈔票塞進(jìn)老男人手里。老男人說明天他就能來跟著學(xué)了。
孫大勇白天在外面找工作,晚上在廣場上學(xué)拉丁舞。找工作還是沒眉目,學(xué)拉丁舞卻漸入佳境。老男人鼓吹說,拉丁舞是催生愛情的魔法舞蹈,是穿著衣服的性挑逗;還是一項絕好的健身運(yùn)動,能充分釋放情緒、減輕精神壓力,同時對腰、腹、臀部曲線塑造作用明顯。孫大勇從沒想過要挑逗什么人,也沒打算塑形,但卻明顯感覺到心態(tài)的變化:一跳起拉丁舞,他就覺得自己像換了一個人,不是下崗工人孫大勇了,而是另外一個人:這個人上過大學(xué),是大公司的白領(lǐng),月薪上萬,像紳士一樣優(yōu)雅;老婆是知識女性,漂亮、溫柔、賢惠、端莊、大方;孩子很優(yōu)秀,將來上清華、北大沒問題,讀了碩士讀博士。孫大勇還有一個神奇的感覺:一跳起拉丁舞,身體就像長出了翅膀,簡直能飛起來。
吃飯的時候,老婆向?qū)O大勇下了最后通牒。雖然是口頭形式,但語氣之嚴(yán)肅比打印在紙上的通知都正式。內(nèi)容如下:第一,按照承諾,今天是找工作的最后一天,必須找到;第二,如果今天沒找到工作,要么死外面別回來,要么從明天開始去妹夫的物流公司或弟弟的飯店上班。
孫大勇吃完飯出門的時候,老婆圍著圍裙、掐著腰站在門口,又把最后通牒重復(fù)了一遍。他打量了老婆一眼,發(fā)現(xiàn)老婆的眉毛描得一邊高一邊低、一邊粗一邊細(xì),看上去很有喜劇效果。他盯著老婆的眉毛,皺了一下眉頭,咂巴了一下嘴,挎上那只黑色帆布挎包開門下樓去了。
二
按照約定,孫大勇今天上午十點(diǎn)和下午兩點(diǎn),分別到一家保潔公司和一家高級會所面試。
從他家到那家保潔公司,騎電瓶車頂多需要二十分鐘。也就是說,他九點(diǎn)半出門都不晚。但他不到八點(diǎn)就出了門。他不知道時間怎么打發(fā),就騎著電瓶車在大街上慢慢轉(zhuǎn)悠。
路過這座城市最著名、在全國也很著名的那家百年學(xué)府門口時,孫大勇看見一個大學(xué)生模樣很像自己的女兒的女孩子。那女孩子身材高挑,長發(fā)披肩,上身穿一件淺黃色的短袖T恤,下身穿一件緊繃繃的牛仔褲,腳蹬白色休閑鞋,走起路來步子很輕盈,腳底下像裝了彈簧。女孩子懷里抱著一摞書,裊裊婷婷地走進(jìn)了學(xué)校大門。孫大勇騎著電瓶車跟過去了。女孩子向“物理樓”走去。因時間還早,孫大勇在校園里轉(zhuǎn)悠起來。校園很漂亮,也很安靜。辦公樓、教學(xué)樓、圖書館、學(xué)術(shù)中心都很氣派。樹林、操場也很大,在擁擠的城市里顯得很奢侈。每棟宿舍樓的墻根下都有一大片五顏六色的暖瓶。宿舍窗戶外面晾著花花綠綠的衣服。校園的路上,男孩子一個個朝氣蓬勃,女孩子一個個青春逼人。
在校園里轉(zhuǎn)了一圈,孫大勇在一片樹林里的木椅上坐下來,點(diǎn)了一支煙。他慢慢地吐著煙圈,想起了自己高考的事情。他上中學(xué)的時候?qū)W習(xí)很好,考大學(xué)可以說是手拿把攥。可是高考前兩天,他夜里吹電扇著涼了,得了重感冒。吃了藥進(jìn)考場,結(jié)果在考場上睡過去了。他從小就想上這所大學(xué),高考時填報的第一志愿也是這所大學(xué),可那場重感冒卻讓他成了搬運(yùn)員和“巡捕”。他這輩子也就這樣了,只希望女兒有出息。如果女兒能考上這所大學(xué),將來再讀碩士、博士,他做夢都會笑醒。可惜的是,女兒不太爭氣。
孫大勇的女兒在郊外一所封閉式民辦高中上高二,兩個星期回家一次。那所學(xué)校教學(xué)質(zhì)量較高,幾乎每年都有學(xué)生考上清華、北大。當(dāng)然,學(xué)費(fèi)也不含糊。當(dāng)初孫大勇是到處求爺爺告奶奶托關(guān)系才把女兒送過去的。可是女兒的學(xué)習(xí)成績一直不理想。她談戀愛。老師都把孫大勇叫過去好幾次了。他想勸勸女兒,可這孩子伶牙俐齒,咄咄逼人,說她一句,她有十句等著,他總是被她氣得干瞪眼。這孩子很講究穿,衣服和鞋非名牌不買。有時候說說笑笑,有時候陰著一張臉,好像誰都欠她什么似的。喜歡唱稀奇古怪的聽不清一句歌詞的歌。如果一起看電視,遙控板一個晚上都會在她手里。脾氣像她媽,動不動就扯著嗓子叫嚷。半個月不見她就想得慌,可是她一回家又覺得很鬧心……
孫大勇忽然很想跳拉丁舞。可是,總有三五成群的學(xué)生從附近的小路上經(jīng)過,他又不好意思跳。又坐了一會兒,他騎上電瓶車出了校門,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轉(zhuǎn)悠。路過一家大商場時,孫大勇遇見一個老熟人,他的老相好小宋。
這家商場門口,進(jìn)進(jìn)出出的人比肩接踵,熙熙攘攘。大都是中老年人。從里面出來的人要么提著大包小包,要么推著滿滿當(dāng)當(dāng)?shù)馁徫镘嚒S袀€看上去四五十歲的中年婦女,正彎著腰、撅著屁股,把購物車?yán)锏纳唐芬患靥统鰜恚b進(jìn)大大小小的方便袋里,那些方便袋在地上擺了一大片。她不時直起腰來拍拍手,東張西望;大概因為東西太多,她看起來有些無助。就在她直起腰來東張西望的時候,孫大勇注意到了她,一眼就認(rèn)出她是小宋。他們九年沒見了,小宋看上去老多了,腰身也有些笨了。
孫大勇在距離小宋五六米遠(yuǎn)的路邊停下來,一只腳支地,悄悄地打量著她,心里猶豫著跟不跟她打招呼。猶豫了一會兒,他想起老婆的最后通牒,意識到保潔公司的面試千萬不能耽擱,于是決定不打招呼了。可是,他正要走,小宋卻抬頭看見了他,沖他擺了擺手,大聲說:“哎,孫大勇,你是孫大勇嗎?孫大勇你愣著干嗎?快過來呀,幫我一把!”
孫大勇只好推著電瓶車走到小宋跟前。小宋問他去干什么,他結(jié)結(jié)巴巴地說不干什么。小宋問他今天不上班嗎,他說今天休班。小宋知道他在那家高檔寫字樓干物業(yè)。他本來不愛撒謊,可這次丟掉工作的事卻不愿說。小宋說:“那好,幫我把東西送回家吧。”說著,她把地上那些方便袋往孫大勇的車后座上綁。方便袋里有花生油、醬油、洗發(fā)液、衛(wèi)生紙、火腿等。她自顧自地說,現(xiàn)在物價太高了,這些東西看上去不起眼,就四百多塊呢,幸虧今天商場搞活動優(yōu)惠,省了一百多。還說,她不在老地方住了,搬家了。去年她家的老房子拆了,給了二百多萬的補(bǔ)償,就在這附近一個小區(qū)買了套新房子。還說,孩子他爸出差去外地了,一個多月了還沒回來;兒子去年考上大學(xué)了,在北京。在孫大勇印象中,以前小宋沒有這么多話……
孫大勇小心地推著電瓶車,小宋在后面扶著,一起去小宋家。孫大勇心里想著面試的事,頭上臉上開始出汗。小宋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一些老同事的情況,誰誰誰去外地照看孫子了,誰誰誰跟孩子出國了,誰誰誰去世了等。自從九年前孫大勇從廠里下了崗,他和那些老同事都沒聯(lián)系過,經(jīng)常想念他們。但這個時候,那些老同事的情況他一點(diǎn)都不關(guān)心,小宋的話他也一句都沒記住。
小宋的家到了。很大一個小區(qū),一片嶄新的高樓,綠化也很好。小宋的家在一棟二十二層樓的第十三層。孫大勇幫小宋把那些東西提進(jìn)家。小宋請孫大勇在客廳沙發(fā)里坐下來,她忙著沏茶、找香煙,然后去了臥室。孫大勇抬頭看了一眼墻上的掛鐘,還差幾分鐘就十點(diǎn)了。從小宋家到保潔公司最少需要二十分鐘,面試已經(jīng)晚了。但他又不想錯過這次機(jī)會,于是掏出手機(jī)給公司打了個電話,說非常抱歉,因家里有急事走不開,現(xiàn)在不能去面試,可不可以再約個時間。接電話的是個中年婦女,聲音懶洋洋的,陰陽怪氣地說,哦,家里有急事,那就先忙家里的事吧。孫大勇還想再說點(diǎn)什么,對方已掛了電話。
小宋穿著一身粉紅色的寬松的家居服,從臥室里出來,緊挨著孫大勇坐下來。她看孫大勇一臉汗,問用不用開空調(diào)。孫大勇急忙說不用。說著,他從茶幾上抽了一張面巾紙,擦了擦臉上和脖子里的汗。小宋從茶幾下面捧出兩個直徑大約一尺的花花綠綠的鐵皮盒子,打開,一個是葵花子,一個是西瓜子,兩個盒子都滿滿的。她抓了一把葵花子和一把西瓜子,放在孫大勇面前的茶幾上,招呼他吃。她自己則抓了一小把西瓜子,一粒一粒地扔進(jìn)嘴里,又“噗”地吐出皮來。
孫大勇又看了一眼墻上的掛鐘,已經(jīng)過十點(diǎn)了,不由得松了一口氣。他笨拙地嗑著瓜子,側(cè)臉偷偷地打量小宋,發(fā)現(xiàn)她以前的鵝蛋臉現(xiàn)在變成了圓臉;笑瞇瞇的時候,眼角的皺紋很密,神情居然像個慈祥的老太太;長發(fā)也變成了短發(fā),燙得蓬蓬松松的,一根根的白發(fā)在黑發(fā)中很刺眼;腹部很豐滿,“救生圈”輪廓分明。
小宋嗑著瓜子說,她如今在一家藝術(shù)類的私立學(xué)校當(dāng)宿舍管理員,和另外幾個老娘們兒輪班,隔一天上一天班。那些孩子的家長都很巴結(jié)她們,來看孩子的時候都給她們帶東西,其中瓜子最多,一天到晚嘴不閑著都吃不完,幾個人就分了帶回家去。學(xué)校里有個小游泳池,她每次去上班都抽空游一個小時。她本來對游泳不感興趣,但本校職工游泳是免費(fèi)的,不游白不游,她和幾個老娘們兒就都學(xué)會了。小宋問孫大勇會不會游泳,孫大勇說不會,他是個旱鴨子,如果跳進(jìn)深一些的水里,肯定會淹死。小宋有些驚訝地問,你真的不會游泳?孫大勇說,我不會游泳很奇怪嗎?小宋笑了笑說,游泳很好學(xué)的,沒想到你不會。
說到在水里淹死,小宋忽然想起了他們的一個老同事,電工小羅,半年前猝死了,才四十六歲。小羅下崗后開出租,開的是夜班,有一天早晨交班后回到家里,忽然很想穿剛買的新衣服。他把新衣服找出來換上后,坐在沙發(fā)里翻報紙,翻著翻著,腦袋忽然往沙發(fā)靠背上一耷拉,眼睛一閉,沒氣了。小宋感慨地說,她越上歲數(shù)越怕死,年輕的時候覺得屬于自己的日子多著呢,沒想到一眨眼就老了。半夜醒來的時候,想到有一天自己會死,覺得特別可怕。孫大勇點(diǎn)了一支煙,使勁吸了一口,咕噥了一句,死有什么可怕的,人活著不就那么回事嗎,活就活,死就死,無所謂。小宋咬著一粒西瓜子,研究著孫大勇的臉,說,大勇,你今天好像有點(diǎn)怪怪的。
孫大勇說忽然很想跳拉丁舞。小宋哈哈大笑,驚訝地問,大勇你會跳拉丁舞?真的假的呀?孫大勇就說起了學(xué)拉丁舞的事。他正說著,小宋打了一個面積大約二十平方厘米的哈欠,瞥了一眼墻上的掛鐘,忽然大聲說,哎呀你看看,快十一點(diǎn)了,光顧著說話,忘了做飯了。說著,她從沙發(fā)里站起來,拍了拍手,去了廚房。孫大勇又給那家保潔公司打電話,電話沒人接。他嘆了一口氣,打開電視看體育節(jié)目。
小宋在廚房里忙活了半個多小時,做了六個菜,有魚有肉,還算豐盛;還開了一瓶紅酒。孫大勇記得小宋是不喝酒的。小宋說,經(jīng)常有孩子的家長請她和同事吃飯,她都學(xué)會喝酒了,紅酒能喝半瓶。孫大勇今天本來不想喝酒,看小宋興致這么高,不好意思不喝;但下午還要去那家會所面試,又不敢多喝。一瓶酒,小宋喝了大半瓶。漸漸地,她臉色開始變紅,眼睛也有些迷離了,不時沖孫大勇嘿嘿地笑,沒頭沒腦地嘟噥一句:“你這個壞蛋,還和那時候一樣帥,越老越有味道了。”
吃完飯,孫大勇幫小宋收拾了碗筷,之后和她一起坐在沙發(fā)里喝茶。他看了一眼墻上的掛鐘,一點(diǎn)十三分。那家會所面試的時間是下午兩點(diǎn),從小宋家到會所,騎電瓶車大約需要十分鐘,時間還充裕。他打算在小宋面前跳一曲拉丁舞,馬上就走。他手機(jī)里存著好幾首經(jīng)典的拉丁舞曲,他想跳美國百老匯著名歌手馬克·安東尼的那首《I Need To Know》。
可是,他打開手機(jī)找《I Need To Know》曲子的時候,小宋起身去了臥室,又從臥室去了衛(wèi)生間。從衛(wèi)生間出來,她穿著一件嫩黃色的睡裙,身上散發(fā)著沐浴露和洗發(fā)露的香氣,臉更紅了,眼睛也更迷離。她倚著臥室的門框,嘿嘿地笑,說:“你這個壞蛋。”又嗔怪地柔聲說,“愣著干嗎,快去洗洗呀。”說著,她進(jìn)了臥室,半掩上臥室的門。
孫大勇嗓子有些發(fā)干,他咕咚咕咚咽了幾口唾沫,之后點(diǎn)了一支煙。大概因為吸得太急,眼淚嗆出來了,嘩嘩地流。他把吸了半截的煙摁滅在煙缸里,悄悄站起來,挎上那只黑色帆布挎包,躡手躡腳地向房門走去,腳步輕得像一只貓。他輕輕地擰開防盜鐵門,想輕輕地帶上,可是這門不用力帶不上,他只好抓著把手使勁拉。“咣當(dāng)”一聲,門關(guān)上了。這一聲“咣當(dāng)”也太響了,他渾身的寒毛都乍起來了。他愣了愣神,“哧溜”鉆進(jìn)了安全出口的樓梯,蹬蹬蹬地往下跑。
三
從小宋家溜出來以后,孫大勇騎上電瓶車,一溜煙地向西又向北,再向西再向北,最后居然來到了城市北郊的黃河岸邊。他總覺得小宋在后面追他,好像她是一匹狼,追上來會把他咬死,他只能沒命地逃竄。上了黃河大堤,他回頭望了望,只見遠(yuǎn)處一幢幢高樓大廈變成了一片森林,黃河大堤下面的公路上空無一人。小宋并沒有追上來,他這才松了一口氣。
他擦了一把汗,準(zhǔn)備去那家會所面試。可是,掏出手機(jī)一看時間,他腦袋上像挨了一悶棍,一下子愣住了:兩點(diǎn)十四分了。沒錯,手機(jī)上顯示的時間是“14∶14”。他盯著手機(jī)屏幕看了一會兒,時間又變成了“14∶15”。
剛才那一陣狂奔,孫大勇怎么也沒想到居然用了五十多分鐘。在他的感覺里,時間很短很短,頂多只有十幾分鐘。可是仔細(xì)一算,從小宋家到黃河岸邊,距離大約三十公里,還要等七八個紅綠燈,騎電瓶車用五十多分鐘已經(jīng)夠快的了……
那家會所的面試又錯過了。
孫大勇來到一棵歪脖子柳樹下,掄起巴掌左右開弓,在自己臉上“啪啪”地扇了幾十個耳光,直到滿嘴是血。之后又握緊拳頭,在柳樹上狠狠地砸了幾十拳,直到手背上也鮮血淋漓。他的臉火火辣辣地疼,手背一陣陣刺疼,心里倒舒服了一些。
那么現(xiàn)在去哪兒呢?孫大勇不知道。但他知道,家是不能回的。他腦子里很亂,想在這個地方靜一靜,于是在歪脖子柳樹下的石凳上坐了下來。今天偶遇小宋的那些場景在他眼前揮之不去;同時,沉睡在他記憶深處的那些漫漶的舊事,也像按在水里的葫蘆一樣,直往上頂。
孫大勇在服裝廠倉庫當(dāng)搬運(yùn)員的時候,小宋是保管員。倉庫一共四個人,兩個女的,是管理員;兩個男的,是搬運(yùn)員。閑下來的時候,四個人就看報紙、喝茶、說笑。小宋的老公是另一家大企業(yè)的業(yè)務(wù)員,經(jīng)常跑外,一出去就兩三個月。十年前那個中秋節(jié),廠里發(fā)了一些福利。小宋拿不了,老公又出差了,就請孫大勇幫她送回家。那天是農(nóng)歷八月十三,孫大勇的老婆下午下班后帶女兒去她媽家送月餅,吃完晚飯才回家。孫大勇騎著摩托車,把那些福利送到了小宋家。小宋得知孫大勇的老婆不在家,就留他吃飯。那天晚上小宋的兒子去了奶奶家,只有小宋一個人在家。
小宋平時嘻嘻哈哈、沒心沒肺的,這天晚上正吃著飯,忽然流淚了。她說她心里苦,沒人疼。她的話一點(diǎn)鋪墊都沒有,孫大勇一下子慌了,手和腳都不知道往哪兒放了。小宋低聲抽泣,不斷用餐巾紙擦眼淚和鼻涕。孫大勇抬起屁股坐到小宋身邊,用右手食指和中指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膀。沒想到,小宋身子一歪,一下子倒在他懷里,使勁摟住他的腰,兩手使勁搓他的脊梁,鼻子里哼哼唧唧的。孫大勇渾身的血都涌到了頭頂上,腦袋瓜子嗡嗡的,他愣了片刻,一把抱起小宋進(jìn)了臥室。事畢,小宋像小貓一樣蜷在他懷里,一會兒哭一會兒笑,一會兒掐他一會兒擰他,說他真棒,真疼她,并讓他以后好好疼疼她。
小宋臉蛋漂亮,氣質(zhì)好,身材好,在人前很傲氣。幾位副廠長和車間主任都打她的主意,但她一概不瞅不睬。孫大勇從沒對她動過歪心思,平時只是說說笑笑而已。這次事情過后,他越想越感激小宋,覺得不是他疼她,而是她疼他,她對自己有恩。他是個知恩圖報的人,但他不知道拿什么報;既然她覺得那是他疼她,他就要好好地疼疼她,累死在她懷里也愿意。于是后來,他又偷偷摸摸地疼了她四回。
自從有了這層關(guān)系,上班的時候兩人再也不像以前那樣說說笑笑了。同事們都是過來人,一眼就看得透透的。于是風(fēng)言風(fēng)語就在廠子里傳開了。孫大勇的老婆質(zhì)問他有沒有那回事,他從小就不會撒謊,也不愿撒謊,這次就沒咬著后槽牙堅決否認(rèn)。老婆又哭又鬧又抓又撓,摔碎了八只碗,踩扁了三口鍋,一個多月沒消停。孫大勇也被小舅子揍掉了一顆后槽牙。好在不久廠子就倒閉了,同事們各奔東西,不然他真不知道該怎么待下去。
雖然這事兒弄得孫大勇聲名狼藉,但他從來沒有后悔過。不但不后悔,還覺得這是他這輩子最美好、最出彩、最值得回味的事兒。在那座高檔寫字樓當(dāng)“巡捕”的九年里,他一天一天沉默得像啞巴,那些男女白領(lǐng)都把他當(dāng)成無色無味的空氣,從沒人正眼瞧他一眼。但他們大概不會想到,這個沉默的“巡捕”也是一個有故事的人,這株不起眼的“野百合”也有過春天。想起和小宋的那些事兒,他的神情是恬靜、柔和的,心里是甜蜜、溫馨的。他這輩子活得窩窩囊囊,要是沒有這么點(diǎn)事兒,就更黯淡無光了。只是沒想到,九年沒見,小宋竟然變成那樣了。這些年他在心里一直把她當(dāng)女神供著,今天才發(fā)現(xiàn),這尊女神塑像已被“歲月”這把錘子殘忍地敲碎了……
這時,孫大勇看見三輛小轎車從河堤上開過來,停在距離他十幾米遠(yuǎn)的樹蔭下。從車上下來十幾個小伙子,看上去都是二十多歲,像公司的白領(lǐng)。一群年輕人說說笑笑,提著幾只方便袋下到了河灘上,都脫得只剩下一條內(nèi)褲,圍成一個圈,蹲在那里喝易拉罐啤酒。過了一會兒,其中的三個小伙子下了水,在水里游泳、嬉戲、打鬧,不時嗷嗷地尖叫。
孫大勇看了一眼手機(jī)上的時間,四點(diǎn)三十八分。天不早了,他該回家了。可是……可是他能回家嗎?他站起來,手里握著手機(jī),圍著歪脖子柳樹轉(zhuǎn)起圈來,按順時針轉(zhuǎn)了二十多圈,又按逆時針轉(zhuǎn)了二十多圈。之后,他嘆了一口氣,給老婆打電話,叫老婆“親愛的”,笑得“咯咯”的。他和老婆結(jié)婚十八年,最少十七年沒叫過“親愛的”了。老婆似嗔似怒,罵他神經(jīng)病,并問他找到工作了沒有。他笑嘻嘻地說,找到了。老婆問是什么工作,工資多少。他說在一家保潔公司當(dāng)部門經(jīng)理,一個月三千多塊呢。老婆的語氣一下子變得溫柔起來:“大勇,你說的是真的嗎?”他說:“是真的,親愛的。”老婆的語氣變得更加溫柔:“大勇,這一個月你受累了。今天是周五,咱閨女也回家,晚上咱們下飯店吧,也慶祝一下。”孫大勇的眼淚嘩一下子流下來了,他極力用平靜的語氣說:“好啊,親愛的。”老婆又悄聲罵了一句“神經(jīng)病”,問他什么時候可以上班,那家公司遠(yuǎn)不遠(yuǎn)。他怕老婆聽出異常,說了句“回家再說,你忙吧親愛的”,匆匆掛斷了電話。
掛斷電話后,孫大勇“哇”的一聲哭出來。從他胸腔里躥出來的這種哭聲尖銳、洪亮,很有穿透力,像狼叫一樣。不過,他沒哭幾聲就不哭了,因為他聽見有人呼喊:“救命啊——救命啊——”他循著聲音向河面望去,只見剛才下水的那三個小伙子在河中央,腦袋一會兒露出水面,一會兒又沒在水里,看上去像是沒勁了,在拼命掙扎。正在河灘上喝啤酒的幾個小伙子急忙跳進(jìn)水里,奮力向河中央游去。還有兩個小伙子從河堤上抬了一架十幾米長的木梯,齜牙咧嘴的,擰著身子向河灘跑去。孫大勇愣了愣,終于確認(rèn)有人溺水了,于是他飛身一躍跳到了河灘上,三下五除二脫得只剩下一條內(nèi)褲,蹚著水跑向河中央……
孫大勇去救別人,最先被救上來的卻是他。他跑向河中央,跑著跑著就一下子沒影了,被卷進(jìn)洶涌的漩渦里了。旁邊一個矮胖的年輕人見狀,急忙一個猛子扎下去,在漩渦中抓住了他的胳膊,努力向上托舉。另兩個年輕人則把那架長長的木梯伸向他。他死死地抓住木梯,被拖到了河灘上。他平躺在柔軟的河灘上,眼前一片金星,胃里一陣陣翻江倒海。矮胖年輕人蹲在他跟前,不住地按壓他的胃部,渾濁的黃河水一股一股從他嘴里噴出來。
年輕人問他需不需要去醫(yī)院,他說不用,過一會兒就好了。他問水里的人都救上來了沒有,年輕人說,嗨,那三個家伙是鬧著玩的,大家都被騙了,剛才把他們揍了一頓,晚上還得讓他們請客吃燒烤。孫大勇咧嘴笑了笑。年輕人問他現(xiàn)在感覺怎么樣,他有些蔫壞地說,今天下午出來沒帶水,渴得喉嚨冒煙,現(xiàn)在喝得飽飽的,感覺很好。年輕人“撲哧”笑了,說,大叔你真萌。他讓年輕人別管他,他要躺一會兒。年輕人叮囑他說,黃河水看起來很淺,其實下面有沙窩子,沙窩子里面有漩渦,以后游泳的時候一定要小心。他微閉上眼睛,舉起手沖年輕人擺了擺。年輕人說了句“拜拜”,站起來走開了。
孫大勇躺了半個多小時,胃里漸漸沒有不舒服的感覺了。他睜開眼睛坐起來,向四周望了望。這時天色有些暗了,西邊的天空飄滿了彩霞;波瀾不驚的黃河水也變成金色的了;河岸邊的柳樹在霞光中變成了黑綠色,仿佛油畫里的靜物一樣。一架銀色的飛機(jī)在絳紅色的云層中時隱時現(xiàn),向東北方向慢慢飄去。四周很安靜,一點(diǎn)聲音都沒有。河灘很空曠,一個人影都沒有。孫大勇忽然淚流滿面,繼而嘿嘿地笑,喃喃地自言自語:“活著真好啊,還是活著好。”
他想跳拉丁舞,于是站起來,找到了自己的衣服和挎包,從挎包里掏出手機(jī),把音量調(diào)到最大,播放那首《I Need To Know》。在馬克·安東尼激越、熱烈、令人陶醉的演唱中,他肩放平,膝放松,大腿和臀部夾緊上提,抬頭,挺胸,收腹,立腰,轉(zhuǎn)胯,旋轉(zhuǎn),留頭……他跳得精準(zhǔn)到位,絲絲入扣,很火辣,很激情,很魅惑。他的身體很白,又穿著白色的內(nèi)褲,在金色的霞光中宛如一只高貴優(yōu)雅的白天鵝。
責(zé)任編輯 王宗坤
郵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