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的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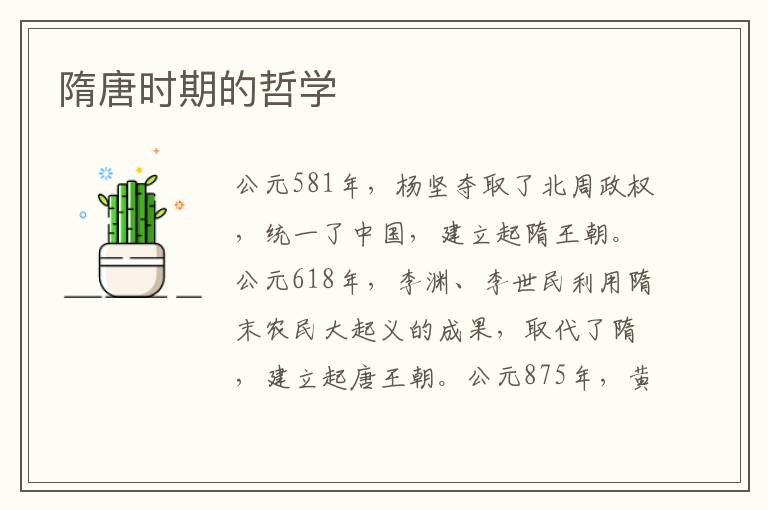
公元581年,楊堅奪取了北周政權,統一了中國,建立起隋王朝。公元618年,李淵、李世民利用隋末農民大起義的成果,取代了隋,建立起唐王朝。公元875年,黃巢領導的農民大起義,致命地打擊了唐王朝和社會上的腐朽反動勢力。公元907年唐亡。從此以后到公元960年,中國又處于分裂狀態,史稱五代十國。
隋唐兩代,仍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時期。唐朝建立后,社會曾出現了一個比較長時期的統一和安定的局面。生產發展,經濟繁榮,同國外的廣泛交流,使唐朝成為當時世界上的一大強國。但繁榮的背后醞釀著危機,特別是安史之亂以后,唐帝國陷入了分崩離析的局面。宦官專政,藩鎮割據,社會混亂,對廣大農民的剝削和壓迫日益加重,各種社會矛盾都在激化。在隋唐時期的政治斗爭中,總的來說,庶族地主不斷上升,門閥士族地主不斷衰落,僧侶地主興盛了一個時期,但不久也衰落下去。
隋唐時期,在生產發展和國內外廣泛交流的推動下,科學文化有很大發展。天文學、數學方面,隋唐之際的庚質、盧太翼和耿洵等,發明了用水力轉動的渾天儀,把天象儀和時鐘結合在一起,渾天儀的天象能跟著時刻的轉動而轉動。僧一行與梁令瓚創造了渾天銅儀,用以表示天體運行的速度。唐初李淳風等注釋的《十部算經》,已有三次方程的解法。地理學方面,隋代有《西域圖記》,唐代除修訂了《十道圖》,還編了《元和郡縣圖志》、《西域圖志》。賈耽著有《海內華夷圖》、《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等七種書。這些著作對國內各地和當時西域地區的山川形勢和民情風俗,都有具體生動的記載和說明。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根據自己的見聞,對中亞細亞、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國古代歷史和地理有重要記載。醫學方面,有孫思邈的《千金方》,王燾的《外臺秘要》,甄權的《脈經》、《針方》和《明堂人形圖》。唐時,中央設立了太醫署,開始分科教學;頒布了《新修本草》,其中收錄藥名八百四十四種。這些科學成就提高了人們對自然界的認識,也推動了當時哲學思想的發展。
隋唐時期,在思想領域內出現了儒、釋、道三者融合的局面,這三者各有一套為封建剝削和壓迫作辯護的理論,它們從不同角度欺騙和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特別是隋末農民大起義以后,唐朝統治者在政治強力之外,更需要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加強思想上的統治。孔子被封為“文宣王”,孔孟之書被奉為經典;老聃被封為“玄元皇帝”,老莊的書也成了開科取士的依據;佛教被大力提倡,到處建立寺院,僧侶經濟發達,僧徒遍天下,高級僧侶交通王侯,甚至參與宮廷斗爭,左右朝政。
隋唐時期哲學戰線上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佛教唯心主義哲學得到了高度發展,特別是由于佛教內部互相競爭,從而形成了許多不同的宗派。各派都圍繞佛性這個中心問題,把人的心理活動、精神修養和世界觀聯系起來,構成一個龐大的宗教唯心主義哲學體系。它們提出了一系列獨特的各詞、概念和范疇,用來對世界各種現象進行抽象的思辨和煩瑣的論證,從中得出宗教唯心主義的結論。如天臺宗和華嚴宗,常常從歪曲事物的相對與絕對、本質與現象、同一性與差別性的關系入手,來構造“一心具三千”、“三諦圓融”、“理事無礙”和“事事無礙”等理論。禪宗則常常夸大人“心”的作用,把世界上的一切都說成是人的幻覺,用以說明一切皆空與“本性是佛”的觀點。唯識宗比較拘泥于印度佛教教義,但它集中地分析了物質現象(色法)和精神現象(心法),并在分析論證中表現了較高的抽象理論思維的形式。唐代各派佛教哲學的論點雖然有所不同,但其形式不外是主觀唯心主義與客觀唯心主義,最終都歸結為主觀唯心主義,把物質世界和現實世界說成是人心造成的假象,把個人的心看成是成佛的依據,宣揚“一切唯心所造”。在認識論上,都宣揚唯心主義先驗論和神秘的直覺主義,用來論證他們所虛構的成佛的本性(“佛性”)是先天具有的。他們都把“佛”和“菩薩”看成是具有最高智慧的“大慈大悲”的“救世主”,把人民群眾看成是愚昧無知(“無明”)的“凡夫”,聲稱人民群眾只有依靠“佛”和“菩薩”才能得救,他們同樣是英雄史觀的鼓吹者。
隋唐時期反對佛教斗爭的主要代表是韓愈與李翱,但他們本身又都是唯心主義者,因此佛教唯心主義在唐代并沒有受到真正有力的批判。韓愈反佛主要是從維護封建的政治、經濟出發的,他不用唯物主義,而是用孔孟唯心主義;不是從批判佛教哲學中建立自己的學說,而是簡單地用傳統的天命來對抗佛教的神;用所謂儒家的“道統”來對抗佛教的“法統”,用性三品說來對抗佛教的佛性說。因此,他不但不能擊中佛教宗教唯心主義世界觀的要害,而且還從唯心主義立場加以吸收融合。他的學生李翱作《復性書》,基本上是按照佛性來講人性的。韓愈等人的反佛斗爭并不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但他反對為腐朽士族制度作辯護的佛教,反對寺院勢力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反對僧侶和道士的寄生生活,這些都是有利于社會向前發展的,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
隋唐時期,圍繞天人關系的問題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韓愈認為天是主宰一切的神;天在社會歷史范疇中體現為道;傳道的圣人都是受命于天的超人,他們決定社會歷史的發展進程,這樣,天、道、圣三者就構成了韓愈一整套唯心主義自然觀和社會歷史觀。柳宗元、劉禹錫認為天是自然現象,天地中充滿了元氣,元氣又分為陰陽二氣,二氣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世界萬物。天與人、自然與社會各有自己的規律,提出了“天人不相預”、“天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著名論點,對天人關系作了比以往更深刻的解釋。同時他們對天命鬼神迷信思想的批判,已深入到產生它們的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對無神論思想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社會歷史觀方面,柳宗元則把人類歷史看作是一個自然過程,它既不是什么天命決定的,也不是以所謂圣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是有其固有的客觀發展的必然趨勢。柳宗元、劉禹錫雖然基本上沒有把佛教作為批判對象,但他們的唯物主義自然與觀佛教唯心主義則是根本對立的。他們圍繞天人關系問題所發揮的樸素唯物主義觀點與無神論思想,對佛教唯心主義實際上也是一個否定。
隋唐時期,在社會歷史觀方面也展開了爭論。韓愈認為,人類歷史是由天意創造的,天意是由圣人體現的,因此社會的興亡治亂都是由圣人決定的。柳宗元則把人類社會看作是一個自然過程,是有其固有的客觀發展的必然趨勢,這種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