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定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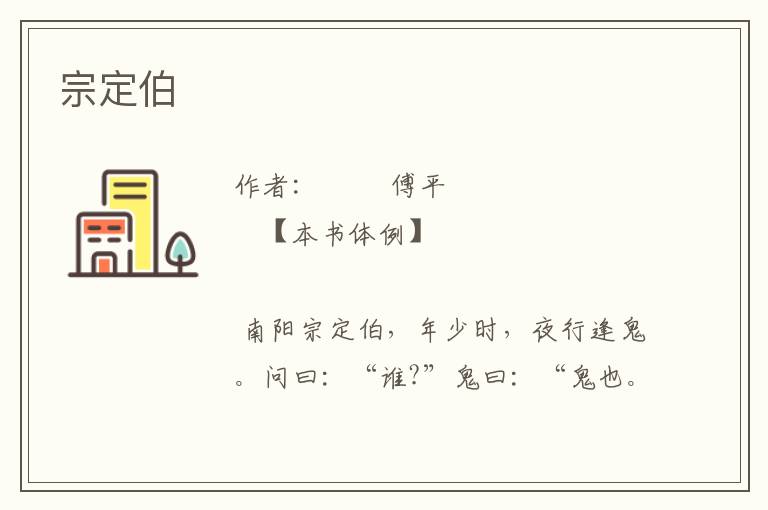
作者: 傅平 【本書體例】
南陽宗定伯,年少時(shí),夜行逢鬼。問曰:“誰?”鬼曰:“鬼也。”鬼曰:“卿復(fù)誰?”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數(shù)里,鬼言:“步行大亟,可共迭相擔(dān)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dān)定伯?dāng)?shù)里。鬼言:“卿大重,將非鬼也?”定伯言:“我新死,故重耳。”定伯因復(fù)擔(dān)鬼,鬼略無重。如其再三。定伯復(fù)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曰:“惟不喜人唾。”
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因命鬼先渡,聽之,了無聲。定伯自渡,漕作聲。鬼復(fù)言:“何以作聲?”定伯曰:“新死,不習(xí)渡水耳。勿怪。”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dān)鬼至頭上,急持之。鬼大呼,聲咋咋,索下,不復(fù)聽之。徑至宛市中,著地,化為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乃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于是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
(選自《列異傳》)
宗定伯,南陽人,年輕的時(shí)候,一天夜晚走路碰到一個(gè)鬼。問:“你是誰?”鬼說:“我是鬼。”鬼反問:“你是誰?”宗定伯欺騙他,說:“我也是鬼。”鬼說:“你要去什么地方?”宗定伯回答說:“想到宛市。”鬼說:“‘我也要到宛市。”兩人同行了幾里路,鬼說:“步行很快,咱倆輪換著互相背,怎么樣?”宗定伯說:“很好。”于是鬼先背宗定伯走了幾里路。鬼說:“你太重,你不是鬼嗎?”定伯說:“我才死不久,所以重些。”定伯又開始背鬼,鬼沒有多少重量。輪換背了幾次,定伯又說:“我才死,不知道鬼害怕什么?”鬼說:“只是不喜歡人的唾沫。”
他倆往前走,遇到了一條河溝,定伯讓鬼先渡河,聽不到一點(diǎn)涉水的聲音。定伯渡水時(shí),嘩嘩有聲。鬼又問:“為什么有聲音?”定伯答:“我才死,不習(xí)慣渡河,才有聲音,你不要見怪。”共同走到宛市,宗定伯就把鬼頂在頭上,急忙抓牢它。鬼大聲呼喊,要下來,宗定伯不再聽他的。一直至宛市上,把鬼放下來,鬼變成了一只羊,宗定伯就對(duì)它吐唾沫。防止他變化,宗定伯賣了羊得了一千五百錢,離開宛市回去了。于是有人說:“宗定伯賣鬼,得到了一千五百錢。”
這是一個(gè)很有趣的故事。
宗定伯和鬼打交道,能把非常精明的鬼騙住,是很希罕的,充分表現(xiàn)了宗定伯機(jī)智、勇敢、沉著的個(gè)性。
作者塑造宗定伯的性格,不單靠敘述故事,主要靠的是用人物的行動(dòng)來塑造人物。
夜晚走路相遇,自然要彼此盤問一番,打聽一下相互的身份,心中有個(gè)數(shù)。當(dāng)宗定伯得知對(duì)方為鬼,便欺騙地說:“我亦鬼。”鬼相信了。
民間迷信的說法,鬼最精明。于是。形容某某人點(diǎn)子多,往往說“鬼精”、鬼頭鬼腦”、或“鬼得很”這類詞。和精明的鬼同行,人不“鬼”一下,是會(huì)吃虧的。為了避免吃虧上當(dāng),宗定伯就以新鬼無知為由探聽制服鬼的秘密。萬一出現(xiàn)破綻,引起了鬼的疑心,也有個(gè)法子制服鬼。鬼交待了“不喜人唾”。于是,宗定伯就有了主動(dòng)權(quán)。到了宛市,抓住鬼不放,表現(xiàn)得十分堅(jiān)定。鬼無奈,變?yōu)檠颉W诙úu了羊,又吐羊身上一口唾沫,鬼被制服了,不能再變了。
這篇故事講的是人鬼的關(guān)系,宣傳了人不怕鬼的思想,這在一千七百年前迷信思想濃厚的時(shí)代,是很可貴的。
今天讀這篇故事,我們不妨把意義引伸一下:鬼是壞蛋、犯罪分子,是天災(zāi)人禍,是困難,是洪水猛獸。這一切,可以稱之為“鬼類”。人要戰(zhàn)勝“鬼類”,一定要想辦法,動(dòng)腦筋,找出制服“鬼類”的方法和竅門。方法找準(zhǔn)了,再有適當(dāng)?shù)臅r(shí)機(jī),就能戰(zhàn)而勝之。
作者為故事安排了幾次波瀾,克服了一般筆記小說平鋪直敘的毛病。第一次波瀾是宗定伯身子沉重,引起鬼的懷疑;第二次波瀾是宗定伯過河有聲;第三次波瀾是鬼無可奈何地變成羊被賣掉。三次波瀾,使故事曲折,情節(jié)起伏,產(chǎn)生了引人入勝的藝術(shù)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