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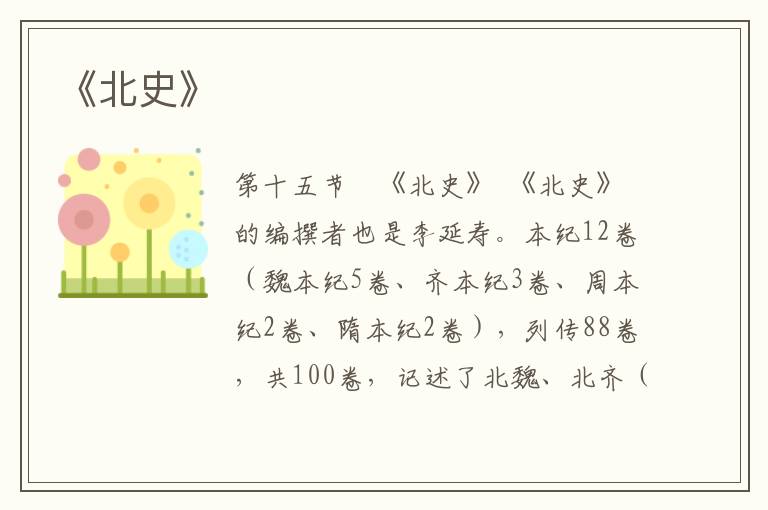
第十五節 《北史》
《北史》的編撰者也是李延壽。本紀12卷(魏本紀5卷、齊本紀3卷、周本紀2卷、隋本紀2卷),列傳88卷,共100卷,記述了北魏、北齊(包括東魏)、北周(包括西魏)、隋四代的史事。起自北魏道武帝登國元年,終于恭帝義寧二年,共三代,計二百三十三年。
本紀部分以魏、齊、周、隋為主,增補了西魏的三帝紀、皇后的傳記,以及魏宗室的部分史料,另外還增補了梁覽等人的專傳。
列傳部分的敘述次序,按先魏宗室、諸王,次魏諸大臣,然后先齊宗室、諸王,次齊諸大臣,直至周、隋,分朝進行敘述,體例井然有序。但也并非全部盡然,個別的列傳部分因為以子孫附傳,所以就造成了敘述時序的混亂。另外,在敘述體例方面,對于權位歷代相承者,作者往往把他們都列入了“家傳”,這與“國史”的編次不相符合。
《魏書》的部分大多以魏收的記載為依據,對于《齊書》則進行了大幅度的增刪,《周書》的刪減有限,《隋書》也是略有刪節,但錯誤偏頗部分沒有糾正,并且有很多的回護。如隋文帝殺周朝皇室諸王一事,《周書》里面記載的是諸王因為謀劃執政權位被害,《北史》的記載則是他們有罪而伏法。對于隋煬帝弒父的事件,仍舊因襲了《隋書》對此事的回護方法。
《北史》可稱道之處正如《四庫提要》所說:
延壽既與修隋書十志,又世居北土,見聞較近,參核同異,于北史用力獨深,故敘事詳密,首尾典贍,如載元韶之好利,彭樂之勇敢,郭琰、沓龍超之節義,皆具見特筆。出酈道元于酷吏,附陸法合于藝術,離合編次,亦深有別裁。視南史之多仍舊本者,迥如兩手。(《四庫提要》卷四十六)
李延壽撰寫南北史的最初動機,就是繼承父志,貫通南、北各朝。所以,他在《北史裴蘊傳》中說“祖之平,父忌,《南史》有傳”,在《王頒傳》中又說“父憎辨,《南史》有傳”,所有這些,都是兩書相互貫通的印證。盡管如此,但還是存在不少重復的地方,如:《南史》列傳中有晉熙《王昶傳》,而《北史》又列《劉昶傳》;《南史》中有《豫章王綜》、《樂良王大圜傳》,而《北史》又列《蕭大圜傳》——這些都是一人兩傳,但未予刪改合并。
南、北二史的共同特點都在于敘事簡潔明凈,都屬于史籍中的佳作。相對于《北史》,《南史》對所依借的史書舊本刪減、補缺都較少,而《北史》在這方面則耗費了撰者極大的精力。雖然后世毀譽參半,但以一己之力,能成煌煌兩本史書,也絕非常人所為,所以,雖有部分失真或者說不足,還是可以稱為瑕不掩瑜。清朝的史家李慈銘對《南北史》校讀的方法,有較為中肯的述評,他說:
竊謂本紀宜用南北史,列傳宜用八書,而去其重復,平其限斷,除其內外之辭,正其逆順之跡,更以彼此互相校注,志則用《隋書》中五代史志,而注以宋魏南齊諸志,庶為盡善矣。(《越縵堂讀史札記》)








